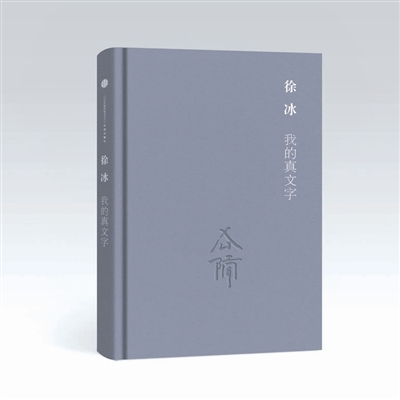
徐冰的新书 《我的真文字》
古元和解放区艺术的深度
“现在看来,对我有帮助的,是民族性格中的自省,文化基因中的智慧,和我们付出的有关社会主义实验的经验,以及学习西方的经验。”徐冰总结说。在全球化语境之下,艺术家们谈论中国传统和西方经验的绝对不少,但社会主义经验倒真是听起来新鲜。但对徐冰而言,在每个需要辨别方向的阶段,古元先生是他的参照坐标。
徐冰写古元不止一次,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学时代,他模仿范文《我爱林风眠的画》写了篇作文《我爱古元的画》。1996年,古元先生去世,徐冰在纽约写了一篇悼文《懂得古元》,谈及古元所代表的解放区文艺如何影响了他。
“木刻版画其实是西方的画种,中国的木刻运动和木刻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古元、李桦这一代人建立起来的。”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解放区的古元和国统区的李桦,堪称“新兴木刻运动的两面旗帜”。“要我看,以古元为代表的解放区的这些人在艺术上做了更多的推进。”徐冰对古元艺术的感情,就像对某种“土特产”的瘾。
“解放区的艺术家最初刻得和国统区艺术家一样,比较西方化。”徐冰说。他们把作品拿给农民看,农民看到脸上一道一道的刻痕,都说不好看。“后来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创作要源于生活,为人民服务,向民间学习。咱们这些土八路琢磨出一套中式木刻法,版画里的老百姓脸上干净了,不像洋人了,画面也喜庆了。老百姓一看,特别喜欢。”
在徐冰眼里,恰恰是解放区的“土”艺术家很有成效地处理好了艺术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创造了新的艺术样式。古元的工作方式不是“深入基层的采风”,他就生活在农村,被分配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参加农村基层工作时,古元渐渐知道了农民喜欢的艺术语言,他把《羊群》初稿拿给老乡看,几经修改,完稿时老乡甚至可以认出自己家里的羊。“他们想的不是艺术,而是如何为百姓服务,为政治运动服务。在不为艺术的艺术实践里,获得了最有效的进展。”说到底,“如何处理艺术家和社会现场的关系,古元那一代解放区艺术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