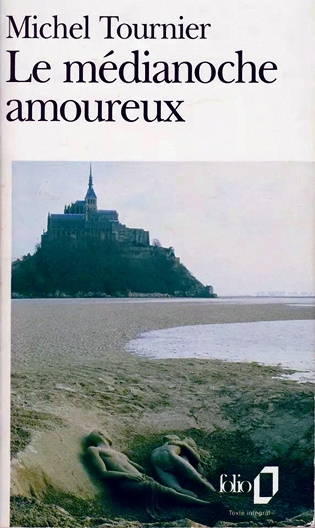
要说“新寓言派”里写书写得最好看的一位,还得说是最熟悉污浊之物的图尔尼埃。这污浊之物可以是粪便,是战争和杀戮,也可以是最普通的现代存在:城市,街道,楼房,车辆。他的短篇《铃兰空地》,写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喜欢上了一片宛如沙漠绿洲一般的、长满铃兰花的空地,但城市里飞奔的钢铁和车轮,扼杀了他最后的梦想。勒克雷齐奥在其生涯早期也写过类似的“残酷童话”,《飙车及其他新闻故事》里的少男少女,企图在庸俗沉闷的城市生活里寻找刺激,他们飙车,让激增的肾上腺素,帮助他们体验逼近死亡的高潮。
虽然喜欢孩子,为孩子写书,但图尔尼埃自己不娶不育,他的相貌似乎一生都没有变过,老来更有种特别奇怪的童颜。他像是科幻卡通片里的天外来客,跟地球上的主人公慢慢耗熟,然后在一个特殊的时机,和盘托出自己所肩负的、要改变太阳系诸星球上物种分布的计划……
他只有一位养子,当1月18日,91岁的他在睡梦中去世,出面通报消息、接待来访的都是他的养子。《桤木王》里着迷于男童身体的阿贝尔·迪弗热就是他自己,血统纯正的德国军人是他眼里美的化身。三岁看老,16岁时家里的那间小阁楼,便决定了图尔尼埃将来是个怎样的人。
图尔尼埃是不是法国的“一流作家”?依我的理解,当然是,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不肯垂顾于他,而选择了“新寓言派”里比他年轻的另两位,肯定他们的成就。图尔尼埃自己说,他是巴尔扎克和左拉的继承人,他写小说,是有话要讲,而不是为了“玩”。此即老派作风。同样老派的是他对媒介的认识:符号高于图像——电影高于电视,文学又高于电影。法国作家、学者跨界去搞电影的不少,对此,图尔尼埃是比较不屑的。
《桤木王》也曾改编成电影,导演是德国大导、专爱拍第三帝国题材片子的沃尔克·施隆多夫。主演迪弗热的约翰·马尔科维奇,容貌粗糙,戴着一副小圆眼镜,跟他相对的则是气宇轩昂、民族荣誉感十足的德国人。做这件事,估计导演费了一番说服工夫,因为图尔尼埃一向认为,只有三流小说,比如西姆农的梅格雷探案系列,才适合改编成电影。
有点电影常识的人,都知道克劳德·朗兹曼拍过一部九个半小时的纪实长片《浩劫》。朗兹曼跟图尔尼埃两人亲密无间。《浩劫》首映时,朗兹曼邀请老友观摩,被他拒了:“坐那儿九个半小时,我要死掉的。”后来图尔尼埃出版小说《金滴》,给朗兹曼寄了一本。导演大怒。“你疯了吗?”他打电话过去,“你不来看我的电影,却要我看你的书?”
图尔尼埃也怒了:“可是这俩不一样!你的电影要逼你一动不动地看完,我却没有逼你读我的小说,你放着或扔了,随你,你拿在旅途中读也行,你是自由的。电影跟书不同,电影把人变成了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