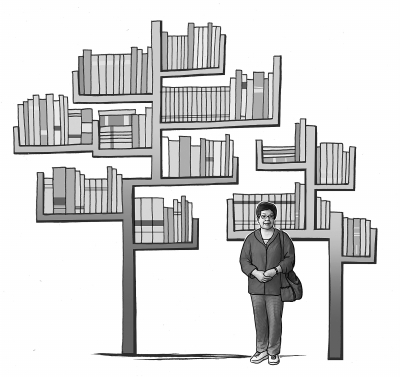 插图 宋溪
插图 宋溪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会儿书,是郭斌这个图书馆人多年的老习惯。八年前,她从西城区图书馆馆长的职位退休之后,又被聘任为西城区图书馆管理协会的会长,“我跟图书馆的缘分,几乎就是一辈子。我们的图书馆事业现在发展特别快,必须学习,真的,‘活到老,学到老’绝对不是个形式。”
结缘 我们阅览室的背景就是故宫角楼
小时候跟着父母住在单位宿舍,郭斌就迷上了那里的图书室,看书之余,她也经常帮忙整理图书。“后来有一次,图书室的一个大姐姐要去首都图书馆办事,她跟我说:‘我带你去看个图书馆’。”
当时的首都图书馆还在国子监,郭斌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震撼:“我到那儿一看,呀!这么大的图书馆!还是古建!这么壮观!他们还跟我讲,那儿是过去中国‘历代皇上讲学’的地方。” 从那一刻起,郭斌对图书馆的崇敬油然而生,“当时我就想,要是能在这儿工作,该多好!”
从学校毕业之后,郭斌真的被分配到了文化系统工作,“先让我们到基层去锻炼,可以选单位。” 当听说待选单位里有图书馆的时候,她立刻表态要去图书馆,“当时别人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姑娘愿意到图书馆去工作。” 郭斌笑着说,“很多人觉得图书馆是个给人做嫁衣,默默无闻的工作。”
那时的西城区图书馆在西华门,“也是一个古建筑,是武官朝拜天子的后朝房,挨着故宫筒子河,图书馆阅览室的背景就是故宫角楼。”
郭斌的职业理想实现了,但“特别喜欢图书馆”的她也有过动摇,并且直接导致了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西城区夙称文化教育区,我们的图书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总馆有分馆了,在当时区县图书馆里,我们的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但那时候图书馆的工作还是很传统,更像藏书楼。我就觉得图书馆太封闭,太死板了。” 困扰中的郭斌想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当时单位推荐我去北大上学,学图书馆专业,但是我没去,放弃了。”
后来再去北大进修时,她一个人坐在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哭了半天,“那么难得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真是脑袋进水了。”如今,头发花白的郭斌回忆当年的自己,哈哈一笑。
从馆长到会长,郭斌再也没有离开过图书馆。而这个行业近年来的变化,让这个老图书馆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压力。
新意 菜市场也能开图书室
“过去我们跟国际上的同行交流,总觉得和别人差距特别大,尤其是在硬件上;但是现在不同了,别人常常也会用羡慕的眼光来看我们;像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的负责人,曾经到我们的图书馆也参观过,他就感叹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太快了。’”
身在其中的郭斌,则看到了硬件提升之外更深层次的变化,“我感觉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最近十年,而最近三年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不光是场馆建设这些硬件的提升,还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像张家港市的驿站图书馆、扬州的城市书房、北京西城的公共阅读空间……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 郭斌感到,这是一个和自己当图书馆馆长时完全不同的发展环境,图书馆不再是藏书楼,图书馆管理协会也不再局限于只为会员单位服务。
“曾经有个超市找到西图协会,想在店里建一间图书室来吸引顾客,但后来因为客流很好,图书室挤成了一丁点,成了个点缀品,我们觉得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于是西城商委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建议我们到他们的网站上‘招商’。”郭斌和同事们虽然也犹豫公益组织“招商”靠不靠谱,但还是决定试一试。“当时的四环菜市场找到我们,想在市场里建一个为农民工服务的图书室。”作为西城区政协委员的郭斌恰好关注过“菜娃”的问题,“‘菜娃’是说一些农民工在市场里摆摊卖菜,他们的孩子就在菜包上待着。”双方一拍即合,菜市场腾出了一间最好的办公室,全市首家农民工图书室建立了。西图协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图书室办了起来,而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各摊位的农民工不光利用图书室教育孩子,他们自己的精神面貌也有所改变。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之后,还有人给图书室捐书捐玩具。
虽然后来菜市场由于疏解城市功能的需要搬离了西城,但这次尝试既让郭斌体会到图书馆协会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看到了社会力量的影响,“感觉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们的服务可以有很多新课题,新内容。” 郭斌和协会同事们开始思考,如何利用环境发展提供的机遇,打破过去社会组织等靠的生存方式,走出社会组织和政府脱钩后的发展瓶颈。
尝试 书不但没被拿光,还放进去不少
“就是借脑、借势、借力;很多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可以跟区域里方方面面的资源合作。”郭斌总结说,“比如‘老龄化’问题是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热点,政府和社会都很关注,那我们能做什么?书,亦药也。我们就发挥图书的作用,为银发群体提供‘阅读疗法’,把阅读推广活动做到社区,让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健康快乐生活。”
书是资源,但作为一个5A级社会组织,他们的资源不仅是书。西图协会和北京邮电大学的公益组织“夕阳再晨”合作,请大学生们到社区来教老人们用微信,“有老人当场就跟在国外的孙子通话了,孩子还特别吃惊:奶奶你怎么会用这个?”
“我们还在汽南、前铁社区挂了科普主题的图书‘迷你箱’,不用像图书馆那样需要借还手续,还可能有滞纳金;就是让社区居民可以自取一本,也可以放一本。”筹备项目时,郭斌和同事们思考过可能会出现的窘况,“担心一放上去,书就被拿光了,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担心会不会碰上收废品的,连箱子都给端了!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书不但没给拿光,有的地方居民还放进去不少。” 郭斌觉得,这个小平台也在促进社区的邻里守望。
“很多事都是我们过去没做过的。”在不断的新尝试中,郭斌也感受到了压力:“倡导全民阅读,建立‘书香社会’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我们也有做不完的事,政府和企业跟我们要咨询的专家,公共阅读空间跟我们要专业馆员、文化志愿者……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需要探索,越来越需要把学习内化到工作中来提升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真不是一句空话。”
细节 辅导作业、帮填税表……图书馆的资源不止于书
在为国内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而自豪的同时,郭斌也在每一次交流考察中留意国外同行们的长处。“这几年,我们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真是不少了,我们的建筑规模、硬件设施已经比很多国外的图书馆更好,但在一些服务细节上还要学习。我们的硬件不比别人差,但读者量和服务内容仍然有差距。”
在美国纽约,郭斌发现当地图书馆的同行们对中国的情况极为关注。“在皇后区图书馆,我发现他们的拓展部(相当于我们的儿童部)装饰很眼熟,他们的主任就乐了,说这个布置是跟大陆的图书馆学的。在布鲁克林图书馆,他们的一个负责人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数字图书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关心这方面?他说,这几年中国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很多人到图书馆来查中文资料,所以他想了解一下哪些资料适合他们的图书馆。其实国内的图书馆现在也购置了大量的数字资源,但利用得不是特别好,缺乏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另一个在郭斌看来非常值得借鉴的,是美国图书馆为社会融合所做的努力。“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图书馆也专门为移民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比如皇后区的图书馆有63个分馆,他们会特别关注区域里的新移民。过去叫‘扫盲’,现在不是了。比如现在有很多美国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他们就会利用华裔的移民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然后再对新移民进行教育。他们的图书馆里还提供每个街区里人种、民族的文献,定期组织活动,把区域里各个移民群体融合在一起。”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也承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责任,比如他们的馆员都会熟练地填写税表,因为这是公共图书馆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每年的纳税日帮助国民填写税表。另外,他们的公共图书馆有少儿部,他们把图书馆作为少儿的安全岛,里面的馆员还要给孩子们辅导家庭作业;图书馆甚至和软件公司合作,开发图书馆作业辅导系统。”
让郭斌印象深刻的还有首尔图书馆的残障阅览室,“韩国国家不大,图书馆规模也不大,比如首尔图书馆,就是四千多平方米,他们的残障阅览室服务细节做得非常好。举个例子,假如我右手有残疾,它提供左手键盘;我左手有残疾,他有专门的右手键盘……很体贴。我们很多地方国家也一直在投资建设残疾人阅览室、视障阅览室了;但是对特殊弱势群体的服务不光是形式上的,而应该想办法提供完备的措施,让他们更好地利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