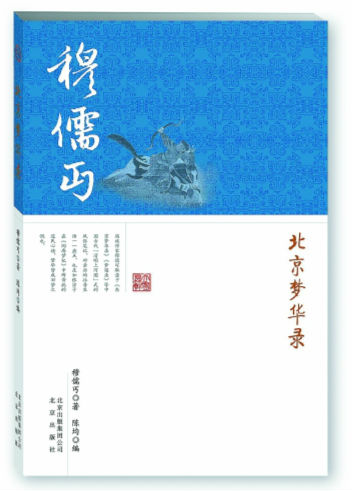
《北京梦华录》 穆儒丐 著 北京出版社
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苦闷
穆儒丐的写作体现出一名作家最起码的良知,那就是当鸡蛋与墙碰撞时,他坚决地站在更弱的那一边。
虽然遭遇太多的黑暗,穆儒丐却不肯麻木、不肯沉沦,他笔下没有肮脏的描写,没有轻佻的挑逗,他对人性缺乏信心,却能免于玩世不恭。他讽刺议员、将军们的无耻与虚伪,看不起同僚的与世沉浮、毫无准则,鄙夷小市民的唯利是图、定力不足,但他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一切,只能寄希望于草莽人物身上偶尔闪现出的人性光芒,并将其加以夸大。
“但是这些熙来攘往的人,穿着极美的衣服,坐着极好的车辆,究竟他们在社会上是做什么的?高高兴兴地出来,有什么目的呢?……社会上什么东西是他们创造的?社会上的文明,哪一样是由他们振兴的?他们在社会国家里,究竟是有什么意义?”从这段疑问中,可以看出穆儒丐深深的困惑。
在日本留学时,穆儒丐也曾激烈过,“什么事都喜欢新的,那时候我骂中国的东西,比现在的青年还厉害呢”。当时日本是革命党的基地,可作为旗人,穆儒丐不可能被主张暴力革命的同学接纳,穆儒丐曾写道:“当时是最流行的,崇拜孙文、黄兴的人,谁不天天说两句‘杀满奴’,嘴里头自要有‘满奴’两个字,便算革命党人,在会馆里,也可以当一名干事。”
或者正是因为这段挫折,使穆儒丐终生信奉改良主义。
不被革命党接纳,而自知改良又无法成功,故穆儒丐的小说虽然写得很有切肤之痛,却流于发牢骚。
他痛骂:“想一想那些女工劳动十二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圆的报酬,而她们所制造的成绩品,便是一点生产事业不做在国家社会里横行无忌军人丘八所穿的制服。当他们穿上这身制服,他们绝不想一想,这是无数可怜的贫女,为了六枚铜圆的代价,替他们制成。他们穿了这身制服,居然跻登社会上最高的阶级。也就因为有了这身制服,他们便能把给他们缝制服的人,看得没有一条狗有价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们身上,便如给虎添翼。”
可除了骂,穆儒丐也拿不出实际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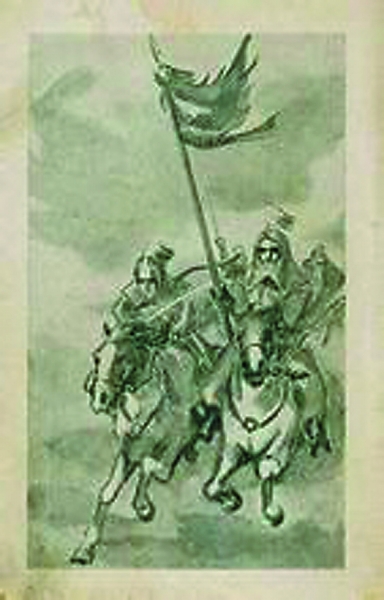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插图
穆儒丐《福昭创业记》插图
被日寇利用
1937年至1938年,穆儒丐连载了他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这本书写到努尔哈赤兴兵,以及皇太极移居沈阳,奠定皇朝基业,小说最终以八旗入关、吴三桂投降为止。
为了写好它,穆儒丐参考了大量历史典籍,力求真实,但字里行间掺入许多肤浅议论,宣扬了狭隘的民族意识。穆儒丐这么写,体现出他经历多年困惑之后,思考而来的结果——既然找不到解决方案,那么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英雄、伟人身上,期待他们来拯救危局,实现平稳改良。
此外,在穆儒丐的思想深处,确有遗民情结,对前朝颇为留恋,他曾写道:“再说前清时代,科考举子,任是贫富,都是衣冠中人,一个个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读书种子,国家社会,都知道另眼看待。如今无论考什么,也见不出什么体面来,纯粹是饭碗问题。社会的组织变了,读书人自然没有从前有价值。”
《福昭创业记》是穆儒丐此生写的最长的一部小说,共计40多万字,却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旧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从写作技术上,堪称是全倒退。
然而,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穆儒丐的这本小说恰好能被政治利用,故伪满洲国立即开动宣传机器,全面鼓噪,并授予这本小说“民生部大臣赏”,该书1939年正式结集出版,1986年,该书曾经再版,但只是删节本。
穆儒丐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悬念:他与傀儡政权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他甘心充当其吹鼓手?伪政权倒台后,他为什么能逃过法律的惩处?有了这段说不清的履历,他又是怎么在后来历次运动中过关的呢?
虽然有《福昭创业记》这样的乱流,但穆儒丐很快又回到了原来的创作轨道中,1941年至1942年,他完成了新的社会小说《如梦令》,描写健锐营乡亲们进城后,被生活所迫,最终不得不卖儿卖女,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也是穆儒丐最后一部社会小说。在小说中,穆儒丐哀叹道:“社会是什么?伦理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了。”
此时,穆儒丐似乎已经放弃拯救的尝试,甘心将一切视为宿命了。
他从历史中走失
1945年,穆儒丐回到北京,此后的人生轨迹成谜,经著名学者张菊玲等先生多方考证,目前可知大概:回京后,穆儒丐见人只称自己的汉名宁裕之,他一度沉迷于八角鼓、单弦等曲艺,写了很多作品,集于手稿本中,被友人珍藏,其中一首题为《自遣》的七律这样写道:
苦茶一盏代白干,饭后能拧一袋烟。
老眼不花书细字,闲情有寄校芸篇。
文章西汉难追企,乐府东篱尚可攀。
高歌一曲调元气,今日才知乐尧天。
张菊玲先生认为这首诗其中深含隐忧。1953年,在张伯驹先生的介绍下,穆儒丐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令人意外的是,在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竟无一本提起穆儒丐。
一方面,文学史是一个遴选、建构的过程,选谁进入,便意味着授予其地位与身份,这其中包含着权力的运作过程,而穆儒丐处境不佳,他主要影响在伪满洲国,作品多发表在敌伪报纸上,而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穆儒丐的写作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基本没响应过主流文学界的任何号召,虽然穆儒丐的小说也有社会批判、反思民族性等方面内容,但与严肃作家们往来太少,被视为圈外人,而在通俗作家中,穆儒丐的小说又显得过于沉重,不够轻松、刺激,不适宜休闲阅读。
因为不好定位,致使穆儒丐的文坛地位被彻底忽略,此外,穆儒丐的作品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硬伤,有特色,但难称是佳作。
穆儒丐的小说多来自真实事件,在情节上构思不足,显得过于呆板和潦草,人物漫画化,性格没有变化过程,此外作者对议论过于自信,经常派主人公发表一番不切实际、不顾情境的道德教训,伤害了作品的真实性,此外穆儒丐的幽默藏得不够,相比之下,来自底层的老舍也是旗人作家,却更善于板着脸说笑话。
穆儒丐小说的优美来自细节,语言生动,刻画细腻,但整体上捏不起来,读者可以轻松读完,却很难留下深刻印象。毕竟穆儒丐的创作是新文学发端初期的写作,相对幼稚,缺乏整体感,且穆儒丐的作品都是边写边连载,不易写出精品。
但,穆儒丐仍不失为一位风格作家,他的小说是清末民初之交北京社会动荡的精彩记录,堪称并世无双,仅此一点,穆儒丐便不应被遗忘。
1961年2月15日,76岁的穆儒丐与世长辞,据一些见证者说,他身后“无嗣”,但也有人称,他有儿有孙,孙子叫宁俭,究竟谁是谁非,尚无公断。据同好称,穆儒丐晚年曾写过岔曲《敬爱的毛主席》,但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