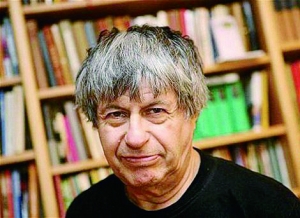 伊凡·克里玛
伊凡·克里玛
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他的童年,这也成了他为自由而奋斗终身的开始。这些悲惨经历的烙印渗透在他的文字之间,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
现年85岁的克里玛,是当今捷克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之一,欧美文学评论界一向将克里玛与昆德拉、哈维尔和赫拉巴尔相提并论——几人之中,哈维尔和赫拉巴尔已经去世,昆德拉又移居法国,现如今唯一留在捷克,留在布拉格的,只有克里玛。对他来说,祖国和母语,无法割舍,他习惯于在祖国的氛围里创作。而克里玛的始终在场,让他的文字与捷克人心绪相通,也难怪捷克评论家一致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均在昆德拉之上”。
在集中营 度过童年时光
“我想我继承了母亲对寂寞的偏爱。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害怕独自待在黑暗中。”——伊凡·克里玛
1931年9月14日,布拉格的伊梵考德斯,伊凡·克里玛出生在一个祖上具有犹太血统的富裕家庭之中。他的父亲维兰·克里玛是位电机工程师,一家人过着恬淡而宁静的生活。
然而,无忧无虑的时光并不长,因为纳粹占领了捷克。克里玛第一次亲眼见到盖世太保时只有7岁,当时是1939年,纳粹入侵捷克不久,这些德国秘密警察冲进他家中寻找他的两位叔叔。这是一段残酷的经历,他的家乡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克里玛被禁止去上学,也不能够去看电影或者逛公园,他们一家人被迫穿上了黄角星的衣服——这是贱民身份的标志。在这之前,克里玛从来没有听说过“犹太人”,他的父母也并不知道自己祖上具有犹太血统。然而,战争将这个标签打在了他们的身上,用克里玛自己的话来说,希特勒的上台,让他们一家人成为了犹太人。
1941年,10岁的克里玛和祖父母、父母、弟弟等家人一起被送往泰雷津集中营关押——这里是纳粹在布拉格北方修建的“堡垒”区。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祖父母的死亡,看到了他的同伴死于毒气室。“作为一个从集中营里出来的孩子”,克里玛写道:“对于那些幸免于这种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周围的人随时会被杀死的生活。生命可以说就像是一根琴弦,这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接受到的教育。”
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克里玛只有一本书——《匹克威克外传》,这是狄更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匹克威克及其3位朋友外出旅行途中的一系列遭遇。这本书克里玛读了一遍又一遍,沉浸在山姆·维勒和纳撒尼尔·温克尔的世界里。
在这里,克里玛一家人度过了3年多的时光,直到“二战”结束,一家人才被解救离开泰雷津集中营。事实上,克里玛一家人能活着走出集中营,还得益于父亲是个电机工程师——集中营维持运转需要电机工程师,他们一家也因此得以免于被运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也才有机会等到最终的自由。
为了自由剥夺是值得的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一定会听信于重复千万遍的谎言,并开始怀疑真正的现实。”——《我的疯狂世纪》
除去暗无天日的恐怖,这段在泰雷津集中营中的极端经历让伊凡·克里玛对幸福和自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与此同时,他听从自己内心对创作的召唤。用克里玛自己的话来说:“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
在集中营里,克里玛开始写作,每一页都被他当作有可能是自己写下的最后一页,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种不停逃离的感觉。他写作剧本,用自己的木偶去表演,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故事里的女孩,他第一次爱上了做白日梦。等到离开集中营后,克里玛发现,这种创作的能力并没有离开他。
自由是他心中所有故事的主题,正如他多年以后所说:“我对缺乏自由的感觉远胜过对缺乏食物的感觉。”在他位于布拉格的家中,克里玛告诉采访者,“我一直追寻着内心的自由……为了那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感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
少年时代的克里玛同样开始了对残酷人性的思索——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如此残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接受,面对强加的命运,个人除了无助,只能被迫接受。
这些早期的经历,统统被克里玛称为“童年”。这样的经历留给他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即使他成年以后,他仍然习惯在脸上盖着围巾睡觉,这是他在泰雷津集中营留下的习惯——在那里夜晚没有任何灯光。他还喜欢柔软的毛毯,这会让他觉得自己有了些许保护。
用手中的笔 写出“布拉格精神”
“生活如果不通过行动使之丰富,不以奋斗努力代替反省,它将会变成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捉摸,越来越富有敌意。它引起焦虑和衰竭。”——《布拉格精神》
在伊凡·克里玛77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一本有关于自己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他说,他这一生中总是做着同样一个梦,每隔几个星期,他就会梦到自己再次被捕,被囚禁,他习惯于在醒着的时候重温这种感觉。
“也许在我生命中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里,我并不自由”,克里玛回忆着自己的一生,回忆着那些充满牺牲和斗争的岁月。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他被制裁了21年——他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工作,同时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作。在21年间,克里玛的作品在捷克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但在这时,他从来没有失去自己自由的思想,他认为,这可以让他在写作时发现真理。
克里玛的小说往往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如何在逆境中正常地生活。克里玛的笔,能够与捷克人心绪相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作品试图表现的是一种“布拉格精神”。“(我们)生活在真实之中”,他说:“爱和背叛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人……贫困的现实生活放大了对浪漫的幻想。”
伊凡·克里玛
伊凡·克里玛,1931年9月14日出生于布拉格。因其祖辈的犹太血统,克里玛全家人于1941年被送入泰里茨集中营。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3年多时光,也初次尝试写作。1945年苏军解放集中营,克里玛及其家人均幸存。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和剧本。克里玛与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齐名,且因其“始终在场”,被捷克读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克里玛著有二十多部小说、戏剧、评论集。
数十年出自内心的创作
“他应当问问他们的,他很愿意问一问他们,然而他随即察觉到自己同他们之间有道无法逾越的界限,这界限由滑轨装置以及他的摄影机划出,像两道铁丝网围墙一样划清了界线。”——《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现如今,伊凡·克里玛居住在布拉格南部,一个茂密森林的边缘,他的两个孩子的家庭和他们家都在同一条道路上——1958年,克里玛迎娶了心理治疗师海伦娜,他们生了两个孩子迈克和汉娜,迈克是位报社编辑,汉娜是位艺术家。
在大多数的早晨里,克里玛会前往树林里采摘蘑菇。他的朋友菲利普·罗斯曾经这样描述他,“他有着‘披头士的发型’、‘肉食者的牙齿’,以及古斯塔尔·荣格的智商。”这样的描述再合适不过,虽然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但在某种意义上,克里玛依然非常固执。菲利普·罗斯说:“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每年春天都回去布拉格旅行,伊凡就是我的导游。他带我去街角的报刊亭,作家们在那里卖烟。他带我去出版社大楼,他们在那里拖地、铺砖、架设自来水管道,他们穿着工作服和靴子辛勤地工作着,他们的一个口袋里放着扳手,另外一个口袋里放着一本书……”
在克里玛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创作了三十余部作品,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本书都出自内心:诚实、无畏、浪漫,偶尔会尝试着摸索哲学。“我已经活得太久了,看到了太多的痛苦”,克里玛说:“……你能够找到自己的自由状态。你也许不能成为富人,你不能旅行,甚至可能不能前往匈牙利,但你可以创作。”
北京晨报记者 何安安 综合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