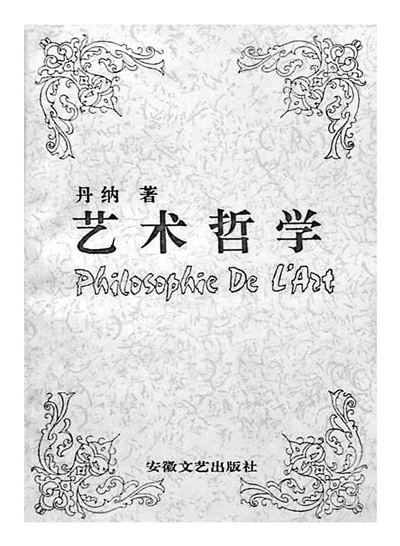用于艺术的科学方法总是层出不穷,都大大拓宽了人们看待艺术的视野,让经典作品显得更为有趣。各种理论互有批判也互有借鉴,“艺术哲学”从一家之言变成了百家争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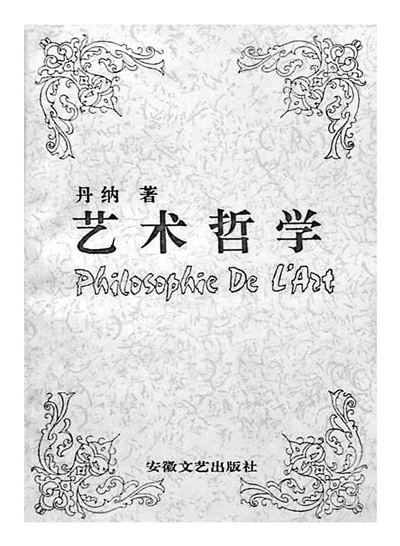
《艺术哲学》(法)丹纳著 傅雷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理科生关于文科生的诸多偏见之一就是,觉得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是杂学,是没有科学方法的学问。事实上,人文学科也是有系统性的研究方法的,只不过思维方式与理科大为不同。今天的人文学科遇到的一大挑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大有全面入侵之势,传统的思辨和经典阅读或许要让位于文献检索和数据分析,一切非理性的东西终将被理性收编,纳入绝对正确的解释系统。根据我的臆想,艺术风格、审美趣味变迁的终极规律终将被发现,想知道未来哪一年哪一种艺术风格最吃香、时尚界流行什么,都可以经由一套基于艺术科学原理的软件计算出来,那时候的艺术史家——或者叫艺术预言家——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已然泛滥成灾的艺术理论,会不会觉得都挺low的啊?
让艺术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野心,在19世纪的欧洲已经显露无遗了。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1828-1893)的《艺术哲学》一书可算是这种努力的经典代表。19世纪的欧洲人自认为引领着世界文明的潮流,倾向于认为科学理性无所不能,一切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丹纳提出,那些按照不同派别陈列在美术馆中的艺术品,就像标本室里的植物和博物馆里的动物一般,可以作为以科学方法观察的事实;人类精神的诸多面貌,好比是植物的多种形态,由是“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跟着目前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接近的潮流前进。精神科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与谨严的态度,就能有同样稳固的基础,同样的进步”。丹纳已经看到了在他之前的美学特别是德意志美学思想的缺陷,那就是总是从抽象的先验概念出发,执着于为“美”下定义,然后以之来评判各色各样的艺术现象。丹纳采用了相反的路径:从事实出发探求规律。这正是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也是法国人尤为擅长的治学方法。
植物的形态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因“水土异也”。在丹纳看来,艺术和植物一样,长成什么样子,取决于其所生长的环境,除此之外,决定艺术形态的还有种族和历史形势这两大因素。所以,对艺术的研究就意味着对艺术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考察艺术史就等于考察地理、风俗、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这就要求艺术研究者具备繁杂丰富的知识,要博览群书,最好还得实地考察——不是在美术馆里凝视大师名作,而是背起行囊,看山观水,记录一地的风土人情。
如此说来,艺术史家就要做一个旅行家了?丹纳自己就是个旅行达人,要是放在今天,他完全可以担纲制作最有水准的纪录片。《艺术哲学》的不少段落读来都有类似纪录片的范儿,如在专论尼德兰绘画时,作者会精心描绘这个地区的风光:“懒洋洋的大河,近海的地段有四里宽,睡在河床里像一条硕大无朋的鱼,腻答答的,扁扁的,颜色惨白,夹着黏土,带着鱼鳞的色调”,好比是将镜头对准一处风光来一段特写。当丹纳如此形象地、实证地描摹尼德兰风光时,我们仿佛就看到了尼德兰风景画,艺术与现实得以相互佐证。尽管也有抽象的论证,《艺术哲学》大半的章节是充满了画面感的,读来非常有趣,比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好懂多了。再比如他为了说明尼德兰绘画的特征而描绘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详尽描述他亲眼所见的日耳曼人的日常生活:“那边酒店林立,顾客盈门,无数的零售商出卖各种啤酒和烈性饮料,可见群众的嗜好。阿姆斯特丹有的是小铺子,摆着湛亮的酒桶,只看见人们把白的、黄的、绿的、棕色的酒精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酒里往往还加生姜和胡椒,增加刺激……”这样的文字,哪像艺术的“哲学”,分明就是游记。不过,丹纳绝不是在记流水账,他的一切描述都是为了说明主要问题,为了见出特定民族的艺术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如果说地理与民族性格是常量的话,他还引入历史这一关键变量,以此说明艺术风格的变迁。
“环境决定论”的确是很有说服力的说法,以之来看中国古代艺术的某些方面,似乎也能见出南北差异在艺术上的体现。不过,后世的艺术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与艺术作品绝不是简单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艺术家并不是机械地受其生活环境影响的,更有艺术家会反抗自己的环境乃至抗拒自己的民族、挑战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这在现代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艺术作品与其说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如说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当文明生活越来越富足、城市越来越整洁有序时,我们在艺术家的画面上看到的却往往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毫不安分守己的色彩、杂乱无章的线条。
我们在古典艺术中也能找出不符合“环境决定论”的例子来,比如西班牙画家牟里罗(1617-1682),看他画中以甜美少女形象显现的圣母、如沐圣光的世俗人物,似会觉得画家生活在一个欢乐祥和的年代,然而事实上,画家正是用这些令人忘忧的美好形象来掩盖社会现实或者说逃避现实——在他生活的年代,西班牙已经衰落了;在他生活的塞维利亚,这座曾经凭借来自殖民地的财富而奢华一时的城市,遍地是乞丐和流浪汉,太多的穷人吃不饱肚子、得不到救治,现实是悲哀惨淡的。
解读一件艺术作品,固然不能无视艺术作品所诞生的环境,但也应认识到,艺术作品不是植物,而是人的精神的产品,是灵动的、有太多的变量需要去考量的。人本就是一个不安于自身环境、时时想着去改变环境的动物,人的创造便也是捉摸不定、难以预料的。
在《艺术哲学》的译者序中,傅雷先生在肯定丹纳学说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丹纳在考察艺术时所揭露的时代与环境,只限于风俗人情、政治法律等,总之是一切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他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忽略了人类生活的最基本方面——经济生活,盖因他完全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基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这段话来看,傅雷先生应是在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提出这样的批判的。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艺术,的确可以进一步拓宽对艺术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在丹纳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分类和知识体系还不似今天这般发达,他在面对艺术作品诞生其中的社会现实时并没有多么先进的理论工具,只能或简或繁地叙写一个概貌。今天的艺术研究者可以把各种社科理论引入艺术研究,新阶级的出现如何体现在画作中、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艺术品如何成为可以议价的商品,等等,无不成为各种艺术理论,也就是说,各种艺术哲学的焦点。
另一方面,在丹纳之后,尤其是在德语国家,涌现出从艺术本身来看艺术的形式主义理论,如李格尔的“艺术意志”说、沃尔夫林的“视觉图式”与风格对比的方法,都执著于艺术形式本身,倾向于认为艺术有艺术自己的演化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全然由艺术以外的东西所决定的。这些理论就要比丹纳的《艺术哲学》更适用于艺术史学科的建设,因为当艺术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时,它需要专属于自己、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方法。在发挥想象、提炼概念并以这些概念为中心建构一套理论体系时,德语国家的学者就发挥出他们的优势了。
不管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还是从具体事实出发,科学方法必然意味着超越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得出一般规律。根据丹纳的艺术哲学观,每一个艺术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属于特定时代的本民族艺术家的群体,这个群体致力于表现民族的、时代的“主要特征”。这样说来,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就好比是在参加同一台大合唱,他们只是比其他的歌者唱得更响亮、更漂亮而已,所以才青史留名。可是细看这三位大师的画作,还是能见出他们各自的鲜明印记的,不论是笔法、气质还是主题的偏好,都各有不同。为了证明一个艺术理论的合理性,就必须牺牲掉艺术家的个性吗?艺术家们五味杂陈、各有不同的个人生活,难道就和他们各自的作品没有半点关系吗?丹纳之后,又有心理分析的方法被运用到艺术研究中来,艺术家个人回忆中的某个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就有可能成为解读他所偏爱的主题的关键。用于艺术的科学方法总是层出不穷,都大大拓宽了人们看待艺术的视野,让经典作品显得更为有趣。各种理论互有批判也互有借鉴,“艺术哲学”从一家之言变成了百家争鸣。
傅雷先生曾在更早的一篇《译者弁言》中谈到翻译此书的动机。他指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时为1929年),此书固然有种种缺陷,但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法,“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多是批判老祖宗、救国心切,引入西方科学方法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学术事业、培养国人的科学精神。傅雷与丹纳在文字上的相遇,真可谓是一件幸事。
用于艺术的科学方法总是层出不穷,都大大拓宽了人们看待艺术的视野,让经典作品显得更为有趣。各种理论互有批判也互有借鉴,“艺术哲学”从一家之言变成了百家争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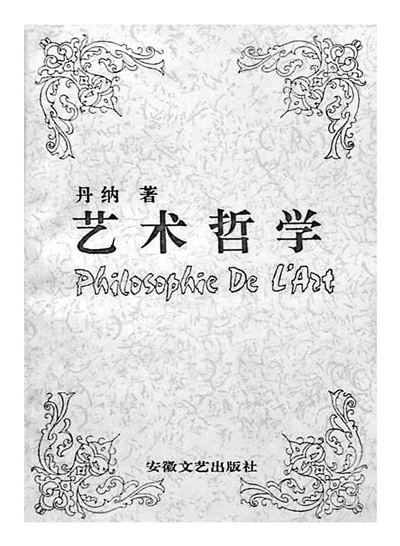
《艺术哲学》(法)丹纳著 傅雷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理科生关于文科生的诸多偏见之一就是,觉得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是杂学,是没有科学方法的学问。事实上,人文学科也是有系统性的研究方法的,只不过思维方式与理科大为不同。今天的人文学科遇到的一大挑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大有全面入侵之势,传统的思辨和经典阅读或许要让位于文献检索和数据分析,一切非理性的东西终将被理性收编,纳入绝对正确的解释系统。根据我的臆想,艺术风格、审美趣味变迁的终极规律终将被发现,想知道未来哪一年哪一种艺术风格最吃香、时尚界流行什么,都可以经由一套基于艺术科学原理的软件计算出来,那时候的艺术史家——或者叫艺术预言家——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已然泛滥成灾的艺术理论,会不会觉得都挺low的啊?
让艺术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野心,在19世纪的欧洲已经显露无遗了。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1828-1893)的《艺术哲学》一书可算是这种努力的经典代表。19世纪的欧洲人自认为引领着世界文明的潮流,倾向于认为科学理性无所不能,一切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丹纳提出,那些按照不同派别陈列在美术馆中的艺术品,就像标本室里的植物和博物馆里的动物一般,可以作为以科学方法观察的事实;人类精神的诸多面貌,好比是植物的多种形态,由是“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跟着目前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接近的潮流前进。精神科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与谨严的态度,就能有同样稳固的基础,同样的进步”。丹纳已经看到了在他之前的美学特别是德意志美学思想的缺陷,那就是总是从抽象的先验概念出发,执着于为“美”下定义,然后以之来评判各色各样的艺术现象。丹纳采用了相反的路径:从事实出发探求规律。这正是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也是法国人尤为擅长的治学方法。
植物的形态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因“水土异也”。在丹纳看来,艺术和植物一样,长成什么样子,取决于其所生长的环境,除此之外,决定艺术形态的还有种族和历史形势这两大因素。所以,对艺术的研究就意味着对艺术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考察艺术史就等于考察地理、风俗、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这就要求艺术研究者具备繁杂丰富的知识,要博览群书,最好还得实地考察——不是在美术馆里凝视大师名作,而是背起行囊,看山观水,记录一地的风土人情。
如此说来,艺术史家就要做一个旅行家了?丹纳自己就是个旅行达人,要是放在今天,他完全可以担纲制作最有水准的纪录片。《艺术哲学》的不少段落读来都有类似纪录片的范儿,如在专论尼德兰绘画时,作者会精心描绘这个地区的风光:“懒洋洋的大河,近海的地段有四里宽,睡在河床里像一条硕大无朋的鱼,腻答答的,扁扁的,颜色惨白,夹着黏土,带着鱼鳞的色调”,好比是将镜头对准一处风光来一段特写。当丹纳如此形象地、实证地描摹尼德兰风光时,我们仿佛就看到了尼德兰风景画,艺术与现实得以相互佐证。尽管也有抽象的论证,《艺术哲学》大半的章节是充满了画面感的,读来非常有趣,比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好懂多了。再比如他为了说明尼德兰绘画的特征而描绘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详尽描述他亲眼所见的日耳曼人的日常生活:“那边酒店林立,顾客盈门,无数的零售商出卖各种啤酒和烈性饮料,可见群众的嗜好。阿姆斯特丹有的是小铺子,摆着湛亮的酒桶,只看见人们把白的、黄的、绿的、棕色的酒精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酒里往往还加生姜和胡椒,增加刺激……”这样的文字,哪像艺术的“哲学”,分明就是游记。不过,丹纳绝不是在记流水账,他的一切描述都是为了说明主要问题,为了见出特定民族的艺术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如果说地理与民族性格是常量的话,他还引入历史这一关键变量,以此说明艺术风格的变迁。
“环境决定论”的确是很有说服力的说法,以之来看中国古代艺术的某些方面,似乎也能见出南北差异在艺术上的体现。不过,后世的艺术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与艺术作品绝不是简单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艺术家并不是机械地受其生活环境影响的,更有艺术家会反抗自己的环境乃至抗拒自己的民族、挑战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这在现代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艺术作品与其说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如说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当文明生活越来越富足、城市越来越整洁有序时,我们在艺术家的画面上看到的却往往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毫不安分守己的色彩、杂乱无章的线条。
我们在古典艺术中也能找出不符合“环境决定论”的例子来,比如西班牙画家牟里罗(1617-1682),看他画中以甜美少女形象显现的圣母、如沐圣光的世俗人物,似会觉得画家生活在一个欢乐祥和的年代,然而事实上,画家正是用这些令人忘忧的美好形象来掩盖社会现实或者说逃避现实——在他生活的年代,西班牙已经衰落了;在他生活的塞维利亚,这座曾经凭借来自殖民地的财富而奢华一时的城市,遍地是乞丐和流浪汉,太多的穷人吃不饱肚子、得不到救治,现实是悲哀惨淡的。
解读一件艺术作品,固然不能无视艺术作品所诞生的环境,但也应认识到,艺术作品不是植物,而是人的精神的产品,是灵动的、有太多的变量需要去考量的。人本就是一个不安于自身环境、时时想着去改变环境的动物,人的创造便也是捉摸不定、难以预料的。
在《艺术哲学》的译者序中,傅雷先生在肯定丹纳学说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丹纳在考察艺术时所揭露的时代与环境,只限于风俗人情、政治法律等,总之是一切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他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忽略了人类生活的最基本方面——经济生活,盖因他完全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基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这段话来看,傅雷先生应是在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提出这样的批判的。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艺术,的确可以进一步拓宽对艺术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在丹纳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分类和知识体系还不似今天这般发达,他在面对艺术作品诞生其中的社会现实时并没有多么先进的理论工具,只能或简或繁地叙写一个概貌。今天的艺术研究者可以把各种社科理论引入艺术研究,新阶级的出现如何体现在画作中、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艺术品如何成为可以议价的商品,等等,无不成为各种艺术理论,也就是说,各种艺术哲学的焦点。
另一方面,在丹纳之后,尤其是在德语国家,涌现出从艺术本身来看艺术的形式主义理论,如李格尔的“艺术意志”说、沃尔夫林的“视觉图式”与风格对比的方法,都执著于艺术形式本身,倾向于认为艺术有艺术自己的演化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全然由艺术以外的东西所决定的。这些理论就要比丹纳的《艺术哲学》更适用于艺术史学科的建设,因为当艺术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时,它需要专属于自己、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方法。在发挥想象、提炼概念并以这些概念为中心建构一套理论体系时,德语国家的学者就发挥出他们的优势了。
不管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还是从具体事实出发,科学方法必然意味着超越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得出一般规律。根据丹纳的艺术哲学观,每一个艺术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属于特定时代的本民族艺术家的群体,这个群体致力于表现民族的、时代的“主要特征”。这样说来,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就好比是在参加同一台大合唱,他们只是比其他的歌者唱得更响亮、更漂亮而已,所以才青史留名。可是细看这三位大师的画作,还是能见出他们各自的鲜明印记的,不论是笔法、气质还是主题的偏好,都各有不同。为了证明一个艺术理论的合理性,就必须牺牲掉艺术家的个性吗?艺术家们五味杂陈、各有不同的个人生活,难道就和他们各自的作品没有半点关系吗?丹纳之后,又有心理分析的方法被运用到艺术研究中来,艺术家个人回忆中的某个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就有可能成为解读他所偏爱的主题的关键。用于艺术的科学方法总是层出不穷,都大大拓宽了人们看待艺术的视野,让经典作品显得更为有趣。各种理论互有批判也互有借鉴,“艺术哲学”从一家之言变成了百家争鸣。
傅雷先生曾在更早的一篇《译者弁言》中谈到翻译此书的动机。他指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时为1929年),此书固然有种种缺陷,但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法,“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多是批判老祖宗、救国心切,引入西方科学方法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学术事业、培养国人的科学精神。傅雷与丹纳在文字上的相遇,真可谓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