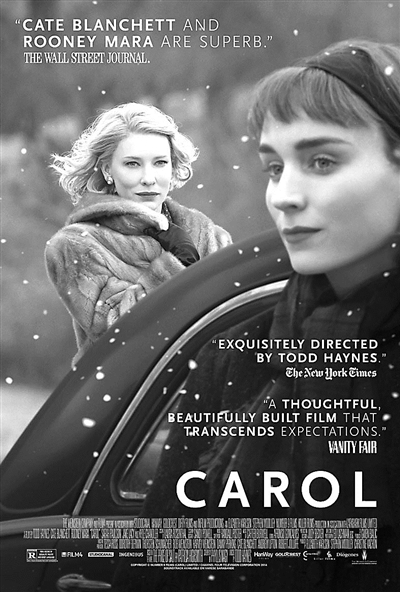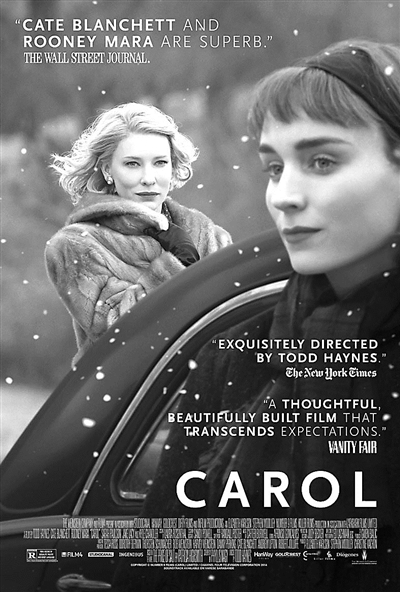
“女王”凯特·布兰切特和“龙文身女孩”鲁妮·玛拉在《卡罗尔》中扮演恋人,这样一对CP再加上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小说原著《盐的代价》珠玉在前,以及导演托德·海恩斯对“酷儿”电影的驾轻就熟,使该片成为68届戛纳电影节“零差评”电影,并斩获“酷儿”金棕榈奖。鲁妮·玛拉在片中安静内敛的表演风格,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初恋少女陷入爱情时的种种反应,摘得影后头衔。影片精致的画面、唯美的爱情、演员高超的演技也把影迷们瞬间“掰弯”。
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同性之爱是社会的“禁忌”,小说《盐的代价》中的“盐”指的就是同性之间的情欲。情欲如何突破“禁忌”的桎梏,实现自由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而在影片《卡罗尔》中则弱化了原著中的“禁忌”的成分,举重若轻地讲述热爱摄影的女售货员特瑞斯和中产阶级的成熟贵妇卡罗尔一见钟情,克服社会舆论压力、不同的阶层、年龄的差距等问题,“相遇”、“相爱”、“被迫分手”、“再次重逢”的过程。卡罗尔和特瑞斯成为现实中邂逅爱情的普通人,吃饭、旅行、书信往来等日常生活构成影片的主要内容;凝视、沉默、细部动作、身体触碰,营造唯美浪漫的恋爱情境。正如凯特·布兰切特所说:“《卡罗尔》真诚地表达了人们坠入爱河的感受,与取向无关。”
不同于《坏宝贝》、《来自远方》、《丹麦女孩》、《被拒人生》等同期“酷儿”电影中对非主流人群求子、生存、养老维权等群体问题的展现,《卡罗尔》更关注个人的成长。在认识卡罗尔之前,特瑞斯对自己的取向是茫然的,当经历了真正的爱情之后,她终于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真正渴望,并获得成长。卡罗尔在遇到特瑞斯之后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彻底撕破“伪装”,坚决离婚,直面自己。《卡罗尔》中的“成长”主题不仅体现在对性向的自我确认,还体现在两人作为一名普通个体参与社会劳动,在工作中寻找自我价值。
作为“酷儿”电影的杰出代表,托德·海恩斯一直关注和拍摄同性恋的生存现状。海恩斯的电影一向坚持形式主义的花哨,影像风格另类、新奇,经常混合多种叙事和剪辑手法。海恩斯在《卡罗尔》中遵循主流的影像表达,故事线索清晰,塑造了“凡人”之爱,简单单纯。影片没有《毒药》中对混乱、恐惧、暴力和受虐的迷恋和困扰;也不像《安然无恙》充满社会隐喻和政治寓言;卡罗尔和特瑞斯的爱情也不似《天鹅绒金矿》中布莱德和库尔特那般激进,而是在爆发和克制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海恩斯说:“《卡罗尔》想告诉我们的是,爱情这东西是如何让人茫然不知所措,陷入恋爱中的人,每个手势都被附加了期望与意义。”
《卡罗尔》被认为是海恩斯早年作品《远离天堂》的姐妹篇。两片在很多地方都很相像,都在探究二战后,少数派在社会中的压力;同样是女性题材,细腻而别致,对情感的表述非常入微;整体氛围华丽而复古,服饰场景都很精致。不同之处在于,《卡罗尔》的态度是开放的,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卡罗尔,还是平民阶层的特瑞斯;《远离天堂》中则是被隐藏的,法兰克面对自己的取向是羞愧、自责的,凯西也濒临崩溃。《卡罗尔》采取极简主义,主要人物只有卡罗尔和特瑞斯;《远离天堂》表现的人物更多,涵盖的社会问题更丰富,种族歧视、人性的虚伪和冷漠、社会的沉默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卡罗尔》的审美诉求,也是其被诟病的地方,如影片把卡罗尔和特瑞斯的爱情托举过高,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功能和意义,故事单薄。无论是卡罗尔的丈夫、特瑞斯的男友、暗恋特瑞斯的记者,还是跟踪她们的侦探,都是自私、冷酷和麻木的,卡罗尔和前女友的感情线索交代含混,特瑞斯和卡罗尔女儿也几乎没有交流,由人物构成的社会环境被过度的“凡人”爱情消解。影片对原著小说中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还原,仅停留在复古的街景、服饰、造型上,对外部世界的刻意忽略,造成该片与现实的咬合不紧密,或许是以电影为檄文的海恩斯在知天命之年,突然想为自己拍一部简单的纯爱电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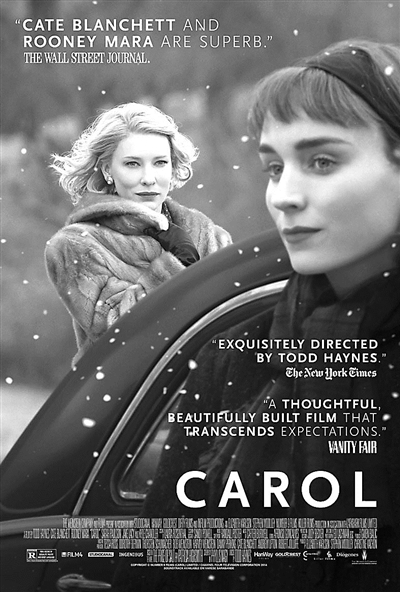
“女王”凯特·布兰切特和“龙文身女孩”鲁妮·玛拉在《卡罗尔》中扮演恋人,这样一对CP再加上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小说原著《盐的代价》珠玉在前,以及导演托德·海恩斯对“酷儿”电影的驾轻就熟,使该片成为68届戛纳电影节“零差评”电影,并斩获“酷儿”金棕榈奖。鲁妮·玛拉在片中安静内敛的表演风格,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初恋少女陷入爱情时的种种反应,摘得影后头衔。影片精致的画面、唯美的爱情、演员高超的演技也把影迷们瞬间“掰弯”。
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同性之爱是社会的“禁忌”,小说《盐的代价》中的“盐”指的就是同性之间的情欲。情欲如何突破“禁忌”的桎梏,实现自由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而在影片《卡罗尔》中则弱化了原著中的“禁忌”的成分,举重若轻地讲述热爱摄影的女售货员特瑞斯和中产阶级的成熟贵妇卡罗尔一见钟情,克服社会舆论压力、不同的阶层、年龄的差距等问题,“相遇”、“相爱”、“被迫分手”、“再次重逢”的过程。卡罗尔和特瑞斯成为现实中邂逅爱情的普通人,吃饭、旅行、书信往来等日常生活构成影片的主要内容;凝视、沉默、细部动作、身体触碰,营造唯美浪漫的恋爱情境。正如凯特·布兰切特所说:“《卡罗尔》真诚地表达了人们坠入爱河的感受,与取向无关。”
不同于《坏宝贝》、《来自远方》、《丹麦女孩》、《被拒人生》等同期“酷儿”电影中对非主流人群求子、生存、养老维权等群体问题的展现,《卡罗尔》更关注个人的成长。在认识卡罗尔之前,特瑞斯对自己的取向是茫然的,当经历了真正的爱情之后,她终于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真正渴望,并获得成长。卡罗尔在遇到特瑞斯之后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彻底撕破“伪装”,坚决离婚,直面自己。《卡罗尔》中的“成长”主题不仅体现在对性向的自我确认,还体现在两人作为一名普通个体参与社会劳动,在工作中寻找自我价值。
作为“酷儿”电影的杰出代表,托德·海恩斯一直关注和拍摄同性恋的生存现状。海恩斯的电影一向坚持形式主义的花哨,影像风格另类、新奇,经常混合多种叙事和剪辑手法。海恩斯在《卡罗尔》中遵循主流的影像表达,故事线索清晰,塑造了“凡人”之爱,简单单纯。影片没有《毒药》中对混乱、恐惧、暴力和受虐的迷恋和困扰;也不像《安然无恙》充满社会隐喻和政治寓言;卡罗尔和特瑞斯的爱情也不似《天鹅绒金矿》中布莱德和库尔特那般激进,而是在爆发和克制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海恩斯说:“《卡罗尔》想告诉我们的是,爱情这东西是如何让人茫然不知所措,陷入恋爱中的人,每个手势都被附加了期望与意义。”
《卡罗尔》被认为是海恩斯早年作品《远离天堂》的姐妹篇。两片在很多地方都很相像,都在探究二战后,少数派在社会中的压力;同样是女性题材,细腻而别致,对情感的表述非常入微;整体氛围华丽而复古,服饰场景都很精致。不同之处在于,《卡罗尔》的态度是开放的,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卡罗尔,还是平民阶层的特瑞斯;《远离天堂》中则是被隐藏的,法兰克面对自己的取向是羞愧、自责的,凯西也濒临崩溃。《卡罗尔》采取极简主义,主要人物只有卡罗尔和特瑞斯;《远离天堂》表现的人物更多,涵盖的社会问题更丰富,种族歧视、人性的虚伪和冷漠、社会的沉默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卡罗尔》的审美诉求,也是其被诟病的地方,如影片把卡罗尔和特瑞斯的爱情托举过高,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功能和意义,故事单薄。无论是卡罗尔的丈夫、特瑞斯的男友、暗恋特瑞斯的记者,还是跟踪她们的侦探,都是自私、冷酷和麻木的,卡罗尔和前女友的感情线索交代含混,特瑞斯和卡罗尔女儿也几乎没有交流,由人物构成的社会环境被过度的“凡人”爱情消解。影片对原著小说中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还原,仅停留在复古的街景、服饰、造型上,对外部世界的刻意忽略,造成该片与现实的咬合不紧密,或许是以电影为檄文的海恩斯在知天命之年,突然想为自己拍一部简单的纯爱电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