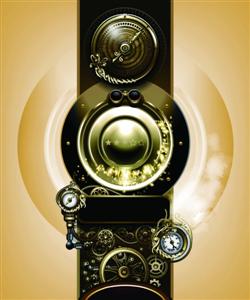电影《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刚刚上映,便成为一个热点文化事件。其全球票房已累计10.9亿美元,成为以最快速度突破10亿美元票房的影片。
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却在其新作《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中,将星战系列影片列为“没有思想的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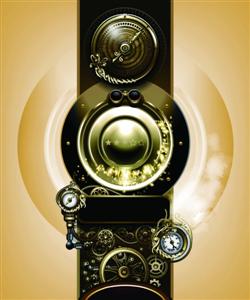
敢冒天下“星战迷”之大不韪的江晓原,在接受专访时强调: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看科幻电影,更多着迷于震撼的视觉效果,却没有看懂科幻作品背后蕴藏的深意。
看科幻电影,是需要懂些“正确姿势”的。
科幻不是“小儿科”
包括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在内的科幻作品的起源,有人认为可以一直追溯到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
1600年,开普勒出版《月亮之梦》一书,书中幻想人类与月亮人交往,涉及了很多当时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喷气推进、零重力状态、轨道惯性、宇宙服等。人们至今不明白,400年前的开普勒是根据什么想象出这些的。
到了19世纪,科幻作品主要以通俗小说为表现形式,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科幻小说的模样了。
很多人觉得彼时的国人缺乏想象力,在科幻作品创作方面应该比较“木讷”,但其实,清末的中国人并未错过那波刚刚涌现的热潮,也曾出现过一批本土科幻作家,但因为作品以模仿西方的居多,且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评判体系中,科幻显然是不入流的,所以这股风潮很快也就偃旗息鼓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幻作品。江晓原认为,把科幻作品等同于儿童文学是对科幻的第一重误解,而这个误解的形成,正与我们最初引进的作品类型有关。
如今六十来岁的人,不少人都在小时候读过法国科幻作家卢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凡尔纳的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科技的热烈呼唤,想象只要科技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除了中国,凡尔纳的作品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引进,因为它们符合当时这些国家所倡导的目标——发展科技。
科技要发展,未来才美好,用这样的逻辑编撰的故事,最适合用来教育孩子。因此,最初引进凡尔纳作品的多为少年儿童出版社这一类定位于青少年教育的出版社,科幻作品被深深地打上了“低幼”的烙印。
误解在科幻作品和成人之间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套莱姆作品集,莱姆是位极有思想深度的波兰科幻作家,他的代表作《索拉里斯星》和《完美的真空》 都非常棒,但这套书完全卖不动。经此失败,商务印书馆再也没有出过科幻作品。”
可选的出版社有限,逼得科幻作者们只能继续“混”少儿文学圈子。一次,一家少儿出版社要出一套 《中国科幻名家获奖佳作丛书》,其中也有刘慈欣的作品。出版社请江晓原写书评。江晓原申明:要么不写,要写就说真话。出版社表示,他们要的就是真话。结果,等看到江晓原发表的书评他们就傻眼了。原来江晓原在书评中说,作为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本就不应该出这套书:想想看,一个成年人在书店里拿起一本科幻小说,一看,封面印着“少年儿童出版社”,没准就又放下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科幻作品,有时对科幻作品和科幻作家是种伤害,会让大家继续误会下去,继续把科幻作品看作是少儿文学。”
科幻作家并非不知道这是种伤害,只是现实让他们别无选择。“但《三体》的火爆,让科幻作品有了走出 ‘低幼’的机会,要抓牢。”江晓原说。
那么,《三体》为什么会在成人世界走红,而没有被困在少儿文学里?对此,江晓原承认,《三体》 确实非常独特,完全是靠自身的强大魅力征服了成人世界,“但《三体》英文版在中国的首发式还是在一个童书展上搞的,刘慈欣还拿过儿童文学的奖项。”
错把科幻当科普
相比把科幻看作儿童文学,把科幻当成科普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隐秘的误解,“尤其是当成科普的一种低幼形式,想象出一个科技发展的美好故事来哄孩子”。
科普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一种公众易于理解、接受的浅显方式,向普通大众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技术的应用,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科幻的定义则众说纷纭,认可度较高的一种定义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技术的远景或对人类的影响。
对比两个定义可以看出,科普是让大众了解真实的科技进展,科幻描摹的则是未来,着重讨论的是未来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可是,虽然定义明确,混淆科幻和科普的现象却十分普遍。不仅是人们谈论科幻时这么想,甚至是有些科幻作品创作者本人,也认为自己是在做科普工作。
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确实有一些科幻作品中含有科普的成分,“比如《小灵通漫游未来》 之类的作品,拿来给孩子读未尝不可,但很多深具思想性的科幻作品,比如《2001太空漫游》,并不适合当做科普作品提供给孩子,因为别说是孩子,成人也未必看得懂。”江晓原说。
江晓原认为,把科幻当成科普的一部分,是一种自我矮化,“科幻做的事情远比科普深刻得多,国际上当红的科幻作家,都不认可自己写的是科普作品。比如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他面对媒体时,强调自己写的是哲学小说,他甚至连‘科幻’两字都不接受,更别提科普了。”
阿西莫夫原是美国的科幻大家,为响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号召,他从科幻创作改为科普创作,但晚年架不住粉丝们的“死缠烂打”,还是回到了他的《基地》系列科幻创作上。这一去一回说明,在阿西莫夫的心里,科幻和科普是泾渭分明的。
尽管如此,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误解还是时常发生。2010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谈到电影中的科学时显得十分愤慨:“所有的科学技术都臣服在好莱坞脚下。”文章认为,“电影通常都是在歪曲科学本身。龙卷风、火山、太空飞船、病毒等等,服从的都是好莱坞的规则,而不是牛顿和达尔文的规则”。文章还认为,“电影中描绘的研究者和现实实验室中的研究者很少有共同之处。银幕上的一些科学家要么是被英雄打败的恶棍,要么因与众不同的鲁莽而具有威胁性,还有一些则是独自一人在深山老林中寻找治癌方法的异类”。
文章所归纳的好莱坞影片中的科学家形象,倒是相当符合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一般情形。但其实,电影人和科学家本来就是“同床异梦”。科学家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电影来宣传科学,而电影人却总是将科学当作可利用的资源,就像利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军事等资源一样。电影人追逐的是奥斯卡小金人,而不会对诺贝尔奖存有幻想。
在电影中的科学知识是否必须准确的问题上,科学家和电影人闹得不可开交。许多科学家认为:当然必须准确。一般公众也都支持这个意见。但为什么我们能容忍很多影视作品对历史的“戏说”,却不能接受科幻电影“戏说”科学呢?仔细想来,这种愤慨的背后,其实隐含的还是把科幻当科普的误解,因此而不能接受对科学的超现实幻想。
为何没有光明的尾巴
消弭误解才能真正读懂、看懂科幻作品。
江晓原认为,讨论科学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警示科技过度发展可能带来的灾难,才是科幻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读”懂作品隐含的寓意,才是观看科幻电影的“正确姿势”。
事实上,从19世纪末开始,以英国人威尔斯的一系列科幻小说为标志,科幻作品中的人类未来就不再是美好的了。而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里,未来世界几乎没有光明,而是充斥着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和大瘟疫,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主题:资源耗竭、惊天浩劫和高度专制。威尔斯抛弃了凡尔纳所持的简单、乐观的科技无限发展论,而是警示人们,科技过度发展可能会带来荒谬的结果,启发人们讨论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伦理问题。
虽然威尔斯是反思科学传统的开创者,但其实之前也已经有人开始进行了类似的反思,只是未能在当时的社会引起足够的警觉。那就是被称为现代科幻鼻祖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拍成电影,即为不少人所熟知的《科学怪人》。作品中被造出来的科学怪人,对自己的创造者是怨恨的,因为他始终无法确认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被创造的生物对造物主的怨恨、不信任和恐惧,是科幻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反复出现在后来的科幻作品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思,与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的单向发展观念有关。人们认为,社会总是无限往前发展的,而只要往前发展便是好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多辉煌成就,这更使人们相信,自然科学法则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但事实上,历史并不完全支持这个信念,有时,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却是文明的倒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科技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真的就全然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很多问题,是有待商榷的。
“实际上,很多不好的东西也是科技带来的,至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科技无限发展下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人类以这种思路设计未来,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江晓原说。
100多年里,大量的科幻作品都没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并非偶然。因为,悲观的态度和立场,更有助于产生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这些年来,我看了上千部西方科幻电影,也读了不少科幻小说,竟没有一部是有着光明未来的。结尾处,当然会伸张正义,惩罚邪恶,但编剧和导演从来不向观众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么多的编剧和导演,来自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的高度一致,这对于崇尚多元化的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奇怪现象。”江晓原说。
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物质生活,确实是依靠科技的发展获得的。但科技的发展是有加速度的——它会发展得越来越快,就像电影《雪国列车》中的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而我们就乘坐在上面。
“刚开始,我们确实快活得如同《泰坦尼克号》中那对在船头迎风展臂的青年男女。但我们逐渐发现,对于这列列车的车速和行驶方向,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我们既不知列车将驶向何方,也不知列车由谁在操控。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列车正在越开越快。此时,作为车上的一员,你难道不想知道自己正在驶向何方?难道不担心车开太快会出事?”
影片中的雪国列车只是不停地向前行驶,不能给出答案。
如果说雪国列车是对当代科技发展的隐喻,那么影片结局时列车的颠覆毁灭,简直就是对如今这种过度依赖科技支撑的现代化之不可持续性的明喻了。
对人性“严刑逼供”
相比《星球大战》系列,江晓原显然更欣赏《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是一部经典的科幻电影,但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激烈的打斗、酷炫的特技。实际上,这部电影是极度反对科学的盲目发展的,它的思想深度引得西方哲学家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和讨论。”
江晓原看《黑客帝国》不下5遍,而且每看一遍都是三部连看。他琢磨每一句台词,又怕中文翻译得不够准确而去看原版英文字幕。每看完一遍,他都会写下自己的观感,下一次看片的时候,再翻看上一次的观感,对比自己的感受是否有所改变。“《黑客帝国》启示人们:外部世界真实吗?看完影片,人们可能会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
为什么一部好的科幻作品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魅力就在于作品设置的突破常人想象的情境。有许多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是不会被思考的,或者是无法展开思考的,如果硬要去思考,也会显得很荒谬,显得不正常。但科幻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逼迫人们在它所设置的极端情境下进行深度思考。在这个虚拟的语境中,我们演绎、展开那些平日无法进行的思考,就不显得荒谬、不正常了。
数学上有“归谬”、“反证”等论证方法,科幻作品便相当于人们思考未来的归谬法和反证法:科幻作品将某种技术的应用推展或夸张到极致,由此来提出问题,或给出创作者自己的思考。比如机器人日见发达,《机械公敌》《黑客帝国》等作品就引导出机器人会不会、能不能统治人类这样的问题。
我们平日里对人性的拷问,都是针对已经发生的、受到现有社会结构制约的事物,拷问力度未免有限,充其量是一种“盘问”,而科幻作品中对人性的拷问,有可能达到“严刑逼供”的力度。刘慈欣把这称之为“思想实验”,就是从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所不具备的视角来看人性。
当然,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学者,不需要这些假设的情境,就能自觉地思考一些高度抽象的问题,比如史蒂芬·霍金。他在思考,时空旅行是否可能?人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是否可以改变历史?但是,这些学者的思考,如果要想让广大公众接触或理解,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让一部优秀的科幻电影将它们表现出来。而这就需要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构成一个语境,使得那些思考在这个虚拟的语境中得以展开,可以顺利进行。
可是,既不是科学工作者也不是科学政策决策者的普通人,有反思科学的必要吗?
江晓原认为,不要以为科技跟普通人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
从小的方面来说,很多现代科技都跟我们有利害关系。比如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要不要吃?人们有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普通人是不懂的,也不需要懂,只要听专家的话就行了,只有专家有资格发表意见。“那么,谁是专家?专家由谁来认定?专家背后站着谁?”
转基因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诸如克隆人、智能机器人等,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经济、安全、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对科技抱有戒心,每当争议出现时,要关注它的利益维度,不要听任某些人把事情简化为科学问题,而不问一问这个事情背后的利益格局是怎样的。”江晓原提醒。
其他类型的电影,如言情、战争、匪警、动作等,难道就没有这个功能吗?
回答是:它们绝大部分没有这个功能。
道理很简单:一旦它们的故事涉及对科学的思考,它们就是科幻电影了。对公众来说,有什么途径能够接触到反思科学的东西?几乎没有。一般都是纯学术的讨论,不会进入公众层面。要想让公众接触到反思科学的东西,科幻差不多是唯一的途径。
这个途径相当珍贵,但当我们把科幻看成是科普和少儿文学的时候,自然就把这一点“阉割”掉了。“在那些把科幻作品当成科普和少儿文学的人眼里,《黑客帝国》是不值得看的,整部片子充斥着暴力,有什么看头?”
在江晓原看来,科幻作品中所表达的,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作品无疑是当代科学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似乎也只有科幻在承担着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电影《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刚刚上映,便成为一个热点文化事件。其全球票房已累计10.9亿美元,成为以最快速度突破10亿美元票房的影片。
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却在其新作《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中,将星战系列影片列为“没有思想的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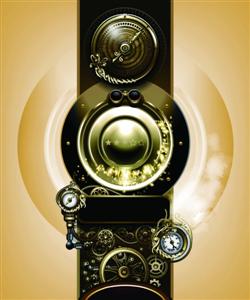
敢冒天下“星战迷”之大不韪的江晓原,在接受专访时强调: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看科幻电影,更多着迷于震撼的视觉效果,却没有看懂科幻作品背后蕴藏的深意。
看科幻电影,是需要懂些“正确姿势”的。
科幻不是“小儿科”
包括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在内的科幻作品的起源,有人认为可以一直追溯到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
1600年,开普勒出版《月亮之梦》一书,书中幻想人类与月亮人交往,涉及了很多当时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喷气推进、零重力状态、轨道惯性、宇宙服等。人们至今不明白,400年前的开普勒是根据什么想象出这些的。
到了19世纪,科幻作品主要以通俗小说为表现形式,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科幻小说的模样了。
很多人觉得彼时的国人缺乏想象力,在科幻作品创作方面应该比较“木讷”,但其实,清末的中国人并未错过那波刚刚涌现的热潮,也曾出现过一批本土科幻作家,但因为作品以模仿西方的居多,且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评判体系中,科幻显然是不入流的,所以这股风潮很快也就偃旗息鼓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幻作品。江晓原认为,把科幻作品等同于儿童文学是对科幻的第一重误解,而这个误解的形成,正与我们最初引进的作品类型有关。
如今六十来岁的人,不少人都在小时候读过法国科幻作家卢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凡尔纳的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科技的热烈呼唤,想象只要科技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除了中国,凡尔纳的作品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引进,因为它们符合当时这些国家所倡导的目标——发展科技。
科技要发展,未来才美好,用这样的逻辑编撰的故事,最适合用来教育孩子。因此,最初引进凡尔纳作品的多为少年儿童出版社这一类定位于青少年教育的出版社,科幻作品被深深地打上了“低幼”的烙印。
误解在科幻作品和成人之间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套莱姆作品集,莱姆是位极有思想深度的波兰科幻作家,他的代表作《索拉里斯星》和《完美的真空》 都非常棒,但这套书完全卖不动。经此失败,商务印书馆再也没有出过科幻作品。”
可选的出版社有限,逼得科幻作者们只能继续“混”少儿文学圈子。一次,一家少儿出版社要出一套 《中国科幻名家获奖佳作丛书》,其中也有刘慈欣的作品。出版社请江晓原写书评。江晓原申明:要么不写,要写就说真话。出版社表示,他们要的就是真话。结果,等看到江晓原发表的书评他们就傻眼了。原来江晓原在书评中说,作为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本就不应该出这套书:想想看,一个成年人在书店里拿起一本科幻小说,一看,封面印着“少年儿童出版社”,没准就又放下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科幻作品,有时对科幻作品和科幻作家是种伤害,会让大家继续误会下去,继续把科幻作品看作是少儿文学。”
科幻作家并非不知道这是种伤害,只是现实让他们别无选择。“但《三体》的火爆,让科幻作品有了走出 ‘低幼’的机会,要抓牢。”江晓原说。
那么,《三体》为什么会在成人世界走红,而没有被困在少儿文学里?对此,江晓原承认,《三体》 确实非常独特,完全是靠自身的强大魅力征服了成人世界,“但《三体》英文版在中国的首发式还是在一个童书展上搞的,刘慈欣还拿过儿童文学的奖项。”
错把科幻当科普
相比把科幻看作儿童文学,把科幻当成科普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隐秘的误解,“尤其是当成科普的一种低幼形式,想象出一个科技发展的美好故事来哄孩子”。
科普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一种公众易于理解、接受的浅显方式,向普通大众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技术的应用,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科幻的定义则众说纷纭,认可度较高的一种定义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技术的远景或对人类的影响。
对比两个定义可以看出,科普是让大众了解真实的科技进展,科幻描摹的则是未来,着重讨论的是未来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可是,虽然定义明确,混淆科幻和科普的现象却十分普遍。不仅是人们谈论科幻时这么想,甚至是有些科幻作品创作者本人,也认为自己是在做科普工作。
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确实有一些科幻作品中含有科普的成分,“比如《小灵通漫游未来》 之类的作品,拿来给孩子读未尝不可,但很多深具思想性的科幻作品,比如《2001太空漫游》,并不适合当做科普作品提供给孩子,因为别说是孩子,成人也未必看得懂。”江晓原说。
江晓原认为,把科幻当成科普的一部分,是一种自我矮化,“科幻做的事情远比科普深刻得多,国际上当红的科幻作家,都不认可自己写的是科普作品。比如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他面对媒体时,强调自己写的是哲学小说,他甚至连‘科幻’两字都不接受,更别提科普了。”
阿西莫夫原是美国的科幻大家,为响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号召,他从科幻创作改为科普创作,但晚年架不住粉丝们的“死缠烂打”,还是回到了他的《基地》系列科幻创作上。这一去一回说明,在阿西莫夫的心里,科幻和科普是泾渭分明的。
尽管如此,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误解还是时常发生。2010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谈到电影中的科学时显得十分愤慨:“所有的科学技术都臣服在好莱坞脚下。”文章认为,“电影通常都是在歪曲科学本身。龙卷风、火山、太空飞船、病毒等等,服从的都是好莱坞的规则,而不是牛顿和达尔文的规则”。文章还认为,“电影中描绘的研究者和现实实验室中的研究者很少有共同之处。银幕上的一些科学家要么是被英雄打败的恶棍,要么因与众不同的鲁莽而具有威胁性,还有一些则是独自一人在深山老林中寻找治癌方法的异类”。
文章所归纳的好莱坞影片中的科学家形象,倒是相当符合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一般情形。但其实,电影人和科学家本来就是“同床异梦”。科学家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电影来宣传科学,而电影人却总是将科学当作可利用的资源,就像利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军事等资源一样。电影人追逐的是奥斯卡小金人,而不会对诺贝尔奖存有幻想。
在电影中的科学知识是否必须准确的问题上,科学家和电影人闹得不可开交。许多科学家认为:当然必须准确。一般公众也都支持这个意见。但为什么我们能容忍很多影视作品对历史的“戏说”,却不能接受科幻电影“戏说”科学呢?仔细想来,这种愤慨的背后,其实隐含的还是把科幻当科普的误解,因此而不能接受对科学的超现实幻想。
为何没有光明的尾巴
消弭误解才能真正读懂、看懂科幻作品。
江晓原认为,讨论科学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警示科技过度发展可能带来的灾难,才是科幻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读”懂作品隐含的寓意,才是观看科幻电影的“正确姿势”。
事实上,从19世纪末开始,以英国人威尔斯的一系列科幻小说为标志,科幻作品中的人类未来就不再是美好的了。而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里,未来世界几乎没有光明,而是充斥着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和大瘟疫,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主题:资源耗竭、惊天浩劫和高度专制。威尔斯抛弃了凡尔纳所持的简单、乐观的科技无限发展论,而是警示人们,科技过度发展可能会带来荒谬的结果,启发人们讨论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伦理问题。
虽然威尔斯是反思科学传统的开创者,但其实之前也已经有人开始进行了类似的反思,只是未能在当时的社会引起足够的警觉。那就是被称为现代科幻鼻祖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拍成电影,即为不少人所熟知的《科学怪人》。作品中被造出来的科学怪人,对自己的创造者是怨恨的,因为他始终无法确认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被创造的生物对造物主的怨恨、不信任和恐惧,是科幻作品永恒的主题之一,反复出现在后来的科幻作品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思,与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的单向发展观念有关。人们认为,社会总是无限往前发展的,而只要往前发展便是好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多辉煌成就,这更使人们相信,自然科学法则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但事实上,历史并不完全支持这个信念,有时,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却是文明的倒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科技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真的就全然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很多问题,是有待商榷的。
“实际上,很多不好的东西也是科技带来的,至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科技无限发展下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人类以这种思路设计未来,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江晓原说。
100多年里,大量的科幻作品都没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并非偶然。因为,悲观的态度和立场,更有助于产生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这些年来,我看了上千部西方科幻电影,也读了不少科幻小说,竟没有一部是有着光明未来的。结尾处,当然会伸张正义,惩罚邪恶,但编剧和导演从来不向观众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么多的编剧和导演,来自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的高度一致,这对于崇尚多元化的西方文化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奇怪现象。”江晓原说。
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物质生活,确实是依靠科技的发展获得的。但科技的发展是有加速度的——它会发展得越来越快,就像电影《雪国列车》中的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而我们就乘坐在上面。
“刚开始,我们确实快活得如同《泰坦尼克号》中那对在船头迎风展臂的青年男女。但我们逐渐发现,对于这列列车的车速和行驶方向,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我们既不知列车将驶向何方,也不知列车由谁在操控。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列车正在越开越快。此时,作为车上的一员,你难道不想知道自己正在驶向何方?难道不担心车开太快会出事?”
影片中的雪国列车只是不停地向前行驶,不能给出答案。
如果说雪国列车是对当代科技发展的隐喻,那么影片结局时列车的颠覆毁灭,简直就是对如今这种过度依赖科技支撑的现代化之不可持续性的明喻了。
对人性“严刑逼供”
相比《星球大战》系列,江晓原显然更欣赏《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是一部经典的科幻电影,但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激烈的打斗、酷炫的特技。实际上,这部电影是极度反对科学的盲目发展的,它的思想深度引得西方哲学家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和讨论。”
江晓原看《黑客帝国》不下5遍,而且每看一遍都是三部连看。他琢磨每一句台词,又怕中文翻译得不够准确而去看原版英文字幕。每看完一遍,他都会写下自己的观感,下一次看片的时候,再翻看上一次的观感,对比自己的感受是否有所改变。“《黑客帝国》启示人们:外部世界真实吗?看完影片,人们可能会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
为什么一部好的科幻作品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魅力就在于作品设置的突破常人想象的情境。有许多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是不会被思考的,或者是无法展开思考的,如果硬要去思考,也会显得很荒谬,显得不正常。但科幻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逼迫人们在它所设置的极端情境下进行深度思考。在这个虚拟的语境中,我们演绎、展开那些平日无法进行的思考,就不显得荒谬、不正常了。
数学上有“归谬”、“反证”等论证方法,科幻作品便相当于人们思考未来的归谬法和反证法:科幻作品将某种技术的应用推展或夸张到极致,由此来提出问题,或给出创作者自己的思考。比如机器人日见发达,《机械公敌》《黑客帝国》等作品就引导出机器人会不会、能不能统治人类这样的问题。
我们平日里对人性的拷问,都是针对已经发生的、受到现有社会结构制约的事物,拷问力度未免有限,充其量是一种“盘问”,而科幻作品中对人性的拷问,有可能达到“严刑逼供”的力度。刘慈欣把这称之为“思想实验”,就是从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所不具备的视角来看人性。
当然,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学者,不需要这些假设的情境,就能自觉地思考一些高度抽象的问题,比如史蒂芬·霍金。他在思考,时空旅行是否可能?人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是否可以改变历史?但是,这些学者的思考,如果要想让广大公众接触或理解,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让一部优秀的科幻电影将它们表现出来。而这就需要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构成一个语境,使得那些思考在这个虚拟的语境中得以展开,可以顺利进行。
可是,既不是科学工作者也不是科学政策决策者的普通人,有反思科学的必要吗?
江晓原认为,不要以为科技跟普通人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
从小的方面来说,很多现代科技都跟我们有利害关系。比如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要不要吃?人们有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普通人是不懂的,也不需要懂,只要听专家的话就行了,只有专家有资格发表意见。“那么,谁是专家?专家由谁来认定?专家背后站着谁?”
转基因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诸如克隆人、智能机器人等,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经济、安全、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对科技抱有戒心,每当争议出现时,要关注它的利益维度,不要听任某些人把事情简化为科学问题,而不问一问这个事情背后的利益格局是怎样的。”江晓原提醒。
其他类型的电影,如言情、战争、匪警、动作等,难道就没有这个功能吗?
回答是:它们绝大部分没有这个功能。
道理很简单:一旦它们的故事涉及对科学的思考,它们就是科幻电影了。对公众来说,有什么途径能够接触到反思科学的东西?几乎没有。一般都是纯学术的讨论,不会进入公众层面。要想让公众接触到反思科学的东西,科幻差不多是唯一的途径。
这个途径相当珍贵,但当我们把科幻看成是科普和少儿文学的时候,自然就把这一点“阉割”掉了。“在那些把科幻作品当成科普和少儿文学的人眼里,《黑客帝国》是不值得看的,整部片子充斥着暴力,有什么看头?”
在江晓原看来,科幻作品中所表达的,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作品无疑是当代科学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似乎也只有科幻在承担着这方面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