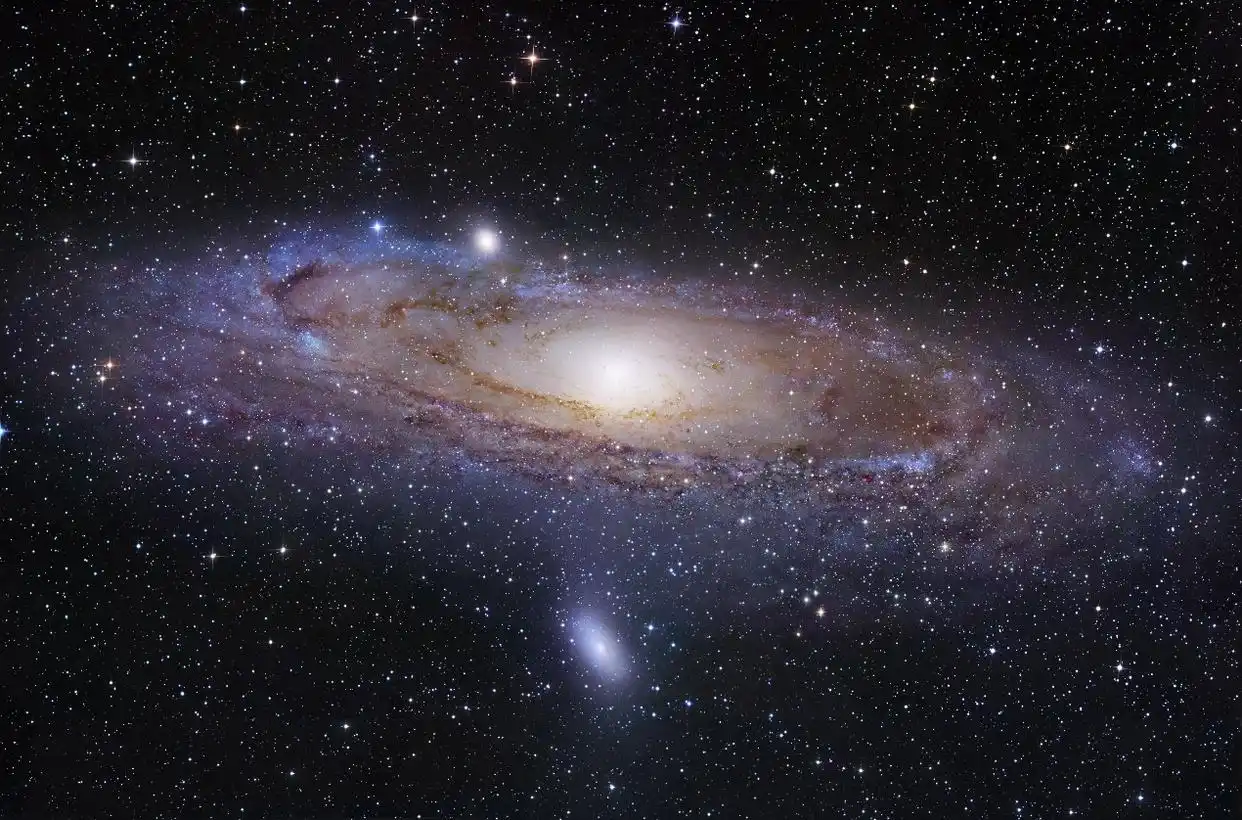三 学诗漫有惊人句
张恨水爱书、淘书,也不尽是“小说史”的材料,就书而言,他也喜欢诗词韵文。尤其醉心于古典词章。这个嗜好可谓伴随他一生。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中写道,最初,他是热衷于读小说的,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然而,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 那时,他读小说,所欣赏的,往往是其中的诗词。比如《花月痕》,他认为,魏子安诗、词均好,小说却非所长。所以他说:“《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陆续的,他还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响甚大,以至于他看曹雪芹的诗,竟一无是处,认为“曹雪芹诗格不高,高兰墅诗格亦极平凡,故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一超凡脱俗之句”。他喜欢以诗抒怀, 而作诗也的确给他带来许多快乐。他尤其享受朋友之间诗词唱和的快乐。当年,张楚萍、郝耕仁、张东野等老朋友,都是他的诗友,据他回忆,在与郝耕仁一起出游时,“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 后来,他到北京,结识成舍我,也是一首《念奴娇》做了牵线的“红娘”。张伍讲过一个张恨水与成舍我赋诗联句的故事,亦是一则文坛佳话,他写道:
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抒怀”中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诗曰:
碧天迢递夜方长,(杨) 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定后,(舒) 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 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 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 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 西风落木为诗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 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 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 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 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莫谈天下事,(杨) 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 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富于诗情与才思敏捷。他解释自己喜欢诗的原因:“我想,诗之为物,抒发自己的心情,是最好的工具;而感人之深,更是他物所不能及。” 多年后,忆及自己学诗的经历,他还表示:“我是十一二岁,就学这劳什子。我二十年来,除了为它废时失业而外,又是没有得一文好处。可是,我至今还爱它。遇到月明之夜,在月光下就哼哼唧唧,‘今夜月明人尽望’,遇到春天花红柳绿,在东风下,又哼哼唧唧,‘春城无处不飞花’了。” 刚来北京时,他兼几份工作,很辛苦,但工作之余,读书的热情丝毫未减。他曾写道:“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大全》。每日从秦墨哂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阕。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并不认为“旧诗”有什么不好,他宣称自己是“旧诗旗帜下的一个信徒” 时,一直都很坦然。当初,新文学家“颇以旧诗人之颓废,詈为无病而呻”,对此,他亦不以为然。一次,他借梁任公的诗“生平不作呻吟语”而加以发挥,认为:“虽胸襟不凡,然就诗言之,殊属矫枉过正。盖无病而呻,自属不可,有病而不呻,非人情也,亦非诗情也。” 那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为旧诗,乃至为古典文化辩护。他认为,旧诗的价值,至少“有令人记诵的魔力,不像新诗会受人家的厌弃”。他说,“设若任取一本旧诗给人看,除非那人根本上不爱诗便了,否则他决不能说看了头痛。”他还谈到自己昔日读旧诗的体会:“旧诗的近体,诚然是有些束缚人的(但是作家功夫到家,也不受它的束缚),古体却不如此。读者若是偶然肯翻一翻唐诗,念一念《将进酒》、《高轩过》、《蜀道难》,那样才气纵横的文字,你才知道旧诗一点不会束缚人。”
有人指责文人的吟风弄月对“亡国”负有责任,他则针锋相对,写了《吟风弄月罢》一文,其中写道:
有人说:中国文学是颓废的,不是振作的,应当洗刷一下。因为这样的文学,和民气大有关系的。这话谁不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是受了压迫,所谓不敢言而怒,文人没有法子去作激昂慷慨文字的,并不是不作。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一腔热血,托之芳草美人,隐隐约约地说出来。一部《诗经》,一部《楚辞》,不大半是如此吗?
直到中年以后,张恨水再谈“旧诗”,态度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编《剪愁集》,所作序言便颇多含糊模棱之语。诗集既名以“剪愁”,顾名思义,是要剪除故态也。但又表示,文人积习既难忘,其环境,“亦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而且,“予遭遇坎坷,每多难言之隐,更得机会,辄一触而发,因是淡月纱窗,西风庭院,负手微吟,颇亦成章”。 其纠结如此,怕是内心冲突的自然流露吧。
数年之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更含蓄地谈到,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还“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 的。这怕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三四十年代已被建构为绝对正确的历史性话语,并被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内化为评判自身行为的标准,身在其中的张恨水,固不能不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
三 学诗漫有惊人句
张恨水爱书、淘书,也不尽是“小说史”的材料,就书而言,他也喜欢诗词韵文。尤其醉心于古典词章。这个嗜好可谓伴随他一生。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中写道,最初,他是热衷于读小说的,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然而,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 那时,他读小说,所欣赏的,往往是其中的诗词。比如《花月痕》,他认为,魏子安诗、词均好,小说却非所长。所以他说:“《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陆续的,他还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响甚大,以至于他看曹雪芹的诗,竟一无是处,认为“曹雪芹诗格不高,高兰墅诗格亦极平凡,故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一超凡脱俗之句”。他喜欢以诗抒怀, 而作诗也的确给他带来许多快乐。他尤其享受朋友之间诗词唱和的快乐。当年,张楚萍、郝耕仁、张东野等老朋友,都是他的诗友,据他回忆,在与郝耕仁一起出游时,“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 后来,他到北京,结识成舍我,也是一首《念奴娇》做了牵线的“红娘”。张伍讲过一个张恨水与成舍我赋诗联句的故事,亦是一则文坛佳话,他写道:
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抒怀”中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诗曰:
碧天迢递夜方长,(杨) 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定后,(舒) 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 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 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 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 西风落木为诗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 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 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 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 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莫谈天下事,(杨) 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 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富于诗情与才思敏捷。他解释自己喜欢诗的原因:“我想,诗之为物,抒发自己的心情,是最好的工具;而感人之深,更是他物所不能及。” 多年后,忆及自己学诗的经历,他还表示:“我是十一二岁,就学这劳什子。我二十年来,除了为它废时失业而外,又是没有得一文好处。可是,我至今还爱它。遇到月明之夜,在月光下就哼哼唧唧,‘今夜月明人尽望’,遇到春天花红柳绿,在东风下,又哼哼唧唧,‘春城无处不飞花’了。” 刚来北京时,他兼几份工作,很辛苦,但工作之余,读书的热情丝毫未减。他曾写道:“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大全》。每日从秦墨哂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阕。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并不认为“旧诗”有什么不好,他宣称自己是“旧诗旗帜下的一个信徒” 时,一直都很坦然。当初,新文学家“颇以旧诗人之颓废,詈为无病而呻”,对此,他亦不以为然。一次,他借梁任公的诗“生平不作呻吟语”而加以发挥,认为:“虽胸襟不凡,然就诗言之,殊属矫枉过正。盖无病而呻,自属不可,有病而不呻,非人情也,亦非诗情也。” 那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为旧诗,乃至为古典文化辩护。他认为,旧诗的价值,至少“有令人记诵的魔力,不像新诗会受人家的厌弃”。他说,“设若任取一本旧诗给人看,除非那人根本上不爱诗便了,否则他决不能说看了头痛。”他还谈到自己昔日读旧诗的体会:“旧诗的近体,诚然是有些束缚人的(但是作家功夫到家,也不受它的束缚),古体却不如此。读者若是偶然肯翻一翻唐诗,念一念《将进酒》、《高轩过》、《蜀道难》,那样才气纵横的文字,你才知道旧诗一点不会束缚人。”
有人指责文人的吟风弄月对“亡国”负有责任,他则针锋相对,写了《吟风弄月罢》一文,其中写道:
有人说:中国文学是颓废的,不是振作的,应当洗刷一下。因为这样的文学,和民气大有关系的。这话谁不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是受了压迫,所谓不敢言而怒,文人没有法子去作激昂慷慨文字的,并不是不作。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一腔热血,托之芳草美人,隐隐约约地说出来。一部《诗经》,一部《楚辞》,不大半是如此吗?
直到中年以后,张恨水再谈“旧诗”,态度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编《剪愁集》,所作序言便颇多含糊模棱之语。诗集既名以“剪愁”,顾名思义,是要剪除故态也。但又表示,文人积习既难忘,其环境,“亦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而且,“予遭遇坎坷,每多难言之隐,更得机会,辄一触而发,因是淡月纱窗,西风庭院,负手微吟,颇亦成章”。 其纠结如此,怕是内心冲突的自然流露吧。
数年之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更含蓄地谈到,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还“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 的。这怕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三四十年代已被建构为绝对正确的历史性话语,并被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内化为评判自身行为的标准,身在其中的张恨水,固不能不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