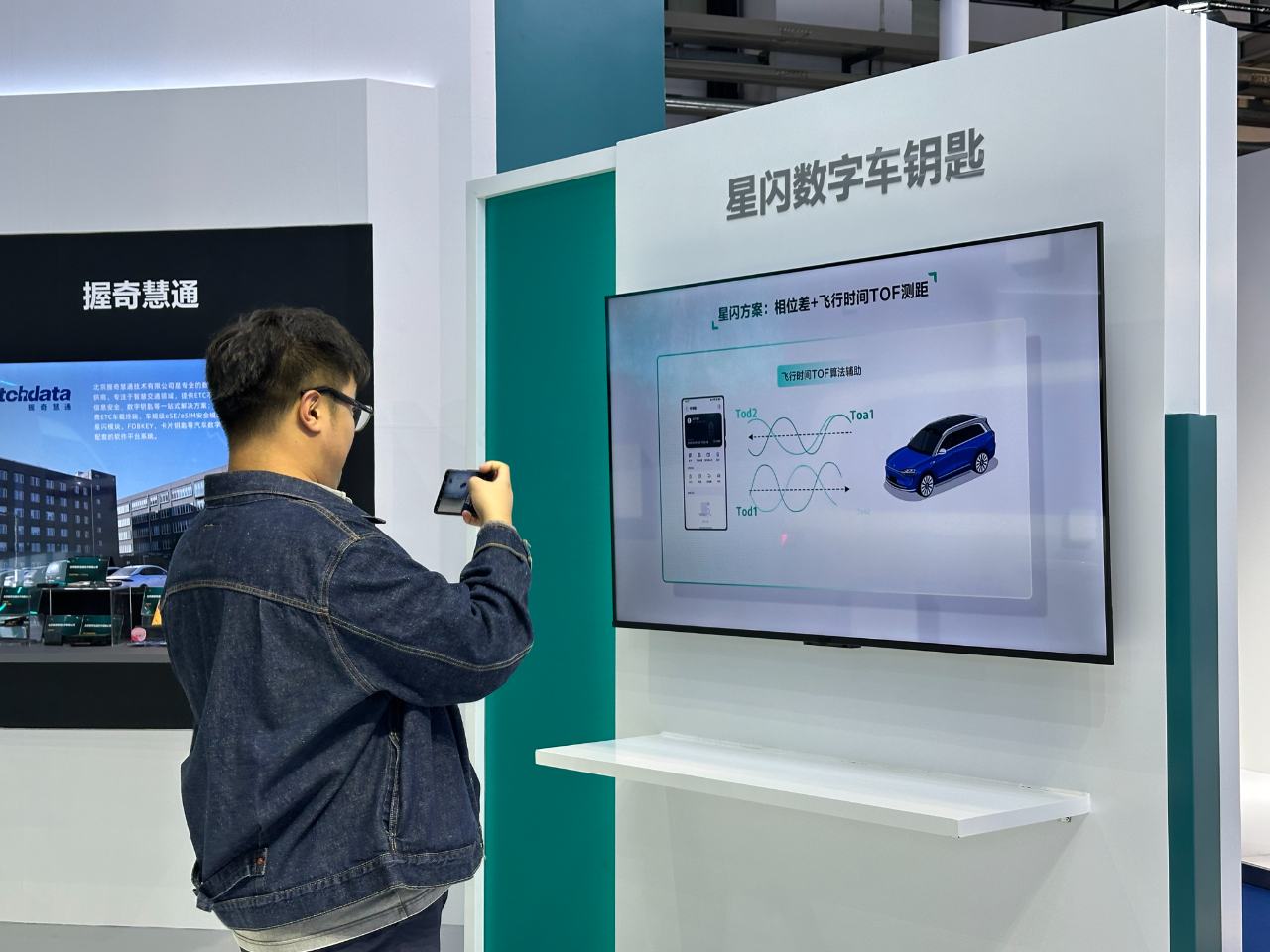《肉体之门》、《春妇传》和《河内的卡门》均改编自田村泰次郎的小说,它们构成了铃木清顺和野川由美子(主演)组合的女性“卖性与性”三部曲,也可以说是清顺的“反战三部典”,借女性的性欲来抵抗军国主义战争这没有人性的残酷命运。三部影片的反战意识不像黑泽明那样张扬外露,而是透过日本军队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压抑性与爱的欲求以及女性以天赋的“性”为反抗武器的描绘,在人性层面上营造出具有悲剧性的震撼力量。《河内的卡门》和《肉体之门》一样,描绘女人依靠性而活着,尽情绽放生命的欲望和力量,和增村保造的《赤色天使》异曲同工。而清顺美学对色彩的执迷,在《肉体之门》有着令人叫绝的表现:以红、紫、绿、黄的服装颜色来区分四位妓女,每位妓女都以显示自身姿色的裙子和灯光来表现,这种艳丽的感官刺激,似乎是对日本主流的战争悲情女性电影的一种反讽。
如果说《关东无宿》、《刺青一代》、《花与怒涛》是任侠片的变奏,那么《野兽的青春》、《东京流浪者》及《杀手的烙印》则属黑帮片类型的破格之作,有着石破天惊的表现。这几部影片的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帮分子,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孤独个体,导演突出的是一种残酷的冷血主义,他们不动感情,不动声色,为一己私利而奋斗,独来独往,如独虎战群狼,个体的反抗在冷酷的社会面前显得毫无意义。用破格的黑帮片类型来反映人在社会中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冷酷的写实主义,这种冷面无情的主角飞蛾扑火般投入世界的愤世孤绝的人物形象,对日后深作欣二的无仁义系列黑帮片和吴宇森的黑帮片有着深刻的影响。
《东京流浪者》将清顺美学推进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正如论者所言,对色彩和舞台美术的利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块地使用鲜艳、混合的色彩,如黄色、红色、深蓝、碧绿、粉红,布置成彩色的墙壁、纱帷作为背景,每一种色彩都清晰、醒目,犹如抽象的泼墨,汇合成一个令人目眩的色彩漩涡;利用台阶、圆柱、雕塑外加追光将舞厅的内景布置成舞台,变换着角度俯拍、仰拍玻璃地板上跳舞人群的投影;用影绘手法拍摄暴力打斗动作,格斗、枪击的人物在漆黑的背景上只留下前景在动,一片乱枪响起,不见人倒下,停顿几秒钟镜头转向别的屋中,才见一人从椅子上滑倒。时间、空间跳跃式变换,镜头忽然离开打斗的人群,槅扇纸窗骤然拉开,积雪的庭园突如其来展现在画面上……
被称为铃木前期最高代表作的《杀手的烙印》,剧本由清顺、木村以及大和屋竺、曾根中生、田中阳造等八个人合作写成,署名“具流八郎”。《杀手的烙印》的实验色彩较《东京流浪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放肆游走的镜头,跳轴、随意切换的画面、无处不在的叠印,色彩、构图和种种无逻辑元素的呈现:布满蝴蝶的房间、突然变成负片效果的画面、头发在马桶里旋转的意象……营造出怪异、艳丽、嚣张、刺激的氛围,也使得清顺成为日本坎普美学的最佳代言人。
《暴力挽歌》则是一曲暴力与性交织的青春挽歌。少年的性欲无处发泄,于是用一场又一场的打架来补偿。后来,少年的仰慕对象转移到了俳句老师身上,这位老师的原型是北一辉,这暗示少年对性欲的憧憬转到了对权力的幻想上。影片最后暗示少年会上京追随北一辉,加入发动“二二六”事件的少壮派军人的行动中,青春的梦想最终被成人世界和污浊的政治所吞噬。这是曾经成为二战士兵的铃木清顺的青春残酷物语。他写道:战争使我的青春像献祭一样,燃烧了。《暴力挽歌》对此进行了最深刻有力的反思。当代日本导演黑泽清深爱这部影片,甚至说它不是日本电影,不是美国电影,也不是欧洲电影,而是地球上存在不了、从宇宙掉下来的电影。
清顺虽然在日活拍出了一系列极具创意的影片,但他用前卫实验的手法拍娱乐片的做法,却激怒了日活的头头堀久作,《杀手的烙印》公映后票房惨淡,后者勃然大怒说:“铃木导演一直拍摄让人看不懂的电影,他不是一个好导演,不可理解的作品是日活公司之耻”,并下令解雇清顺。清顺不服,提出诉讼738万日元,一批电影导演、影评人和学生组织发起示威活动,演变成为演艺界大规模的抗议。官司打了多年,最终以日活赔偿清顺100万日元了结,清顺却也为此付出了10年无片可拍的代价。
《肉体之门》、《春妇传》和《河内的卡门》均改编自田村泰次郎的小说,它们构成了铃木清顺和野川由美子(主演)组合的女性“卖性与性”三部曲,也可以说是清顺的“反战三部典”,借女性的性欲来抵抗军国主义战争这没有人性的残酷命运。三部影片的反战意识不像黑泽明那样张扬外露,而是透过日本军队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压抑性与爱的欲求以及女性以天赋的“性”为反抗武器的描绘,在人性层面上营造出具有悲剧性的震撼力量。《河内的卡门》和《肉体之门》一样,描绘女人依靠性而活着,尽情绽放生命的欲望和力量,和增村保造的《赤色天使》异曲同工。而清顺美学对色彩的执迷,在《肉体之门》有着令人叫绝的表现:以红、紫、绿、黄的服装颜色来区分四位妓女,每位妓女都以显示自身姿色的裙子和灯光来表现,这种艳丽的感官刺激,似乎是对日本主流的战争悲情女性电影的一种反讽。
如果说《关东无宿》、《刺青一代》、《花与怒涛》是任侠片的变奏,那么《野兽的青春》、《东京流浪者》及《杀手的烙印》则属黑帮片类型的破格之作,有着石破天惊的表现。这几部影片的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帮分子,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孤独个体,导演突出的是一种残酷的冷血主义,他们不动感情,不动声色,为一己私利而奋斗,独来独往,如独虎战群狼,个体的反抗在冷酷的社会面前显得毫无意义。用破格的黑帮片类型来反映人在社会中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冷酷的写实主义,这种冷面无情的主角飞蛾扑火般投入世界的愤世孤绝的人物形象,对日后深作欣二的无仁义系列黑帮片和吴宇森的黑帮片有着深刻的影响。
《东京流浪者》将清顺美学推进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正如论者所言,对色彩和舞台美术的利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块地使用鲜艳、混合的色彩,如黄色、红色、深蓝、碧绿、粉红,布置成彩色的墙壁、纱帷作为背景,每一种色彩都清晰、醒目,犹如抽象的泼墨,汇合成一个令人目眩的色彩漩涡;利用台阶、圆柱、雕塑外加追光将舞厅的内景布置成舞台,变换着角度俯拍、仰拍玻璃地板上跳舞人群的投影;用影绘手法拍摄暴力打斗动作,格斗、枪击的人物在漆黑的背景上只留下前景在动,一片乱枪响起,不见人倒下,停顿几秒钟镜头转向别的屋中,才见一人从椅子上滑倒。时间、空间跳跃式变换,镜头忽然离开打斗的人群,槅扇纸窗骤然拉开,积雪的庭园突如其来展现在画面上……
被称为铃木前期最高代表作的《杀手的烙印》,剧本由清顺、木村以及大和屋竺、曾根中生、田中阳造等八个人合作写成,署名“具流八郎”。《杀手的烙印》的实验色彩较《东京流浪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放肆游走的镜头,跳轴、随意切换的画面、无处不在的叠印,色彩、构图和种种无逻辑元素的呈现:布满蝴蝶的房间、突然变成负片效果的画面、头发在马桶里旋转的意象……营造出怪异、艳丽、嚣张、刺激的氛围,也使得清顺成为日本坎普美学的最佳代言人。
《暴力挽歌》则是一曲暴力与性交织的青春挽歌。少年的性欲无处发泄,于是用一场又一场的打架来补偿。后来,少年的仰慕对象转移到了俳句老师身上,这位老师的原型是北一辉,这暗示少年对性欲的憧憬转到了对权力的幻想上。影片最后暗示少年会上京追随北一辉,加入发动“二二六”事件的少壮派军人的行动中,青春的梦想最终被成人世界和污浊的政治所吞噬。这是曾经成为二战士兵的铃木清顺的青春残酷物语。他写道:战争使我的青春像献祭一样,燃烧了。《暴力挽歌》对此进行了最深刻有力的反思。当代日本导演黑泽清深爱这部影片,甚至说它不是日本电影,不是美国电影,也不是欧洲电影,而是地球上存在不了、从宇宙掉下来的电影。
清顺虽然在日活拍出了一系列极具创意的影片,但他用前卫实验的手法拍娱乐片的做法,却激怒了日活的头头堀久作,《杀手的烙印》公映后票房惨淡,后者勃然大怒说:“铃木导演一直拍摄让人看不懂的电影,他不是一个好导演,不可理解的作品是日活公司之耻”,并下令解雇清顺。清顺不服,提出诉讼738万日元,一批电影导演、影评人和学生组织发起示威活动,演变成为演艺界大规模的抗议。官司打了多年,最终以日活赔偿清顺100万日元了结,清顺却也为此付出了10年无片可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