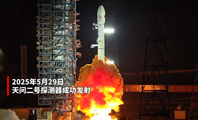“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摘编
黄进兴/演讲
李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选录
第一场
《历史的转向——二十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
○ “历史的转向”并非史学一科可以矩矱或道尽。它乃发生在人文及社会科学“重新发现历史”的共通现象。
○ “历史的转向”并非单纯回归到19世纪的“历史主义”,盖“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发展性”和“独特性”在后现代的氛围,两者均需再经审慎的检验。而除却唤醒“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转向”需要对以往的史学进行一连串的反思。“反思”的对象包括上至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客体,下抵学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触及时间、空间、时序的范畴。这些概念往昔均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分析单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蕴,却都是在特定时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镜其源流。
○ 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不似自然的事物,而具有时空的制约,必得因时制宜,方能蒙其益而不受其害。
○ 历史意识并非凌空环顾,而是受限于一定的视野;所以,历史意识难免局限、倾斜,甚至酿成系统的偏颇。而十九世纪史学所标榜的客观性理想,只是遥不可及的神话。相形之下,中国的反思史学方刚起步,于今之际,唯有急起直追,才能令中国史学超拔于“历史的无意识”!
第二场
《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 臆想中,世界史应是史家治史最高的境界或最终的目标,究其实并不然。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世界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不得说无足轻重,却是相当边缘。世界史通常只是业余人士的雅好,并不受专业史家所重视。不容讳言,该时的世界史与新建制的史学,实格格不入;因是渐次式微,甚至沦为茶余饭后的佐谈,称不得一门正规的学问。
二十世纪末,由于研究水平的提升及教学的普及,更加上全球化意识的推波助澜,令它居于史学的次领域。演讲即旨在阐述此一曲折的过程:从原初追寻世界的意义,至剖析人类往事的知识历程,以揭露世界史起承转合的蜕化,最终方得在二十世纪末站稳脚步,成为当今史学的核心领域。
○ 历史研究不能没有通史般的胸怀,否则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通史如果没有建立在各民族史扎实的研究之上,也将仅是浮沙建塔而已。因此,批评方法、客观研究和综合解释应该携手合作,缺一不可。
○ “普世史”重视的是历史的大事件,特别攸关各民族的相互关联,而政治和外交的折冲更是关怀的焦点所在。当这些权力冲突时,即是“历史时刻”的来临,其结果终究是平衡的状态,而“世界史”的秘密适见于此。换言之,世界史无非是国家民族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之际所形成的。
○ 二十世纪末期出现超越国家界限的区域整合(如欧盟、东协等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例如跨国公司)的现象,无疑是拓展世界史的极佳温床。要之,一九九〇年代“全球化”的风潮,直可视为五〇、六〇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再进化版。对追求全球化的学者而言,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其过时的架构已无法涵盖日新月异的世界趋势,因此必须突破藩篱,另起炉灶,重新寻找书写世界历史的蓝图。换言之,“全球意识”的觉醒与“全球史”的崛起,乃是相互激荡的结果。若说之前的普世史和世界史大概仅及“人文的世界”,但全球史则需顾及自然的历史,也就是把领域扩充至人类全体所居处的地球。
○ 全球史的目标不在涵盖面的辽阔和时间的长远,而是在从事任何在地或特殊的议题时,都应心系全球的关联性,教导学生过去人类生活的多样性,避免单一轴线的大叙述。是故,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史的教科书不但要告知年轻人攸关这个“世界”的知识,并且应教导他们如何从事反思性的“历史思考”,切忌将人类往事化约为单一原则,或统一因素的作用;也就是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所称的“全球史,但诸多故事”。果真如此,方得符合“人人通古今之变,个个成一家之言”的厚望。
“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摘编
黄进兴/演讲
李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选录
第一场
《历史的转向——二十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
○ “历史的转向”并非史学一科可以矩矱或道尽。它乃发生在人文及社会科学“重新发现历史”的共通现象。
○ “历史的转向”并非单纯回归到19世纪的“历史主义”,盖“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发展性”和“独特性”在后现代的氛围,两者均需再经审慎的检验。而除却唤醒“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转向”需要对以往的史学进行一连串的反思。“反思”的对象包括上至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客体,下抵学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触及时间、空间、时序的范畴。这些概念往昔均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分析单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蕴,却都是在特定时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镜其源流。
○ 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不似自然的事物,而具有时空的制约,必得因时制宜,方能蒙其益而不受其害。
○ 历史意识并非凌空环顾,而是受限于一定的视野;所以,历史意识难免局限、倾斜,甚至酿成系统的偏颇。而十九世纪史学所标榜的客观性理想,只是遥不可及的神话。相形之下,中国的反思史学方刚起步,于今之际,唯有急起直追,才能令中国史学超拔于“历史的无意识”!
第二场
《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 臆想中,世界史应是史家治史最高的境界或最终的目标,究其实并不然。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世界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不得说无足轻重,却是相当边缘。世界史通常只是业余人士的雅好,并不受专业史家所重视。不容讳言,该时的世界史与新建制的史学,实格格不入;因是渐次式微,甚至沦为茶余饭后的佐谈,称不得一门正规的学问。
二十世纪末,由于研究水平的提升及教学的普及,更加上全球化意识的推波助澜,令它居于史学的次领域。演讲即旨在阐述此一曲折的过程:从原初追寻世界的意义,至剖析人类往事的知识历程,以揭露世界史起承转合的蜕化,最终方得在二十世纪末站稳脚步,成为当今史学的核心领域。
○ 历史研究不能没有通史般的胸怀,否则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通史如果没有建立在各民族史扎实的研究之上,也将仅是浮沙建塔而已。因此,批评方法、客观研究和综合解释应该携手合作,缺一不可。
○ “普世史”重视的是历史的大事件,特别攸关各民族的相互关联,而政治和外交的折冲更是关怀的焦点所在。当这些权力冲突时,即是“历史时刻”的来临,其结果终究是平衡的状态,而“世界史”的秘密适见于此。换言之,世界史无非是国家民族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之际所形成的。
○ 二十世纪末期出现超越国家界限的区域整合(如欧盟、东协等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例如跨国公司)的现象,无疑是拓展世界史的极佳温床。要之,一九九〇年代“全球化”的风潮,直可视为五〇、六〇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再进化版。对追求全球化的学者而言,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其过时的架构已无法涵盖日新月异的世界趋势,因此必须突破藩篱,另起炉灶,重新寻找书写世界历史的蓝图。换言之,“全球意识”的觉醒与“全球史”的崛起,乃是相互激荡的结果。若说之前的普世史和世界史大概仅及“人文的世界”,但全球史则需顾及自然的历史,也就是把领域扩充至人类全体所居处的地球。
○ 全球史的目标不在涵盖面的辽阔和时间的长远,而是在从事任何在地或特殊的议题时,都应心系全球的关联性,教导学生过去人类生活的多样性,避免单一轴线的大叙述。是故,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史的教科书不但要告知年轻人攸关这个“世界”的知识,并且应教导他们如何从事反思性的“历史思考”,切忌将人类往事化约为单一原则,或统一因素的作用;也就是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所称的“全球史,但诸多故事”。果真如此,方得符合“人人通古今之变,个个成一家之言”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