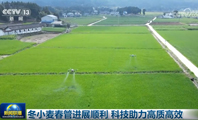建安以后,文学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
从“文学的自觉”说起
从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以来,“文学的自觉”就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命题。按照鲁迅的定义,所谓自觉,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在这里,文学(“诗赋”)与儒教(“教训”)的对立,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术史常规思考模式,在中古学术史研究领域,我们如今仍常看到文学盛因经学衰、史学盛因经学衰、子书衰而文章盛等等观点,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此消彼长”逻辑。
鲁迅对儒教约束文学的看法,当然是有证据可以支撑的,扬雄就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所谓“则”,就是立正则,或者说就是要“寓教训”。但扬雄的话同时也说明,那种“丽以淫”的,即无教训、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自来有之,换言之,文学沾染儒风倒是个阶段性现象,无怪乎后来不断有学者将“自觉”时间自鲁迅规定的曹丕时代上移,乃至有了汉代自觉说、战国发端说、春秋自觉说种种纷争。
本文无意处理文学自觉问题,检讨这一段学术史,是想指出“此消彼长”这一叙述模式本身可能的缺陷:当使用这个模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消减一方的强排他性,并且以此消为彼长的根本甚至唯一原因,但事实上这两者都是很难评估的。在儒教强势时,文学就不发达吗?那如何解释宋代文学的繁荣?在强势思想退潮后,文学就会自动发达吗?那为什么中古时期“自觉”的是文学、史学而偏偏不是直面思想的子书?这些问题都说明,“彼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此消”是一个太过简单的解释。
所以,重新回溯中古文学的产生,我认为“文学自觉”让其他影响因子多少被忽视了。事实上,在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权林立,互相竞争,文学在这样的时局中,很难完全置身事外术而艺术。本文想说明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分裂时期,文学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开发为一种宣传工具,中古文学也正是随着宣传功能的开发而开端的。
新文学功能的发现
宣传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本是宣布传达之意,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宣传”,意义已与古汉语不同。其西文原是不太常用的宗教词汇,有“传教”之义,直到一战,随着协约国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它才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成熟于战争的宣传,既对内更对外,要实现占据正义、鼓舞军心民心、煽动对敌仇恨、拉拢中立等等多重任务,还要对突发的具体事件给与解释。换言之,宣传本身也成为战争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诞生历程,让现代宣传概念比“宣布传达”适用范围要狭窄,但意义层次却更丰富。
尽管作为通行概念的宣传实属晚近舶来,作为现象的宣传却是自古有之,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在宣传。在政权分立时期,来自不同立场的言论确实可以放在宣传视角下解读,但在古代史领域,其实很难见到“宣传史”研究。1985年出版的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可能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古代宣传史著作,但此书将宣传概念极度泛化,导致很多史料解读颇显牵强,比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被视为一种宣传思想。而这也正可见,古代宣传史研究之所以不彰,史料匮乏是一大原因。
按照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看法,所谓宣传,就是通过重要符号控制集体态度。符号,无论文字、图像、音乐还是概念、口号、象征物,构成了宣传活动的核心。尽管局限于史料,我们可能无法详尽勾勒早期社会宣传活动的执行过程和实施效果,但那些曾经使用过的符号多少还散落在文献中,可供后人追踪。而文学,就是这样的符号之一。
对于今日的读者,“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已经是熟识论调,但文学介入宣传,或者说宣传介入文学,是从何时而始呢?无论对于宣传史还是文学史,这都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如果我们在比较狭义的层面上使用宣传这个概念,那么中古时期正是宣传文学的重要时刻。在此之前,尽管文学已经参与了“润色鸿业”,但它尚未在纷争世局中充当过利器。建安以后,文学就不止于润色已有的鸿业,它还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
案例之一:
曹操的周公乐府
在《三国志·崔琰传》“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条下,裴松之补充了两个故事: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青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
这两个事件里都出现了“周公”,而周公正是曹操常用的宣传符号。朱熹说:
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
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
正如朱熹指出的,曹操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周公,有的诗主题本离周公很远,于是周公被强拉进来尤其显得造作。如果从宣传学的角度审视这个现象,那么重复性正是宣传的特征:宣传符号要通过重复推送、不断灌输,才能产生效应。而为了实现有效推送,宣传场合、形式、媒介、渠道都需要优选。酒宴是相当合适的宣传场合,因为宣传者能对主题、受众、气氛有完全的掌握。虽然“周公吐哺”的求贤之意曹操也屡次在教令中表达过,但建立在多形式多渠道上的重复,可以收获更多样化的受众。
乐府显然是曹操重点依赖的宣传形式之一,和徒诗相比,乐府多了一重音乐因素,既作为配乐歌曲宣唱,也可以藉文本流传,可谓早期多媒体,具有很强的传播效力。除了乐府之外,曹操的教令也在推送周公:“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己亥令》)除了曹操本人外,他周围的文人团也在发声,比如王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公讌诗》)的诗句。总之,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宣传的多样化和持续性都是必要的。
比怎样推送更重要的是推送什么,符号的选择是宣传的核心环节。综合曹、王对“周公”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这个符号适用性极强:它既用来表彰曹操廓清天下、再造汉室的功绩,又用来彰显曹操合法的摄政地位,还证明着曹操的忠诚(如果人们选择相信曹操,则曹操就是当代周公;如果怀疑,则更说明曹操是周公),并暗示着一种优惠的人才政策。事实上,能同时收获这些效果的宣传符号,也只有“周公”了,它显然是一个精心的选择,而不是毫无理由的集体用典偏好。
宣传符号的多重意义,往往是随着宣传侧重点的转移而生成的,毕竟对宣传者而言,当新的宣传任务出现,而旧的符号经再阐释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宣传成本要远小于启用新符号。“周公”的生命力就在于此,道理上说,从建安元年(196)献帝都许到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受封魏王的20年中,曹操集团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使用它,惟此前曹操尚无资格比附,此后再提周公就不合适了。前文引及的史料中,可以确知年代的有杨彪事件(建安二年,197)、甄夫人事件(建安九年,204)和《己亥令》(建安十五年,210),前后延续颇久。史料中最后一次出现“周公”符号是在建安十八年(213),这年曹操进爵为公,并接受九锡。册封诏书说:
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衞王室,左右厥世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
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
故周室之不坏,繄二国是赖。
诏书为曹操开国备锡找到的理据是齐、晋故事,但曹操为此发布的令却回应以周公故事: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吾何可比之?
这个微妙的典故置换,与其说是辞让,不如说是对诏书做出的修正。曹操希望人们看到,他受到的待遇仍然符合一直以来的“周公”身份设定。所以在接下来的群臣劝进表中,周公和齐太公一样曾“大启土宇,跨州兼国”的故事得到了强调,而且该表还补充了“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的信息,以便曹操父子在周公符号下继续开展更多的活动。
曹操进封魏公是对汉朝爵制的巨大破坏,正因为如此,周
公的宣传反而要继续,惟将破坏包裹在稳定不变的宣传符号内进行,才能减少震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到了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成为魏王,“周公”终于不再适用的时候,王粲立即写出了“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从军诗》之二,约作于二十一年十月到次年春之间)的诗句,这不仅表明“周公”被抛弃了,也提示我们旧的宣传符号有时是以被超越的形式被抛弃的。
想要评估这场周公运动的实际效果,确实有史料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一直到建安十七年,荀彧仍然认为曹操有恪守臣子本分的可能,倘不考虑宣传的影响,很难解释他的执念从何而来。另一个被宣传影响的人正是前文提到的孔融。成功的宣传符号会使受众产生条件反射式的联想,即使是那些理智上并不认可宣传内容的受众,孔融以“周公”借力打力、讽刺挖苦,就是这样一种条件反射。所以,了解“周公”的宣传符号性质,也才能感受到孔融做的两事会让曹操多么“不堪”。
在这个以“周公”为符号的宣传案例中,文学的贡献非常值得注意。虽然现在可知的参与文本不多,但它们正是被视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端的那些作品。重新考察这些作品中的宣传因子,会让我们对很多旧问题有新认识。
曹操对乐府的偏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面可能有个人兴趣因素,但更可能的是,曹操意识到并利用了乐府诗的多媒体性质。现存曹诗全部是乐府,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纪实,如《蒿里》《薤露》《苦寒》;二是政治愿景,如《度关山》《对酒》;三是游仙。这里面只有第三类是传统题材,而其中也出现了“不戚年往,世忧不治”(《秋胡行》)这样不传统的宣传语,至于前两类,则完全是新鲜的军宣文学和政宣文学。如果认识到这种新变,则前人就曹诗提出的一些内容和风格问题,如谢榛指出的“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兵四十馀万”,胡应麟指出的“《雁门太守行》通篇皆赞词,《折杨柳》通篇皆戒词,名虽乐府,实寡风韵。魏武多有此体,如《度关山》《对酒行》,皆不必法也”,包括前文所引的朱熹的质疑,其实根本不成为问题。
同样该重新审视的还有曹操所谓“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创作方式。过去我们或认为这与当时作曲家的稀缺有关,或认为这与汉乐府“感于哀乐,源事而发”的传统有关。从宣传的角度考量,直接利用人们熟悉的旧题旧曲填词,最简单的意图是提高接受度,因此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或者音乐问题。
前文提到过,曹操的乐府和教令时有呼应,像《己亥令》和《短歌行》(周西伯昌)就有明显的文字配合。以文学来歌颂或阐释新指示、新精神、新政策,也是建安时代文学新变之一,但新变不止于此,在下面一组案例中我们将看到,文学的能力不仅在配合,它还在主动造势。
建安以后,文学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
从“文学的自觉”说起
从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以来,“文学的自觉”就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命题。按照鲁迅的定义,所谓自觉,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在这里,文学(“诗赋”)与儒教(“教训”)的对立,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术史常规思考模式,在中古学术史研究领域,我们如今仍常看到文学盛因经学衰、史学盛因经学衰、子书衰而文章盛等等观点,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此消彼长”逻辑。
鲁迅对儒教约束文学的看法,当然是有证据可以支撑的,扬雄就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所谓“则”,就是立正则,或者说就是要“寓教训”。但扬雄的话同时也说明,那种“丽以淫”的,即无教训、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自来有之,换言之,文学沾染儒风倒是个阶段性现象,无怪乎后来不断有学者将“自觉”时间自鲁迅规定的曹丕时代上移,乃至有了汉代自觉说、战国发端说、春秋自觉说种种纷争。
本文无意处理文学自觉问题,检讨这一段学术史,是想指出“此消彼长”这一叙述模式本身可能的缺陷:当使用这个模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消减一方的强排他性,并且以此消为彼长的根本甚至唯一原因,但事实上这两者都是很难评估的。在儒教强势时,文学就不发达吗?那如何解释宋代文学的繁荣?在强势思想退潮后,文学就会自动发达吗?那为什么中古时期“自觉”的是文学、史学而偏偏不是直面思想的子书?这些问题都说明,“彼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此消”是一个太过简单的解释。
所以,重新回溯中古文学的产生,我认为“文学自觉”让其他影响因子多少被忽视了。事实上,在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权林立,互相竞争,文学在这样的时局中,很难完全置身事外术而艺术。本文想说明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分裂时期,文学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开发为一种宣传工具,中古文学也正是随着宣传功能的开发而开端的。
新文学功能的发现
宣传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本是宣布传达之意,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宣传”,意义已与古汉语不同。其西文原是不太常用的宗教词汇,有“传教”之义,直到一战,随着协约国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它才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成熟于战争的宣传,既对内更对外,要实现占据正义、鼓舞军心民心、煽动对敌仇恨、拉拢中立等等多重任务,还要对突发的具体事件给与解释。换言之,宣传本身也成为战争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诞生历程,让现代宣传概念比“宣布传达”适用范围要狭窄,但意义层次却更丰富。
尽管作为通行概念的宣传实属晚近舶来,作为现象的宣传却是自古有之,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在宣传。在政权分立时期,来自不同立场的言论确实可以放在宣传视角下解读,但在古代史领域,其实很难见到“宣传史”研究。1985年出版的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可能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古代宣传史著作,但此书将宣传概念极度泛化,导致很多史料解读颇显牵强,比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被视为一种宣传思想。而这也正可见,古代宣传史研究之所以不彰,史料匮乏是一大原因。
按照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看法,所谓宣传,就是通过重要符号控制集体态度。符号,无论文字、图像、音乐还是概念、口号、象征物,构成了宣传活动的核心。尽管局限于史料,我们可能无法详尽勾勒早期社会宣传活动的执行过程和实施效果,但那些曾经使用过的符号多少还散落在文献中,可供后人追踪。而文学,就是这样的符号之一。
对于今日的读者,“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已经是熟识论调,但文学介入宣传,或者说宣传介入文学,是从何时而始呢?无论对于宣传史还是文学史,这都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如果我们在比较狭义的层面上使用宣传这个概念,那么中古时期正是宣传文学的重要时刻。在此之前,尽管文学已经参与了“润色鸿业”,但它尚未在纷争世局中充当过利器。建安以后,文学就不止于润色已有的鸿业,它还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
案例之一:
曹操的周公乐府
在《三国志·崔琰传》“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条下,裴松之补充了两个故事: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青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
这两个事件里都出现了“周公”,而周公正是曹操常用的宣传符号。朱熹说:
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
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
正如朱熹指出的,曹操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周公,有的诗主题本离周公很远,于是周公被强拉进来尤其显得造作。如果从宣传学的角度审视这个现象,那么重复性正是宣传的特征:宣传符号要通过重复推送、不断灌输,才能产生效应。而为了实现有效推送,宣传场合、形式、媒介、渠道都需要优选。酒宴是相当合适的宣传场合,因为宣传者能对主题、受众、气氛有完全的掌握。虽然“周公吐哺”的求贤之意曹操也屡次在教令中表达过,但建立在多形式多渠道上的重复,可以收获更多样化的受众。
乐府显然是曹操重点依赖的宣传形式之一,和徒诗相比,乐府多了一重音乐因素,既作为配乐歌曲宣唱,也可以藉文本流传,可谓早期多媒体,具有很强的传播效力。除了乐府之外,曹操的教令也在推送周公:“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己亥令》)除了曹操本人外,他周围的文人团也在发声,比如王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公讌诗》)的诗句。总之,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宣传的多样化和持续性都是必要的。
比怎样推送更重要的是推送什么,符号的选择是宣传的核心环节。综合曹、王对“周公”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这个符号适用性极强:它既用来表彰曹操廓清天下、再造汉室的功绩,又用来彰显曹操合法的摄政地位,还证明着曹操的忠诚(如果人们选择相信曹操,则曹操就是当代周公;如果怀疑,则更说明曹操是周公),并暗示着一种优惠的人才政策。事实上,能同时收获这些效果的宣传符号,也只有“周公”了,它显然是一个精心的选择,而不是毫无理由的集体用典偏好。
宣传符号的多重意义,往往是随着宣传侧重点的转移而生成的,毕竟对宣传者而言,当新的宣传任务出现,而旧的符号经再阐释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宣传成本要远小于启用新符号。“周公”的生命力就在于此,道理上说,从建安元年(196)献帝都许到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受封魏王的20年中,曹操集团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使用它,惟此前曹操尚无资格比附,此后再提周公就不合适了。前文引及的史料中,可以确知年代的有杨彪事件(建安二年,197)、甄夫人事件(建安九年,204)和《己亥令》(建安十五年,210),前后延续颇久。史料中最后一次出现“周公”符号是在建安十八年(213),这年曹操进爵为公,并接受九锡。册封诏书说:
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衞王室,左右厥世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
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
故周室之不坏,繄二国是赖。
诏书为曹操开国备锡找到的理据是齐、晋故事,但曹操为此发布的令却回应以周公故事: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吾何可比之?
这个微妙的典故置换,与其说是辞让,不如说是对诏书做出的修正。曹操希望人们看到,他受到的待遇仍然符合一直以来的“周公”身份设定。所以在接下来的群臣劝进表中,周公和齐太公一样曾“大启土宇,跨州兼国”的故事得到了强调,而且该表还补充了“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的信息,以便曹操父子在周公符号下继续开展更多的活动。
曹操进封魏公是对汉朝爵制的巨大破坏,正因为如此,周
公的宣传反而要继续,惟将破坏包裹在稳定不变的宣传符号内进行,才能减少震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到了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成为魏王,“周公”终于不再适用的时候,王粲立即写出了“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从军诗》之二,约作于二十一年十月到次年春之间)的诗句,这不仅表明“周公”被抛弃了,也提示我们旧的宣传符号有时是以被超越的形式被抛弃的。
想要评估这场周公运动的实际效果,确实有史料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一直到建安十七年,荀彧仍然认为曹操有恪守臣子本分的可能,倘不考虑宣传的影响,很难解释他的执念从何而来。另一个被宣传影响的人正是前文提到的孔融。成功的宣传符号会使受众产生条件反射式的联想,即使是那些理智上并不认可宣传内容的受众,孔融以“周公”借力打力、讽刺挖苦,就是这样一种条件反射。所以,了解“周公”的宣传符号性质,也才能感受到孔融做的两事会让曹操多么“不堪”。
在这个以“周公”为符号的宣传案例中,文学的贡献非常值得注意。虽然现在可知的参与文本不多,但它们正是被视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端的那些作品。重新考察这些作品中的宣传因子,会让我们对很多旧问题有新认识。
曹操对乐府的偏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面可能有个人兴趣因素,但更可能的是,曹操意识到并利用了乐府诗的多媒体性质。现存曹诗全部是乐府,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纪实,如《蒿里》《薤露》《苦寒》;二是政治愿景,如《度关山》《对酒》;三是游仙。这里面只有第三类是传统题材,而其中也出现了“不戚年往,世忧不治”(《秋胡行》)这样不传统的宣传语,至于前两类,则完全是新鲜的军宣文学和政宣文学。如果认识到这种新变,则前人就曹诗提出的一些内容和风格问题,如谢榛指出的“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兵四十馀万”,胡应麟指出的“《雁门太守行》通篇皆赞词,《折杨柳》通篇皆戒词,名虽乐府,实寡风韵。魏武多有此体,如《度关山》《对酒行》,皆不必法也”,包括前文所引的朱熹的质疑,其实根本不成为问题。
同样该重新审视的还有曹操所谓“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创作方式。过去我们或认为这与当时作曲家的稀缺有关,或认为这与汉乐府“感于哀乐,源事而发”的传统有关。从宣传的角度考量,直接利用人们熟悉的旧题旧曲填词,最简单的意图是提高接受度,因此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或者音乐问题。
前文提到过,曹操的乐府和教令时有呼应,像《己亥令》和《短歌行》(周西伯昌)就有明显的文字配合。以文学来歌颂或阐释新指示、新精神、新政策,也是建安时代文学新变之一,但新变不止于此,在下面一组案例中我们将看到,文学的能力不仅在配合,它还在主动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