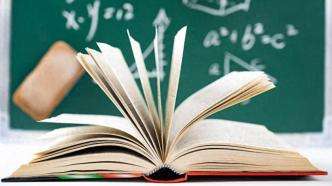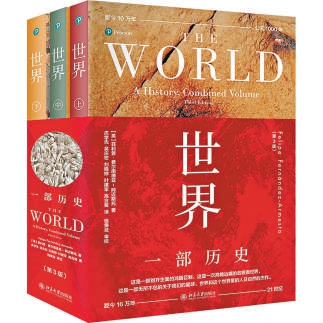
《世界:一部历史》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著 庆学先 等译 钱乘旦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尽管本书讲述的故事是人类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绝不仅限于人类,因为一味突显人类是没有意义的。人类也是动物,要想透彻地理解我们自身,认识我们因何独特,我们就不得不参照其他动物。
人类故事与环境密不可分
正如研究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只有联系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才能更好地研究自身。我们无法脱离环境来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人类的故事与气候密不可分,与我们赖以生存或我们与之竞争的其他生命形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改造环境,但永远脱离不了环境。
我们从自然之中分化出来——我们这样随意谈论自然,就好像我们自己不是自然的产物一样。我们通过采用自认为非自然的行为,如穿衣、吃熟食、用文化取代自然等,与我们的动物伙伴拉开距离。简言之,我们任性行事,但我们创造的所有复杂精美的文化,却使我们与自身改造的环境和利用的生物有了密切的新关系。
与其他动物比较起来,我们更加雄心勃勃,通过主动改造环境来满足自身的目的。我们开垦土地,改草原为田亩,变沙漠为花园,再把花园变为沙漠;在有森林的地方我们将其砍伐一空,又在没有森林的地方植树造林;我们筑坝截水、围海造田、栽培植物、畜养动物、灭绝某些物种,又用人工繁殖和杂交培育出新的物种。有时我们甚至会在原有的地表上面,为我们自己营造出新的环境。
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将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历史的核心悖论:我们愈是改变环境,我们就愈加脆弱,难抵生态失衡和意外灾难的危险。正是由于无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文明才一再沦为废墟。历史成为一条穿行于文明碎片之中的轨道。当然,这并不是说环境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或生活,但环境的确为我们的行动设定了界限。
就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地貌的生存能力而言,我们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物种,几乎超过了其他任何动物。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只不过是这个行星上的探索者,时刻都在努力改造它。我们自命为地球的主人,或者谦称自己为地球的守护者,但大约90%的地球生物圈处在深海或地壳深处,都是一些我们凭借现有技术无法生存的地方。
环境与文化的双线叙事
与人类社会相比,非人类动物的社会变化微乎其微。因此,除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交互作用之外,另一个构成我们历史的重大主题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变化、分流发展、重新建立接触联系并反过来影响彼此的方式。
因此,本书交织讲述了两个故事——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的互动。以环境为核心的故事,聚焦人类如何逐步脱离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探寻一条能在建设性开发与破坏性利用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的共处之道。而以文化为核心的故事,则围绕人类文化展开:不同文化既相互影响、交融共生,又保持自身特质、彼此区隔。这两个故事已在历史长河中演绎了数千年,至于最终将以胜利落幕,还是以灾难收场,我们尚无法预知。
要在一本书中讲述全部的世界历史,显然并不现实。因此,本书的框架是由精挑细选的纲目搭建而成的。读者将会在每章开篇处发现它们或被化入漫谈之中,或被融入故事之内。
以人为焦点的历史生态学,也就是环境主题,将反复向读者呈现一系列关键议题:生存、庇护所、疾病、能源、技术与艺术。对历史学家而言,艺术是尤为重要的范畴。它既是人类与世界其余部分对话的重要界面,更记录了我们看待现实的视角,以及这一视角的变迁历程。
在讲述人类交往互动的全球历史,也就是文化主题时,我们时时关注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迁徙、贸易、战争、扩张、朝圣、礼尚往来、外交、旅行;我们也时时考察其各自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形态、人类群体划分、国家和文明、性别和世代、阶级和团体特征。
在证据与想象间重构过去
古希腊圣贤阿迦同曾说:“鹳以蛇为食,猪以橡果为食,历史则以人类的生活为素材。”想要描绘过去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图景,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人类遗留下来的证据入手,然后借助有根有据的想象一点一点地加以汇总。解读证据本身就是一项挑战——而这份挑战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机遇。历史学的探讨核心并非过去本身——毕竟我们的感官根本无法直接触及过往。我们所能掌握的,不过是一些关于过去的零散证据。因此,历史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更应被视作一门艺术:一门尊重原始资料,并始终受其约束的艺术。
对于本书而言,原始资料为我们的想象设定了界限。有的原始资料能够提供具体线索,告诉我们过去的人们真正做了些什么,例如他们的足迹、他们的食物残余、展现他们技术水平的零星遗物、他们的居所残骸、遗留在他们骸骨上的疾病痕迹等。但在通常情况下,原始资料并不能反映出事物的原貌,而仅能反映出过去的人们如何用艺术、手工艺品和作品表现当时的事物。简言之,绝大多数原始资料都只能反映出留下这些原始资料者的内心世界。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讲述过去是什么样子,而是讲述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因为这就是证据倾向于告诉我们的。由于证据总是不够完整,所以历史研究与其说是描绘、叙述或释疑,倒不如说是质疑。阅读本书的读者切莫期望能从中得到一目了然的史实和已经证明的知识。事实上,研读历史的乐趣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得到正确的答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最佳预期也不过是发现一些能够激发探讨兴趣的问题。而且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我们没有充足的知识去得出结论,探讨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有的历史学家乐于对现在发问:我们是如何陷入当下的混乱状态中的?我们能够从过去找到现在所处困境的原因吗?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追溯到多远的过去?为什么当今世界已是全球互联互通,我们却没有全球治理?为什么和平总是岌岌可危?为什么全球环境面临生态失衡的威胁?有的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未来,他们力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学会改变我们人类的行为,避免历史困境重现。还有的历史学家则致力于合理解读过去,找出一种从整体上描述或叙述过去的办法,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理解了过去。(作者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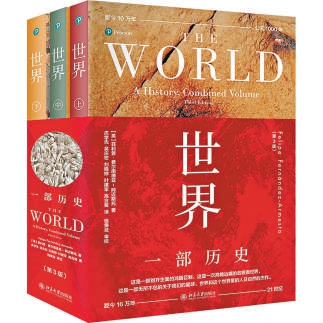
《世界:一部历史》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著 庆学先 等译 钱乘旦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尽管本书讲述的故事是人类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绝不仅限于人类,因为一味突显人类是没有意义的。人类也是动物,要想透彻地理解我们自身,认识我们因何独特,我们就不得不参照其他动物。
人类故事与环境密不可分
正如研究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只有联系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才能更好地研究自身。我们无法脱离环境来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人类的故事与气候密不可分,与我们赖以生存或我们与之竞争的其他生命形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改造环境,但永远脱离不了环境。
我们从自然之中分化出来——我们这样随意谈论自然,就好像我们自己不是自然的产物一样。我们通过采用自认为非自然的行为,如穿衣、吃熟食、用文化取代自然等,与我们的动物伙伴拉开距离。简言之,我们任性行事,但我们创造的所有复杂精美的文化,却使我们与自身改造的环境和利用的生物有了密切的新关系。
与其他动物比较起来,我们更加雄心勃勃,通过主动改造环境来满足自身的目的。我们开垦土地,改草原为田亩,变沙漠为花园,再把花园变为沙漠;在有森林的地方我们将其砍伐一空,又在没有森林的地方植树造林;我们筑坝截水、围海造田、栽培植物、畜养动物、灭绝某些物种,又用人工繁殖和杂交培育出新的物种。有时我们甚至会在原有的地表上面,为我们自己营造出新的环境。
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将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历史的核心悖论:我们愈是改变环境,我们就愈加脆弱,难抵生态失衡和意外灾难的危险。正是由于无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文明才一再沦为废墟。历史成为一条穿行于文明碎片之中的轨道。当然,这并不是说环境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或生活,但环境的确为我们的行动设定了界限。
就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地貌的生存能力而言,我们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物种,几乎超过了其他任何动物。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只不过是这个行星上的探索者,时刻都在努力改造它。我们自命为地球的主人,或者谦称自己为地球的守护者,但大约90%的地球生物圈处在深海或地壳深处,都是一些我们凭借现有技术无法生存的地方。
环境与文化的双线叙事
与人类社会相比,非人类动物的社会变化微乎其微。因此,除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交互作用之外,另一个构成我们历史的重大主题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变化、分流发展、重新建立接触联系并反过来影响彼此的方式。
因此,本书交织讲述了两个故事——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的互动。以环境为核心的故事,聚焦人类如何逐步脱离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探寻一条能在建设性开发与破坏性利用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的共处之道。而以文化为核心的故事,则围绕人类文化展开:不同文化既相互影响、交融共生,又保持自身特质、彼此区隔。这两个故事已在历史长河中演绎了数千年,至于最终将以胜利落幕,还是以灾难收场,我们尚无法预知。
要在一本书中讲述全部的世界历史,显然并不现实。因此,本书的框架是由精挑细选的纲目搭建而成的。读者将会在每章开篇处发现它们或被化入漫谈之中,或被融入故事之内。
以人为焦点的历史生态学,也就是环境主题,将反复向读者呈现一系列关键议题:生存、庇护所、疾病、能源、技术与艺术。对历史学家而言,艺术是尤为重要的范畴。它既是人类与世界其余部分对话的重要界面,更记录了我们看待现实的视角,以及这一视角的变迁历程。
在讲述人类交往互动的全球历史,也就是文化主题时,我们时时关注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迁徙、贸易、战争、扩张、朝圣、礼尚往来、外交、旅行;我们也时时考察其各自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形态、人类群体划分、国家和文明、性别和世代、阶级和团体特征。
在证据与想象间重构过去
古希腊圣贤阿迦同曾说:“鹳以蛇为食,猪以橡果为食,历史则以人类的生活为素材。”想要描绘过去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图景,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人类遗留下来的证据入手,然后借助有根有据的想象一点一点地加以汇总。解读证据本身就是一项挑战——而这份挑战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机遇。历史学的探讨核心并非过去本身——毕竟我们的感官根本无法直接触及过往。我们所能掌握的,不过是一些关于过去的零散证据。因此,历史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更应被视作一门艺术:一门尊重原始资料,并始终受其约束的艺术。
对于本书而言,原始资料为我们的想象设定了界限。有的原始资料能够提供具体线索,告诉我们过去的人们真正做了些什么,例如他们的足迹、他们的食物残余、展现他们技术水平的零星遗物、他们的居所残骸、遗留在他们骸骨上的疾病痕迹等。但在通常情况下,原始资料并不能反映出事物的原貌,而仅能反映出过去的人们如何用艺术、手工艺品和作品表现当时的事物。简言之,绝大多数原始资料都只能反映出留下这些原始资料者的内心世界。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讲述过去是什么样子,而是讲述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因为这就是证据倾向于告诉我们的。由于证据总是不够完整,所以历史研究与其说是描绘、叙述或释疑,倒不如说是质疑。阅读本书的读者切莫期望能从中得到一目了然的史实和已经证明的知识。事实上,研读历史的乐趣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得到正确的答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最佳预期也不过是发现一些能够激发探讨兴趣的问题。而且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我们没有充足的知识去得出结论,探讨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有的历史学家乐于对现在发问:我们是如何陷入当下的混乱状态中的?我们能够从过去找到现在所处困境的原因吗?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追溯到多远的过去?为什么当今世界已是全球互联互通,我们却没有全球治理?为什么和平总是岌岌可危?为什么全球环境面临生态失衡的威胁?有的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未来,他们力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学会改变我们人类的行为,避免历史困境重现。还有的历史学家则致力于合理解读过去,找出一种从整体上描述或叙述过去的办法,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理解了过去。(作者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