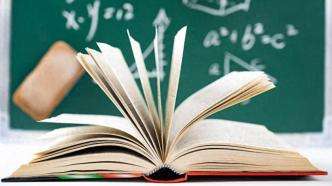谈到“平等”,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已经不会再有明显的反对声音。与此同时,关于“不平等”的公开而直接的讨论却也越来越少。然而其中的悖论在于,明明追求平等看上去已经成了共识,但不平等却并没有消退。谢晶注意到,我们对于“平等”的理解正在走向一种误区。我们看似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讨论平等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平等,但几乎不再追问什么是平等以及为什么要实现平等。
在谢晶看来,后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提出。“就算平等是可实现的,就算我们搞清楚了实现它的方式,如果其结果是人的‘非人化’,是我们获得尊重和关爱的根本需要普遍地得不到满足,是我们最根本的脆弱性被彻底无视,那么这样的平等还是值得追求的吗?”在《平等悖论》这本书中,谢晶试图回答的不是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平等存在,她关心的是我们追求平等而不得的悖论,以及“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
谢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现代性批判、性别研究等。著有《平等悖论》《从涂尔干到莫斯》等。

《平等悖论》作者:谢晶
版本: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1月
从成为母亲开始的“意识”
新京报:先从这本书的缘起聊起吧。我注意到你在后记中提到,对“不平等”的关注曾发生过一次对个人而言重大的转向——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我的”哲学问题。这个转变的契机是做了母亲。
谢晶:现在回想起来,成为母亲给我的是“当头一棒”的感觉,并且后来我发现许多知识分子女性都有类似的感受。尤其当我们身处哲学的领域,它很容易让人对真实世界充满“钝感”。我们一路做“学霸”,再走上科研的道路,大家研究的又都是一些非常抽象且看起来“普世”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被区别对待,但做了妈妈后好像一下子被“打回原形”了。
从怀孕开始就常常有些让我不太理解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么多人都觉得有资格来对我的身体和我的饮食起居指手画脚。在产假之后,我就被问到什么时候可以从当妈妈的状态里“走出来”,重新回到“有产出”的状态。我在生育完大概六个月后第一次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但坐在那里我一直在神游,觉得飘在会场上空的这些抽象的讨论“毫无意义”。那段时间,除了孩子时时刻刻的需求,我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从此,我和很多女性一样,猝不及防地陷入了“兼顾”和“母职惩罚”,尤其是陷入了自责之中,觉得自己妈妈也做不好,学者也做不好。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因为母亲的身份,职场妈妈的身份令我们被苛刻地要求。比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和孩子是一个共同体,不仅婴儿有分离焦虑,母亲也会有,但大家不觉得需要尊重这种状态。又比如,照料的节奏和工作的节奏是完全无法兼容的,但社会在要求女性兼顾的同时,并没有对于公私两个领域能兼顾做出多大努力。
这些是令我一头扎进了“不平等”议题的契机。个人的问题并不都值得被分析,但如果背后的原因是结构性的,那么个人的问题就会成为我们看世界的有效视角。当我意识到自己做母亲的困境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这些结构性的原因不仅令女性陷入困境,而且非常普遍地在不同身份和承担着不同职责的人之间建立着不平等的关系,我就知道自己的经历正在转化成学术上的旨趣。
做母亲的经历不仅给我视角,而且也改变了我做学问的方式。因为做母亲令我对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重新排序,原来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面前变得不值一提。又因为在和这个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越发感觉之前对很多事情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比如一个孩子总是不断在发生变化,他还没有被规训为任何我们可以做出预判的“人设”,所以养育孩子的一大特征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你没办法用理性协商的模式去和他相处,也没办法用理性分析去理解他,这些都打破了我原来“理性至上主义”的迷思,也改变了我对应该如何从事人文社会学科的看法。与孩子的相处让我反思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关于人的最根本的问题。
新京报:这种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谢晶:我博士论文做的是社会本体论,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觉得别人觉得我应该感兴趣”的问题。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绕,但实际上我们常常在做别人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自认为这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现在知道两者的区别,因为我看到“不平等”是怎么样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我的哲学问题。对于性别不平等的体验令我对于任何意义上的统治、剥夺、剥削关系都“有动于衷”,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分析总是令我“上头”,我是带着饱满的情绪在展开这方面的思考,此时的思想本身也是生动的。
正统的哲学训练要求我们“中立、客观”,我也曾经一度以为带有亲身经历和情绪的思考是要避免的。但是我现在确信,这不仅不是“次一等”的思想,而且是更有力的思想。
在“公平”与“平等”之间
新京报:让我们尝试将讨论拉到更地面一些。在我的观察中,今天的很多关于“平等”的讨论似乎和关于“公平”的讨论是缠绕在一起的,一旦一件事看起来满足“公平”的条件,人们似乎也就不再执着于它是否“平等”了,但很多时候恰恰是“公平”才导向了“不平等”。这一点在近两年的教育议题的关注中格外明显,你会怎么看“公平”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谢晶:为什么根据一种定义界定出是好的事情,却不符合另外一种定义?为什么我们认为“平等的”事情却“不公平”,或者反过来,有的人认为是“公平的”可能在另一些人眼里“不平等”?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信印度教的人看来是公平的,但它不符合我们的平等原则。
这些看上去好像涉及我们对于“平等”和“公平”的定义,它们也确实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自己在说“平等”和“公平”时,究竟在指什么。但说到底,定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群体觉得应该怎样对待其成员。正确对待一个人的方式有时被认为是“平等”地待人,有时被认为是“公正”地待人。所以,当我们发现平等地待人却不公平,我们不会满足于说“这只是定义不同”,而是会觉得这样平等待人是有违初衷的。我在书中将此称为“概念失效”:一个明明用来界定好的行动的概念,符合它的行动却并不带来好的结果。
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社会成员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就会产生大量的概念失效。以教育为例,让所有人都接受一样的教育、参加一样的考试这件事到底对不对?很多人其实隐约觉得这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这是用形式平等掩盖实际不平等,甚至是用形式平等去为实际不平等提供正当性。广义的“公正”指的是正确对待每个人的方式,而现代社会认为正确对待每个人的方式就是赋予每个人一样的权利,也就是以平权来实现公正。但这真的合乎平等原则吗?所谓的“同一条起跑线”,其根本目的是让人“跑”起来,每个人都要跑出一个“成绩”,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拉开的差距再大,起跑线都使得这种差距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公正的。更直白地说,它令我们仍然接受人是要分三六九等的,只不过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跑出来的。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核心。桑德尔指出这种赛跑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是不利于团结的,它会在社会成员间产生很多怨恨与嫉妒。而我还想给出的一个视角是,这样赋予所有人同样的权利和机遇,并不是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它实际上不能被称作“平等”。统一的标准仅仅造成平等的假象,它意味着对于不同的人,社会的苛刻程度大有不同。由此我试图给出另一种平等观,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价值多元的,它不会用统一的评价体系去对待所有的人。
谈到“平等”,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已经不会再有明显的反对声音。与此同时,关于“不平等”的公开而直接的讨论却也越来越少。然而其中的悖论在于,明明追求平等看上去已经成了共识,但不平等却并没有消退。谢晶注意到,我们对于“平等”的理解正在走向一种误区。我们看似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讨论平等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平等,但几乎不再追问什么是平等以及为什么要实现平等。
在谢晶看来,后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提出。“就算平等是可实现的,就算我们搞清楚了实现它的方式,如果其结果是人的‘非人化’,是我们获得尊重和关爱的根本需要普遍地得不到满足,是我们最根本的脆弱性被彻底无视,那么这样的平等还是值得追求的吗?”在《平等悖论》这本书中,谢晶试图回答的不是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平等存在,她关心的是我们追求平等而不得的悖论,以及“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
谢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现代性批判、性别研究等。著有《平等悖论》《从涂尔干到莫斯》等。

《平等悖论》作者:谢晶
版本: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1月
从成为母亲开始的“意识”
新京报:先从这本书的缘起聊起吧。我注意到你在后记中提到,对“不平等”的关注曾发生过一次对个人而言重大的转向——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我的”哲学问题。这个转变的契机是做了母亲。
谢晶:现在回想起来,成为母亲给我的是“当头一棒”的感觉,并且后来我发现许多知识分子女性都有类似的感受。尤其当我们身处哲学的领域,它很容易让人对真实世界充满“钝感”。我们一路做“学霸”,再走上科研的道路,大家研究的又都是一些非常抽象且看起来“普世”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被区别对待,但做了妈妈后好像一下子被“打回原形”了。
从怀孕开始就常常有些让我不太理解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么多人都觉得有资格来对我的身体和我的饮食起居指手画脚。在产假之后,我就被问到什么时候可以从当妈妈的状态里“走出来”,重新回到“有产出”的状态。我在生育完大概六个月后第一次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但坐在那里我一直在神游,觉得飘在会场上空的这些抽象的讨论“毫无意义”。那段时间,除了孩子时时刻刻的需求,我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从此,我和很多女性一样,猝不及防地陷入了“兼顾”和“母职惩罚”,尤其是陷入了自责之中,觉得自己妈妈也做不好,学者也做不好。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因为母亲的身份,职场妈妈的身份令我们被苛刻地要求。比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和孩子是一个共同体,不仅婴儿有分离焦虑,母亲也会有,但大家不觉得需要尊重这种状态。又比如,照料的节奏和工作的节奏是完全无法兼容的,但社会在要求女性兼顾的同时,并没有对于公私两个领域能兼顾做出多大努力。
这些是令我一头扎进了“不平等”议题的契机。个人的问题并不都值得被分析,但如果背后的原因是结构性的,那么个人的问题就会成为我们看世界的有效视角。当我意识到自己做母亲的困境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这些结构性的原因不仅令女性陷入困境,而且非常普遍地在不同身份和承担着不同职责的人之间建立着不平等的关系,我就知道自己的经历正在转化成学术上的旨趣。
做母亲的经历不仅给我视角,而且也改变了我做学问的方式。因为做母亲令我对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重新排序,原来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面前变得不值一提。又因为在和这个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越发感觉之前对很多事情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比如一个孩子总是不断在发生变化,他还没有被规训为任何我们可以做出预判的“人设”,所以养育孩子的一大特征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你没办法用理性协商的模式去和他相处,也没办法用理性分析去理解他,这些都打破了我原来“理性至上主义”的迷思,也改变了我对应该如何从事人文社会学科的看法。与孩子的相处让我反思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关于人的最根本的问题。
新京报:这种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谢晶:我博士论文做的是社会本体论,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觉得别人觉得我应该感兴趣”的问题。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绕,但实际上我们常常在做别人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自认为这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现在知道两者的区别,因为我看到“不平等”是怎么样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我的哲学问题。对于性别不平等的体验令我对于任何意义上的统治、剥夺、剥削关系都“有动于衷”,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分析总是令我“上头”,我是带着饱满的情绪在展开这方面的思考,此时的思想本身也是生动的。
正统的哲学训练要求我们“中立、客观”,我也曾经一度以为带有亲身经历和情绪的思考是要避免的。但是我现在确信,这不仅不是“次一等”的思想,而且是更有力的思想。
在“公平”与“平等”之间
新京报:让我们尝试将讨论拉到更地面一些。在我的观察中,今天的很多关于“平等”的讨论似乎和关于“公平”的讨论是缠绕在一起的,一旦一件事看起来满足“公平”的条件,人们似乎也就不再执着于它是否“平等”了,但很多时候恰恰是“公平”才导向了“不平等”。这一点在近两年的教育议题的关注中格外明显,你会怎么看“公平”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谢晶:为什么根据一种定义界定出是好的事情,却不符合另外一种定义?为什么我们认为“平等的”事情却“不公平”,或者反过来,有的人认为是“公平的”可能在另一些人眼里“不平等”?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信印度教的人看来是公平的,但它不符合我们的平等原则。
这些看上去好像涉及我们对于“平等”和“公平”的定义,它们也确实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自己在说“平等”和“公平”时,究竟在指什么。但说到底,定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群体觉得应该怎样对待其成员。正确对待一个人的方式有时被认为是“平等”地待人,有时被认为是“公正”地待人。所以,当我们发现平等地待人却不公平,我们不会满足于说“这只是定义不同”,而是会觉得这样平等待人是有违初衷的。我在书中将此称为“概念失效”:一个明明用来界定好的行动的概念,符合它的行动却并不带来好的结果。
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社会成员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就会产生大量的概念失效。以教育为例,让所有人都接受一样的教育、参加一样的考试这件事到底对不对?很多人其实隐约觉得这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这是用形式平等掩盖实际不平等,甚至是用形式平等去为实际不平等提供正当性。广义的“公正”指的是正确对待每个人的方式,而现代社会认为正确对待每个人的方式就是赋予每个人一样的权利,也就是以平权来实现公正。但这真的合乎平等原则吗?所谓的“同一条起跑线”,其根本目的是让人“跑”起来,每个人都要跑出一个“成绩”,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拉开的差距再大,起跑线都使得这种差距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公正的。更直白地说,它令我们仍然接受人是要分三六九等的,只不过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跑出来的。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核心。桑德尔指出这种赛跑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是不利于团结的,它会在社会成员间产生很多怨恨与嫉妒。而我还想给出的一个视角是,这样赋予所有人同样的权利和机遇,并不是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它实际上不能被称作“平等”。统一的标准仅仅造成平等的假象,它意味着对于不同的人,社会的苛刻程度大有不同。由此我试图给出另一种平等观,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价值多元的,它不会用统一的评价体系去对待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