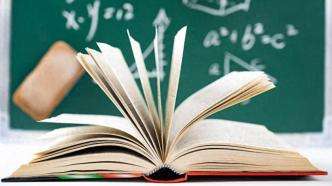冬日的天光和暖可爱,西湖景致正称心意。跨上单车,我来到北山路附近骑行。北风捎带寒气,又为阳光烘烤,扑在脸上,倒也觉出一丝爽利来,精神为之一振。
逆着时针的方向,自六公园一路行至曲院风荷,停了车,往湖畔走去。忽然想起,丰子恺先生的“湖畔小屋”正在北山街(原静江路)85号,与此处仅一步之遥。当下动了念头,想叩响那扇门。
从运河至西湖
丰子恺与杭州,尤其与西湖的渊源颇深。幼时投考,他在杭州做了五年师范生。毕业后,常趁工作间隙,自沪来杭散心。上世纪四十年代,举家迁入葛岭下的湖畔小屋,往来有鸿儒。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年重访,钩沉故人旧事。西湖于丰子恺而言,可谓第二故乡。
丰子恺,原名丰仁,生于桐乡石门镇,家邻京杭大运河。长于水乡的人,兜兜转转,一生总与水有缘。
1914年,丰仁赴杭,投考中等学校。去乡求学,便是面对一整个崭新的世界,其中有新学堂,新教员,新同窗。在此之前,搭乘火车,为第一重关卡。在《车厢社会》一文中,他回忆,当时听同乡人形容火车,不免心生惶恐,“以为这大概是炮弹流星似的凶猛唐突的东西,觉得可怕”。然而,一坐上后,他着迷于变幻窗景,星点车站,觉得新奇而有趣。第一重关卡,消解于搭火车“原来不过尔尔”的感悟,自此也明了“天下事往往如此”。
这位青年人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
念二年级时,因李叔同的鼓励,丰仁确定未来一生的志向。有一晚,他因公事寻李先生。话谈完,他听到轻而严肃的声音传来:“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听到大前辈如此肯定,丰仁“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后来,丰仁因文章练达,笔法出众,颇受单不庵先生的赏识,得名“子恺”。就这样,在杭州贡院,一个自桐乡石门而来的青年人,得了最初的滋养,为日后蜕变成大家丰子恺蓄力。
自石门湾到杭州的投考路线,不光丰子恺走过,丰家人亦是。其父丰斛泉为举人考试,每三年赴杭州贡院。“那时没有火车,便坐船去。运河直通杭州,约八九十里。在船中一宿,次日便到。于是在贡院附近租一个‘下处’,等候进场。”终于,丰斛泉在三十六岁那年考中。
父亲的经历,在年幼的丰仁看来,是模糊不清的。而等到丰子恺女儿这一辈投考,他旁观陪考,心情闲散,录下了种种有趣的情状。
坐船赴杭的路上,外头热闹非凡,考生只管拿出书来看。“从考毕到发表的几天之内,投考者之间的空气非常沉闷。有几个女生简直是寝食不安,茶饭无心。”等到开榜,差人去看,众人引颈企盼,希望听来一个好消息。就连丰子恺一个旁观者,也由衷感慨,仅凭一支自来水笔,无法描摹数秒间的空气的紧张。判决书从嘴里下来,几家欢喜几家愁,丰子恺变着法子安慰受了霹雳的人。“考取了学校的人都鼓着勇气,跑回家去取行李,雇人挑了,星夜启程跑到火车站,乘车来杭入学。”丰子恺不光在写子女辈,亦是回忆青年时代,自己第一次在广大世界施展身手的经历。
相聚湖畔小屋
经师范五年后,丰子恺赴海外留学十个月,归国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教书。工作间隙,他观察日常生活,偶得画稿,接连刊登,“子恺漫画”自此名声远播。
其中,我最欢喜的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月光下,窗内的靠椅茶几一览无余,只是不见交谈的人们。大量的留白,给这幅画赋予古韵。
赏读之余,不免咂摸出画里的人缘。丰子恺交友甚广,学生时代随老师步伐,工作后又因文艺作品,常与学者、作家交游。这一段段人缘,亦为西湖见证。
1947年3月11日,丰家迁入静江路85号,住进“一所简陋的泥地小平房”。丰子恺曾孙丰睿存有一张黑白老照片。石阶之上,满眼白墙,中置窄门,顶有黑瓦。里屋有三间正屋,天井两侧各有一间厢房。
别看小屋样貌平凡,地理位置极妙,毗邻西湖,且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湖畔小屋。据丰一吟回忆,这里环境幽静,门外隔着里西湖,正对孤山放鹤亭。丰子恺想到下联“门对孤山放鹤亭”,又由开明书店的老友章锡琛想出上联,凑成一副完整的对联——“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
我去拜访湖畔小屋时,早已不见丰家留下的痕迹。然而,曾经的湖畔小屋热闹得很。新朋老友相聚,最是欢欣。
七十多年前的春天,老友郑振铎来访湖畔小屋。阔别十年,老友隔着炮火与旧事,在人间天堂重逢,该有多少感慨与庆幸。
偏是老天也作美,丰子恺回忆那天,只说道:“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
畅饮之余,两人瞧见壁上一首苏步青寄来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多少坎坷往事已化烟尘,未来初见光芒。
想着这场夜酌,我走过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虽不语,但飘落的叶片,自会发出最清脆的声响。我听见落叶窸窣,也听见彼时欢笑。
栖息精神的角落
我住在杭州,每月都要游一趟西湖,然而,要论游西湖的老手,我远不及丰子恺。
若要来西湖写生,画家丰子恺会备上作画工具。画西湖,最先映入他脑海的是绿色。“于是我闭着两眼一看,固然看见浓绿的草木,充塞于西湖的四周,好像一条大而厚的绿绒毯子,包裹了湖上的诸山。”他预备浓重地涂抹绿的颜料,让那样平和的色彩,长久地留存于他的画面。
丰子恺不光看西湖,亦看西湖里的生灵。他曾与女儿及学生,一道雇船,穿过西湖,到雷峰塔西侧的白云庵去求签。四人在舟子的陪伴下,一路笑声不断,不知不觉来到湖中心。忽然,一条二尺长的大鱼跳上来,落进学生怀里。舟子一见,想捉来放进后艄,做当晚的佳肴。两个孩子高声喊放生,学生松了手,送大鱼归家。丰子恺留意到舟子那微妙的不快,于是设法安慰:“这是跳龙门的鲤鱼,鲤鱼跳进你的船里,你——(我看看他,又改了口)你的儿子好做官了。”一句轻快的吉祥话,吹散了弥漫在船里的不快。无论是湖里的鱼,还是湖上劳作的人,他都以一种温和的姿态,理解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处境。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每年春天来西湖,觉得西湖“一年美丽一年,一年漂亮一年,一年可爱一年”。依他看,旧时代的西湖,只能看山水,不能细想背后的人事故事。一旦细想,牵扯出私人公馆、楼台亭阁上被压迫的呻吟声,便失了兴致。而新旧时代的更替,仿佛为西子“斋戒沐浴”了一番,变得尽善尽美起来。他看到规范的买票处、工作的舟子,也看到明山秀水。
在杭州,丰子恺还时常忆及李叔同。1953年,在弘一法师故去十一载后,丰子恺与叶圣陶等人,在虎跑建造舍利石塔,纪念恩师,常来祭扫。历时四十六年绘制的《护生画集》,不仅凝聚着师生一同倡导的“护生即护心”理念,更回荡着师道传承的余响。其核心的慈悲与仁爱,与丰子恺在西湖边所观察到、所珍视的万物有灵、人间情味一脉相承。西湖,亦是他的精神栖息地。
思绪从历史中收回,我的眼前又是川流不息的北山街了。终究,我没有叩响湖畔小屋的那扇门,但丰子恺的艺术与人格,为我永久地打开了一扇看世情的窗。
冬日的天光和暖可爱,西湖景致正称心意。跨上单车,我来到北山路附近骑行。北风捎带寒气,又为阳光烘烤,扑在脸上,倒也觉出一丝爽利来,精神为之一振。
逆着时针的方向,自六公园一路行至曲院风荷,停了车,往湖畔走去。忽然想起,丰子恺先生的“湖畔小屋”正在北山街(原静江路)85号,与此处仅一步之遥。当下动了念头,想叩响那扇门。
从运河至西湖
丰子恺与杭州,尤其与西湖的渊源颇深。幼时投考,他在杭州做了五年师范生。毕业后,常趁工作间隙,自沪来杭散心。上世纪四十年代,举家迁入葛岭下的湖畔小屋,往来有鸿儒。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年重访,钩沉故人旧事。西湖于丰子恺而言,可谓第二故乡。
丰子恺,原名丰仁,生于桐乡石门镇,家邻京杭大运河。长于水乡的人,兜兜转转,一生总与水有缘。
1914年,丰仁赴杭,投考中等学校。去乡求学,便是面对一整个崭新的世界,其中有新学堂,新教员,新同窗。在此之前,搭乘火车,为第一重关卡。在《车厢社会》一文中,他回忆,当时听同乡人形容火车,不免心生惶恐,“以为这大概是炮弹流星似的凶猛唐突的东西,觉得可怕”。然而,一坐上后,他着迷于变幻窗景,星点车站,觉得新奇而有趣。第一重关卡,消解于搭火车“原来不过尔尔”的感悟,自此也明了“天下事往往如此”。
这位青年人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
念二年级时,因李叔同的鼓励,丰仁确定未来一生的志向。有一晚,他因公事寻李先生。话谈完,他听到轻而严肃的声音传来:“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听到大前辈如此肯定,丰仁“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后来,丰仁因文章练达,笔法出众,颇受单不庵先生的赏识,得名“子恺”。就这样,在杭州贡院,一个自桐乡石门而来的青年人,得了最初的滋养,为日后蜕变成大家丰子恺蓄力。
自石门湾到杭州的投考路线,不光丰子恺走过,丰家人亦是。其父丰斛泉为举人考试,每三年赴杭州贡院。“那时没有火车,便坐船去。运河直通杭州,约八九十里。在船中一宿,次日便到。于是在贡院附近租一个‘下处’,等候进场。”终于,丰斛泉在三十六岁那年考中。
父亲的经历,在年幼的丰仁看来,是模糊不清的。而等到丰子恺女儿这一辈投考,他旁观陪考,心情闲散,录下了种种有趣的情状。
坐船赴杭的路上,外头热闹非凡,考生只管拿出书来看。“从考毕到发表的几天之内,投考者之间的空气非常沉闷。有几个女生简直是寝食不安,茶饭无心。”等到开榜,差人去看,众人引颈企盼,希望听来一个好消息。就连丰子恺一个旁观者,也由衷感慨,仅凭一支自来水笔,无法描摹数秒间的空气的紧张。判决书从嘴里下来,几家欢喜几家愁,丰子恺变着法子安慰受了霹雳的人。“考取了学校的人都鼓着勇气,跑回家去取行李,雇人挑了,星夜启程跑到火车站,乘车来杭入学。”丰子恺不光在写子女辈,亦是回忆青年时代,自己第一次在广大世界施展身手的经历。
相聚湖畔小屋
经师范五年后,丰子恺赴海外留学十个月,归国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教书。工作间隙,他观察日常生活,偶得画稿,接连刊登,“子恺漫画”自此名声远播。
其中,我最欢喜的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月光下,窗内的靠椅茶几一览无余,只是不见交谈的人们。大量的留白,给这幅画赋予古韵。
赏读之余,不免咂摸出画里的人缘。丰子恺交友甚广,学生时代随老师步伐,工作后又因文艺作品,常与学者、作家交游。这一段段人缘,亦为西湖见证。
1947年3月11日,丰家迁入静江路85号,住进“一所简陋的泥地小平房”。丰子恺曾孙丰睿存有一张黑白老照片。石阶之上,满眼白墙,中置窄门,顶有黑瓦。里屋有三间正屋,天井两侧各有一间厢房。
别看小屋样貌平凡,地理位置极妙,毗邻西湖,且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湖畔小屋。据丰一吟回忆,这里环境幽静,门外隔着里西湖,正对孤山放鹤亭。丰子恺想到下联“门对孤山放鹤亭”,又由开明书店的老友章锡琛想出上联,凑成一副完整的对联——“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
我去拜访湖畔小屋时,早已不见丰家留下的痕迹。然而,曾经的湖畔小屋热闹得很。新朋老友相聚,最是欢欣。
七十多年前的春天,老友郑振铎来访湖畔小屋。阔别十年,老友隔着炮火与旧事,在人间天堂重逢,该有多少感慨与庆幸。
偏是老天也作美,丰子恺回忆那天,只说道:“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
畅饮之余,两人瞧见壁上一首苏步青寄来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多少坎坷往事已化烟尘,未来初见光芒。
想着这场夜酌,我走过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虽不语,但飘落的叶片,自会发出最清脆的声响。我听见落叶窸窣,也听见彼时欢笑。
栖息精神的角落
我住在杭州,每月都要游一趟西湖,然而,要论游西湖的老手,我远不及丰子恺。
若要来西湖写生,画家丰子恺会备上作画工具。画西湖,最先映入他脑海的是绿色。“于是我闭着两眼一看,固然看见浓绿的草木,充塞于西湖的四周,好像一条大而厚的绿绒毯子,包裹了湖上的诸山。”他预备浓重地涂抹绿的颜料,让那样平和的色彩,长久地留存于他的画面。
丰子恺不光看西湖,亦看西湖里的生灵。他曾与女儿及学生,一道雇船,穿过西湖,到雷峰塔西侧的白云庵去求签。四人在舟子的陪伴下,一路笑声不断,不知不觉来到湖中心。忽然,一条二尺长的大鱼跳上来,落进学生怀里。舟子一见,想捉来放进后艄,做当晚的佳肴。两个孩子高声喊放生,学生松了手,送大鱼归家。丰子恺留意到舟子那微妙的不快,于是设法安慰:“这是跳龙门的鲤鱼,鲤鱼跳进你的船里,你——(我看看他,又改了口)你的儿子好做官了。”一句轻快的吉祥话,吹散了弥漫在船里的不快。无论是湖里的鱼,还是湖上劳作的人,他都以一种温和的姿态,理解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处境。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每年春天来西湖,觉得西湖“一年美丽一年,一年漂亮一年,一年可爱一年”。依他看,旧时代的西湖,只能看山水,不能细想背后的人事故事。一旦细想,牵扯出私人公馆、楼台亭阁上被压迫的呻吟声,便失了兴致。而新旧时代的更替,仿佛为西子“斋戒沐浴”了一番,变得尽善尽美起来。他看到规范的买票处、工作的舟子,也看到明山秀水。
在杭州,丰子恺还时常忆及李叔同。1953年,在弘一法师故去十一载后,丰子恺与叶圣陶等人,在虎跑建造舍利石塔,纪念恩师,常来祭扫。历时四十六年绘制的《护生画集》,不仅凝聚着师生一同倡导的“护生即护心”理念,更回荡着师道传承的余响。其核心的慈悲与仁爱,与丰子恺在西湖边所观察到、所珍视的万物有灵、人间情味一脉相承。西湖,亦是他的精神栖息地。
思绪从历史中收回,我的眼前又是川流不息的北山街了。终究,我没有叩响湖畔小屋的那扇门,但丰子恺的艺术与人格,为我永久地打开了一扇看世情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