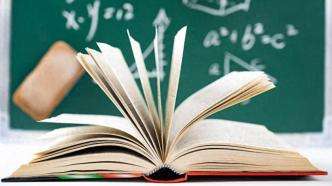作为《史记》七十列传的开篇之作,司马迁为何要为两位事迹可疑、史料匮乏的上古隐士立传,且将其置于众贤之首?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历史作家林聪舜在《〈史记〉的人物世界》中,以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命运为线索穿透迷雾,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解读为司马迁重建人间正义的精神宣言。
林聪舜在书中首先厘清了一个关键问题:司马迁为何选择伯夷、叔齐,这样的隐士作为列传之首?这背后藏着司马迁为《史记》立传的核心标准,也暗示了传首位置的深意。
林聪舜敏锐地指出,这一标准绝非简单的“尊孔”,而是司马迁的价值取舍。吴太伯、伯夷、叔齐虽属传说人物,但均被孔子称颂,他们身上“让国”的核心特质,恰好契合了司马迁的精神追求。在书中,林聪舜将这一选择与《史记》的整体结构相呼应: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贯穿其中的正是“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伯夷、叔齐拒绝继承王位,又以死反抗武王“以暴易暴”,这种对不义权力的决绝姿态,正是司马迁想要在列传开篇确立的价值标杆。
如果说立传标准是外在形式,那么司马迁与伯夷、叔齐的精神共鸣,则是《伯夷列传》成为传首的内在灵魂。孔子认为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司马迁却依据《采薇》佚诗与别传记载,坚持这两位隐士必有“怨”。在伯夷、叔齐眼中,武王伐纣并非“吊民伐罪”的义举,而是以暴力取代暴力的暴行。当天下宗周、无人敢质疑武王时,他们以“不食周粟”的方式殉道,用死亡嘲讽强权,这份坚守与孤独,怎能不藏着怨怼?
司马迁对“怨”的坚持,本质上是自我情感的投射。作为史官,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因替李陵辩解惨遭宫刑。他身处汉王朝的政治深渊,亲眼看见恶无恶报的现实。这种不公让他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正义法则产生了根本性质疑。
伯夷、叔齐的遭遇,成为司马迁抒发悲愤的载体。书中提到司马迁不信《采薇》之诗的细节,却深信黑暗世道中,坚守理想者必然有怨。这份“怨”,是对强权的反抗,是对不公的控诉,更是对自身命运的悲叹。将《伯夷列传》置于传首,司马迁实则是在开篇就亮明自己的立场,他要为天下受委屈的正义之士发声,让他们的“怨”被后世听见。
《伯夷列传》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并非人物事迹本身,而是司马迁借其引出的关于正义的议论。林聪舜在《〈史记〉的人物世界》中将这部分解读为“司马迁如何面对天道破产的困境”,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文中一口气列举了无数现实悖论,直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虚伪,将“天道破产”的困境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汉王朝的统治下,掌权者将仁义道德作为剥削民众的工具,所谓“王道”“天道”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作为这种不公的受害者,司马迁的悲愤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为天下苍生的呐喊。
但司马迁并未陷入虚无。司马迁提出了天道崩塌后的解决方案,以史笔为人间伸张正义。司马迁认为,道义本身具有独立价值,“各从其志”“从吾所好”的自我抉择,足以支撑人在混浊世事中保持尊严。而史家的使命,就是让这些坚守道义的人“名传后世”。
司马迁要效法圣人,以公正的史笔“替天行道”。天道无法给予的公平,他将通过《史记》来实现;忠臣义士在现实中遭受的不公,他用各种人物生动的事迹来展示自己的理念。他要以这部史书为准则,重建人间的正义秩序,让“砥行立名者”得以不朽。这种将历史写作视为正义实践的担当,正是《史记》超越普通史书的伟大之处。
从精神内核来看,《伯夷列传》奠定了整部《史记》的情感基调。司马迁在书中既表达了对天道不公的悲愤,又展现了重建正义的决心;既同情底层贤士的遭遇,又坚守史家的良知与担当。这种精神在后续的《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篇章中不断延续,形成了《史记》独特的人文精神。
两千多年来,伯夷、叔齐的形象在传统士大夫心中始终高洁,却少有人真正读懂司马迁的微旨深义。林聪舜让我们明白,司马迁将这两位隐士置于列传之首,并非单纯表彰他们的让国之举,而是要通过他们宣告自己的历史抱负,当天道不公、强权横行时,史家的笔可以成为正义的武器,文人的坚守可以成为精神的灯塔。而《史记》中,众多性格各异,不同命运的大人物小人物,都成为司马迁对于人性天道、伦理的终极注脚。
作为《史记》七十列传的开篇之作,司马迁为何要为两位事迹可疑、史料匮乏的上古隐士立传,且将其置于众贤之首?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历史作家林聪舜在《〈史记〉的人物世界》中,以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命运为线索穿透迷雾,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解读为司马迁重建人间正义的精神宣言。
林聪舜在书中首先厘清了一个关键问题:司马迁为何选择伯夷、叔齐,这样的隐士作为列传之首?这背后藏着司马迁为《史记》立传的核心标准,也暗示了传首位置的深意。
林聪舜敏锐地指出,这一标准绝非简单的“尊孔”,而是司马迁的价值取舍。吴太伯、伯夷、叔齐虽属传说人物,但均被孔子称颂,他们身上“让国”的核心特质,恰好契合了司马迁的精神追求。在书中,林聪舜将这一选择与《史记》的整体结构相呼应: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贯穿其中的正是“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伯夷、叔齐拒绝继承王位,又以死反抗武王“以暴易暴”,这种对不义权力的决绝姿态,正是司马迁想要在列传开篇确立的价值标杆。
如果说立传标准是外在形式,那么司马迁与伯夷、叔齐的精神共鸣,则是《伯夷列传》成为传首的内在灵魂。孔子认为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司马迁却依据《采薇》佚诗与别传记载,坚持这两位隐士必有“怨”。在伯夷、叔齐眼中,武王伐纣并非“吊民伐罪”的义举,而是以暴力取代暴力的暴行。当天下宗周、无人敢质疑武王时,他们以“不食周粟”的方式殉道,用死亡嘲讽强权,这份坚守与孤独,怎能不藏着怨怼?
司马迁对“怨”的坚持,本质上是自我情感的投射。作为史官,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因替李陵辩解惨遭宫刑。他身处汉王朝的政治深渊,亲眼看见恶无恶报的现实。这种不公让他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正义法则产生了根本性质疑。
伯夷、叔齐的遭遇,成为司马迁抒发悲愤的载体。书中提到司马迁不信《采薇》之诗的细节,却深信黑暗世道中,坚守理想者必然有怨。这份“怨”,是对强权的反抗,是对不公的控诉,更是对自身命运的悲叹。将《伯夷列传》置于传首,司马迁实则是在开篇就亮明自己的立场,他要为天下受委屈的正义之士发声,让他们的“怨”被后世听见。
《伯夷列传》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并非人物事迹本身,而是司马迁借其引出的关于正义的议论。林聪舜在《〈史记〉的人物世界》中将这部分解读为“司马迁如何面对天道破产的困境”,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在文中一口气列举了无数现实悖论,直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虚伪,将“天道破产”的困境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汉王朝的统治下,掌权者将仁义道德作为剥削民众的工具,所谓“王道”“天道”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作为这种不公的受害者,司马迁的悲愤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为天下苍生的呐喊。
但司马迁并未陷入虚无。司马迁提出了天道崩塌后的解决方案,以史笔为人间伸张正义。司马迁认为,道义本身具有独立价值,“各从其志”“从吾所好”的自我抉择,足以支撑人在混浊世事中保持尊严。而史家的使命,就是让这些坚守道义的人“名传后世”。
司马迁要效法圣人,以公正的史笔“替天行道”。天道无法给予的公平,他将通过《史记》来实现;忠臣义士在现实中遭受的不公,他用各种人物生动的事迹来展示自己的理念。他要以这部史书为准则,重建人间的正义秩序,让“砥行立名者”得以不朽。这种将历史写作视为正义实践的担当,正是《史记》超越普通史书的伟大之处。
从精神内核来看,《伯夷列传》奠定了整部《史记》的情感基调。司马迁在书中既表达了对天道不公的悲愤,又展现了重建正义的决心;既同情底层贤士的遭遇,又坚守史家的良知与担当。这种精神在后续的《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篇章中不断延续,形成了《史记》独特的人文精神。
两千多年来,伯夷、叔齐的形象在传统士大夫心中始终高洁,却少有人真正读懂司马迁的微旨深义。林聪舜让我们明白,司马迁将这两位隐士置于列传之首,并非单纯表彰他们的让国之举,而是要通过他们宣告自己的历史抱负,当天道不公、强权横行时,史家的笔可以成为正义的武器,文人的坚守可以成为精神的灯塔。而《史记》中,众多性格各异,不同命运的大人物小人物,都成为司马迁对于人性天道、伦理的终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