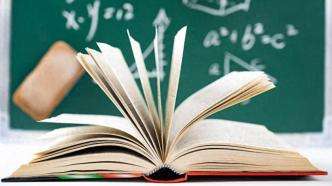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这个灵魂更加饱满。”
今年秋天,王玉珍带着她的新书《我恋禾谷》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签售会,书中收录了王玉珍创作的10篇文章,这些文章当中,有些曾发表在与新书同名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去到签售现场的读者有与她年龄相仿的老人,也有从线上追到线下的年轻人。这位70岁老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她笔下的“故人故事与柴米油盐”,意外地走进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心里,年轻人称她的作品是“老奶文学”,爱上了她字里行间的朴素与挚诚。面对排队等候的读者,她一边签名一边略带歉意地说:“手有点抖,字磕碜点,你们凑合看。”
2023年,68岁的王玉珍在家人劝说下,终于结束了陀螺般转动不停的生活。在此之前,她当过乡村教师,当过基层公务员,退休后依然辗转于打工、做小买卖之间。为了消解突然闲下来的生活的无聊,在外甥女的帮助下,王玉珍在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最开始,王玉珍在平台上学手工,学做菜。后来,王玉珍发现平台上有很多博主在记录生活、回忆往事,这让她有了想要写点什么的念头。就这样,一篇怀念母亲的文字,经由外甥女帮忙发布到名为“我恋禾谷”的社交平台账号,帖文收获的关注令王玉珍欣喜,也给了她继续创作的动力。她后续连载创作的万字长文《老伴儿的生平》,获得了社交平台写作大赛的奖项,也吸引了媒体和出版社的关注。
如今,王玉珍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积攒了近10万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王玉珍给自己取了个“我恋禾谷”的网名,她在平台上介绍自己“无文学慧根,无文字功底,无创作灵感”,发布的多为记录上一代人与事的文本。一位退休老人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那些属于过去的故事,为何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带着这些疑问,新京报记者与“我恋禾谷”本人王玉珍展开对话,讲述从退休老人到创作者的转变,以及她笔下那些在家乡土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就是一个比较热爱写故事的老年写作者”
新京报:从退休老人,到在网上发笔记,再到成为一个作家,你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转变吗?
王玉珍:别这么说,我诚惶诚恐,我不是作家,充其量就是一个有兴趣,比较热爱写故事的一个老年写作者。对生活,我现在很适应了。我之前做的小生意,从新冠(疫情)开始就效益不太好。我儿子和我女儿说,我年岁大了,也不让我做,就关了。像我们都忙了一辈子,从我退休以后,一下子闲下来,反倒是很茫然无措的,很不适应的,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生活就充实起来了,甚至每天都有安排。每天我就写1000字,发1000字,有的时候都觉着时间不够用,这种感觉在之前是没有的。
新京报: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
王玉珍:就是觉着忙了起来,其次就是精神上的变化。说得文雅一点,比如说过去情绪上的东西,比如说孤独,对故去亲人的一种怀念,这种情绪(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消解。因为我不大习惯跟别人说这些事儿。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灵魂更加饱满。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新结识了一些朋友,比如说媒体人、编辑们,包括网友,通过跟网友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就说,“奶奶,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社交平台看你的笔记。我就觉得我应该向你学习。今天我要去考试了,我要好好考试,今后我也要好好地念书。你看,你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学习,现在你老了,实际上你还是在学习,在成长,我们没脸说自己不应该努力。”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我就觉着,我的文字被别人看见是会影响别人的,就有点诚惶诚恐的。其实一开始写就是哄着我自己玩,有很大的随意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可能不想写了,就草草地写写那个人物我也就收场了。这样我就想,我应该把它写好一点。
新京报:之前参加过签售会吗?
王玉珍:我没参加过,也没看着过。但是你看,有一个小女孩还给了我一块她编织的茶杯垫,还有给我写信的,还有给我橙子的,暖贴的。我觉着他们都很热情、很好。他们是通过我的文字认识我的,他们读了我的文字,对我文字里边的那些故事和人物有感,可能他们是热爱,或者叫喜欢故事里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其实离他们都不太远。也可能就是他们这样阅读,可以唤起他们的亲情或者是某种记忆。有的场景,或者有的画面可能都听他家里的老人说过,他们是通过文字,通过我的故事认识我的,因为喜欢故事里的人和事儿,进而成为我的粉丝,关注我。
新京报:你参加了好几场签售会,也遇到了一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也是奶奶级的读者,她们可能没有写下她们的故事,你会不会鼓励她们像你一样去写故事,然后发到网上去?
王玉珍:我会鼓励她们,在我社交平台上留言的人,也有很多跟我年龄(相似),有退休的,有一个好像还是大学老师,她们都很有文化的。“这些故事我也想写,但是没有勇气,觉得我这东西写了,是不是没人看呢?”“我这东西能不能写好?”在(签售会)现场也有人说,“我可以说,你就是我的榜样。”我就跟她们说,不管有人看没人看,不管给钱不给钱,也不管能不能出书,你要有这个念头,你就拿起笔来写,肯定有收获。我都能做到,你有啥做不到的?
“‘我恋禾谷’没特殊含义,想起它就用了”
新京报:为什么要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命名为“我恋禾谷”?
王玉珍:其实这个书出的时候,我的原意是想叫《总有春天再相逢》。因为书里有一篇写我跟我老伴儿的事儿,那个文章的题目,就叫《总有春天再相逢》,而且我也觉着我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物。我写的每一个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通过文字和他们的一次相逢。但最后编辑认为还是《我恋禾谷》好,人家是专业的,所以我说“听专业人士”的。
新京报:“我恋禾谷”是你的笔名,也是你的社交平台网名,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恋禾谷”的含义?
王玉珍:“我恋禾谷”出自《大秦帝国》那个小说里边的两句招魂词,是老秦人让战死在疆场的战士魂归故里的招魂词。其中的两句词是“恋我禾谷,卧我黄土”。几年前,我中专的同学要组一个微信群,那时候我不会上网,她就来帮我弄,她说:“你得起个网名。”我正在看这本书,这两句话我就很喜欢,我说,那我就叫“我恋黄土”。好几个同学就乐,他们一致否定我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你就是叫“我恋红薯”“我恋白薯”,你也别叫“我恋黄土”。我想人家说得有道理,我说我改改,就用了另外一句“我恋禾谷”,没有特殊的含义,就是恰好想起了它,就用了它。
新京报:这本书里面一共有十个故事。你将《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第一篇。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篇?
王玉珍:我先简单地说说这个故事,为什么叫《60块大洋的爱情》?是因为我父亲跟母亲实际上是一个行政村的。在我父亲两岁,我母亲出生100天的时候,他们两家就定了娃娃亲了。我爷爷给了我姥姥60块大洋。这是我父母的定情礼。后来我母亲16岁嫁给我父亲,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生活了57年。我父亲活到七十多岁没的,我母亲活到91岁。《60块大洋的爱情》就是从这60块大洋开始说,他们的一生颠沛流离也好,艰难困苦也好,但是恩恩爱爱地走完了这一生。这样一个故事之所以放在前边,是因为我写的这些人物里边最亲的是我的父母,最近的是我的老伴儿。因为父母是长辈,所以我就把《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了第一篇。
新京报:你写的这些浪漫的爱情,包括你通过文字的方式纪念你逝去的老伴儿,你在文字里和他重逢。你期待的或者是你理解的浪漫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
王玉珍:其实我们俩的婚姻和恋爱算不上浪漫。你就想象他是个木匠,小学毕业上了技校,我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老师。这样的两个人,没有那种花前月下、风花雪月,没有值得人羡慕的浪漫,甚至我们结婚的时候,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我老伴订婚时说:“要不咱俩去照个相”。我说:“咱俩这形象,还是免了。”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尽管恋爱的过程不浪漫,但是在结婚以后,在这35年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中,我们就很默契了。虽然我老伴儿长得五大三粗的,但他也有心细的地儿。比如说生日的时候他会给我买个小礼物,比如说给我买个金戒指、买个金手链、买个金项链这些。他觉得这比买花强,将来给孩子也是个东西,是吧?我就觉着,能够平平安安,这样平静地生活,就很知足了。
新京报:你的文章收获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在与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你会认为年轻人的思路有所不同吗?
王玉珍:有不一样,比如说我写《风中消失的梅》,那是一个换亲的故事,是农村的两家(换亲),可能现在城里的年轻人都不大能懂。农村的两家互相用自己的闺女给儿子换媳妇儿。这种换亲大都是男方的男孩子有缺陷,都是用他妹妹或姐姐出嫁换亲。宋家和艾家这两家的婚姻,两个男孩子都有缺陷,宋学林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这是他的一个缺陷,所以他说不上媳妇儿。艾春是因为长相不太好,人也有些木讷,所以也说不上媳妇儿。这两家的婚姻中,艾红跟宋学林过得还凑合,宋小梅是宋学林的妹妹,长得漂亮,她结婚以后,艾春知道她长得漂亮,所以就把她看得很紧,一种禁锢的生活状态,宋小梅对这种婚姻状态很不满意,曾经绝望过,曾经精神失常。后来到50岁的时候,她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她也出走了。很多年轻的网友就说,换亲都是女孩做了牺牲品。她们不会做这种牺牲,不管哥哥说不说得上媳妇儿,坚决不会做这种选择,这是现在女孩的想法。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可能就没有别的选择。跟不同年龄的人沟通,在一个人物的看法上就有区别。
“我是因为写作,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
新京报:《我恋禾谷》出版后,你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玉珍:这本书写完后,我就开始写下一本。写的是我自己,就是从我出生写到我老伴去世。写我生下来的时候,我母亲因为有严重的妇科病,生了八个孩子都是早产。包括我生下来都没有指甲盖,没有头发。最后八个孩子活下来三个,我是我母亲生的第七个孩子。小的时候差一点就死了,我1955年出生,到1960年前后,我挨过饿,得过一次肺炎,中过一次暑。从小时候到我念书,我写了怎么读书,怎么求学,写我还在武汉给我小姨看过一年孩子,那年我17岁,一直到后来在我们庄里做民办学校老师。然后我上中专,到后来上了大专,上了本科,当了老师,后来又结婚,嫁给我老头,一直到后来当公务员,49岁退休。退休以后我有三年在私企打工,有三年是在北京潘家园卖古董,还有十多年是我自己做一个加工包装盒的小生意,一直到上社交平台写笔记、发笔记,一直到得奖,一直到出书,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这一辈子,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说过去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经历,也许验证了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有某种新的可能性。
王玉珍:整个的社会氛围对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或者说老年人的意愿、尊严会得到尊重或得到实现,我觉着这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一种表现。老年人的问题主要是空虚和孤独。我如果不写作,有时也是觉着很无聊的。我们楼下有一个小花园,那里有一个大平台,每天都有一群老年人,老太太多,老头少,在那里坐着。有的老太太除了中午回去吃个饭,就会在那里一坐坐一天。其实就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她很孤独,很空虚的。现在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年轻人来去都匆匆忙忙的,包括子女能够倾听老人絮絮叨叨的都很少。很多老人也不是没有子女,但是感觉他们已经被世界遗忘了,这个世界离他们越来越远。我是因为写作这些事儿,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所以我希望,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精神上,作为子女,如果能抽出时间的话,听家中老人絮叨一会儿,常回家看看他们。很多老人就是这么等着,等着出太阳了跟大伙坐坐,等着孩子们回来看看他。但实际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就是在等死。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应该让老年人在精神上更丰满一点。
“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这个灵魂更加饱满。”
今年秋天,王玉珍带着她的新书《我恋禾谷》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签售会,书中收录了王玉珍创作的10篇文章,这些文章当中,有些曾发表在与新书同名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去到签售现场的读者有与她年龄相仿的老人,也有从线上追到线下的年轻人。这位70岁老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她笔下的“故人故事与柴米油盐”,意外地走进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心里,年轻人称她的作品是“老奶文学”,爱上了她字里行间的朴素与挚诚。面对排队等候的读者,她一边签名一边略带歉意地说:“手有点抖,字磕碜点,你们凑合看。”
2023年,68岁的王玉珍在家人劝说下,终于结束了陀螺般转动不停的生活。在此之前,她当过乡村教师,当过基层公务员,退休后依然辗转于打工、做小买卖之间。为了消解突然闲下来的生活的无聊,在外甥女的帮助下,王玉珍在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最开始,王玉珍在平台上学手工,学做菜。后来,王玉珍发现平台上有很多博主在记录生活、回忆往事,这让她有了想要写点什么的念头。就这样,一篇怀念母亲的文字,经由外甥女帮忙发布到名为“我恋禾谷”的社交平台账号,帖文收获的关注令王玉珍欣喜,也给了她继续创作的动力。她后续连载创作的万字长文《老伴儿的生平》,获得了社交平台写作大赛的奖项,也吸引了媒体和出版社的关注。
如今,王玉珍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积攒了近10万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王玉珍给自己取了个“我恋禾谷”的网名,她在平台上介绍自己“无文学慧根,无文字功底,无创作灵感”,发布的多为记录上一代人与事的文本。一位退休老人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那些属于过去的故事,为何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带着这些疑问,新京报记者与“我恋禾谷”本人王玉珍展开对话,讲述从退休老人到创作者的转变,以及她笔下那些在家乡土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就是一个比较热爱写故事的老年写作者”
新京报:从退休老人,到在网上发笔记,再到成为一个作家,你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转变吗?
王玉珍:别这么说,我诚惶诚恐,我不是作家,充其量就是一个有兴趣,比较热爱写故事的一个老年写作者。对生活,我现在很适应了。我之前做的小生意,从新冠(疫情)开始就效益不太好。我儿子和我女儿说,我年岁大了,也不让我做,就关了。像我们都忙了一辈子,从我退休以后,一下子闲下来,反倒是很茫然无措的,很不适应的,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生活就充实起来了,甚至每天都有安排。每天我就写1000字,发1000字,有的时候都觉着时间不够用,这种感觉在之前是没有的。
新京报: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
王玉珍:就是觉着忙了起来,其次就是精神上的变化。说得文雅一点,比如说过去情绪上的东西,比如说孤独,对故去亲人的一种怀念,这种情绪(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消解。因为我不大习惯跟别人说这些事儿。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灵魂更加饱满。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新结识了一些朋友,比如说媒体人、编辑们,包括网友,通过跟网友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就说,“奶奶,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社交平台看你的笔记。我就觉得我应该向你学习。今天我要去考试了,我要好好考试,今后我也要好好地念书。你看,你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学习,现在你老了,实际上你还是在学习,在成长,我们没脸说自己不应该努力。”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我就觉着,我的文字被别人看见是会影响别人的,就有点诚惶诚恐的。其实一开始写就是哄着我自己玩,有很大的随意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可能不想写了,就草草地写写那个人物我也就收场了。这样我就想,我应该把它写好一点。
新京报:之前参加过签售会吗?
王玉珍:我没参加过,也没看着过。但是你看,有一个小女孩还给了我一块她编织的茶杯垫,还有给我写信的,还有给我橙子的,暖贴的。我觉着他们都很热情、很好。他们是通过我的文字认识我的,他们读了我的文字,对我文字里边的那些故事和人物有感,可能他们是热爱,或者叫喜欢故事里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其实离他们都不太远。也可能就是他们这样阅读,可以唤起他们的亲情或者是某种记忆。有的场景,或者有的画面可能都听他家里的老人说过,他们是通过文字,通过我的故事认识我的,因为喜欢故事里的人和事儿,进而成为我的粉丝,关注我。
新京报:你参加了好几场签售会,也遇到了一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也是奶奶级的读者,她们可能没有写下她们的故事,你会不会鼓励她们像你一样去写故事,然后发到网上去?
王玉珍:我会鼓励她们,在我社交平台上留言的人,也有很多跟我年龄(相似),有退休的,有一个好像还是大学老师,她们都很有文化的。“这些故事我也想写,但是没有勇气,觉得我这东西写了,是不是没人看呢?”“我这东西能不能写好?”在(签售会)现场也有人说,“我可以说,你就是我的榜样。”我就跟她们说,不管有人看没人看,不管给钱不给钱,也不管能不能出书,你要有这个念头,你就拿起笔来写,肯定有收获。我都能做到,你有啥做不到的?
“‘我恋禾谷’没特殊含义,想起它就用了”
新京报:为什么要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命名为“我恋禾谷”?
王玉珍:其实这个书出的时候,我的原意是想叫《总有春天再相逢》。因为书里有一篇写我跟我老伴儿的事儿,那个文章的题目,就叫《总有春天再相逢》,而且我也觉着我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物。我写的每一个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通过文字和他们的一次相逢。但最后编辑认为还是《我恋禾谷》好,人家是专业的,所以我说“听专业人士”的。
新京报:“我恋禾谷”是你的笔名,也是你的社交平台网名,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恋禾谷”的含义?
王玉珍:“我恋禾谷”出自《大秦帝国》那个小说里边的两句招魂词,是老秦人让战死在疆场的战士魂归故里的招魂词。其中的两句词是“恋我禾谷,卧我黄土”。几年前,我中专的同学要组一个微信群,那时候我不会上网,她就来帮我弄,她说:“你得起个网名。”我正在看这本书,这两句话我就很喜欢,我说,那我就叫“我恋黄土”。好几个同学就乐,他们一致否定我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你就是叫“我恋红薯”“我恋白薯”,你也别叫“我恋黄土”。我想人家说得有道理,我说我改改,就用了另外一句“我恋禾谷”,没有特殊的含义,就是恰好想起了它,就用了它。
新京报:这本书里面一共有十个故事。你将《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第一篇。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篇?
王玉珍:我先简单地说说这个故事,为什么叫《60块大洋的爱情》?是因为我父亲跟母亲实际上是一个行政村的。在我父亲两岁,我母亲出生100天的时候,他们两家就定了娃娃亲了。我爷爷给了我姥姥60块大洋。这是我父母的定情礼。后来我母亲16岁嫁给我父亲,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生活了57年。我父亲活到七十多岁没的,我母亲活到91岁。《60块大洋的爱情》就是从这60块大洋开始说,他们的一生颠沛流离也好,艰难困苦也好,但是恩恩爱爱地走完了这一生。这样一个故事之所以放在前边,是因为我写的这些人物里边最亲的是我的父母,最近的是我的老伴儿。因为父母是长辈,所以我就把《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了第一篇。
新京报:你写的这些浪漫的爱情,包括你通过文字的方式纪念你逝去的老伴儿,你在文字里和他重逢。你期待的或者是你理解的浪漫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
王玉珍:其实我们俩的婚姻和恋爱算不上浪漫。你就想象他是个木匠,小学毕业上了技校,我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老师。这样的两个人,没有那种花前月下、风花雪月,没有值得人羡慕的浪漫,甚至我们结婚的时候,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我老伴订婚时说:“要不咱俩去照个相”。我说:“咱俩这形象,还是免了。”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尽管恋爱的过程不浪漫,但是在结婚以后,在这35年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中,我们就很默契了。虽然我老伴儿长得五大三粗的,但他也有心细的地儿。比如说生日的时候他会给我买个小礼物,比如说给我买个金戒指、买个金手链、买个金项链这些。他觉得这比买花强,将来给孩子也是个东西,是吧?我就觉着,能够平平安安,这样平静地生活,就很知足了。
新京报:你的文章收获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在与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你会认为年轻人的思路有所不同吗?
王玉珍:有不一样,比如说我写《风中消失的梅》,那是一个换亲的故事,是农村的两家(换亲),可能现在城里的年轻人都不大能懂。农村的两家互相用自己的闺女给儿子换媳妇儿。这种换亲大都是男方的男孩子有缺陷,都是用他妹妹或姐姐出嫁换亲。宋家和艾家这两家的婚姻,两个男孩子都有缺陷,宋学林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这是他的一个缺陷,所以他说不上媳妇儿。艾春是因为长相不太好,人也有些木讷,所以也说不上媳妇儿。这两家的婚姻中,艾红跟宋学林过得还凑合,宋小梅是宋学林的妹妹,长得漂亮,她结婚以后,艾春知道她长得漂亮,所以就把她看得很紧,一种禁锢的生活状态,宋小梅对这种婚姻状态很不满意,曾经绝望过,曾经精神失常。后来到50岁的时候,她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她也出走了。很多年轻的网友就说,换亲都是女孩做了牺牲品。她们不会做这种牺牲,不管哥哥说不说得上媳妇儿,坚决不会做这种选择,这是现在女孩的想法。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可能就没有别的选择。跟不同年龄的人沟通,在一个人物的看法上就有区别。
“我是因为写作,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
新京报:《我恋禾谷》出版后,你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玉珍:这本书写完后,我就开始写下一本。写的是我自己,就是从我出生写到我老伴去世。写我生下来的时候,我母亲因为有严重的妇科病,生了八个孩子都是早产。包括我生下来都没有指甲盖,没有头发。最后八个孩子活下来三个,我是我母亲生的第七个孩子。小的时候差一点就死了,我1955年出生,到1960年前后,我挨过饿,得过一次肺炎,中过一次暑。从小时候到我念书,我写了怎么读书,怎么求学,写我还在武汉给我小姨看过一年孩子,那年我17岁,一直到后来在我们庄里做民办学校老师。然后我上中专,到后来上了大专,上了本科,当了老师,后来又结婚,嫁给我老头,一直到后来当公务员,49岁退休。退休以后我有三年在私企打工,有三年是在北京潘家园卖古董,还有十多年是我自己做一个加工包装盒的小生意,一直到上社交平台写笔记、发笔记,一直到得奖,一直到出书,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这一辈子,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说过去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经历,也许验证了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有某种新的可能性。
王玉珍:整个的社会氛围对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或者说老年人的意愿、尊严会得到尊重或得到实现,我觉着这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一种表现。老年人的问题主要是空虚和孤独。我如果不写作,有时也是觉着很无聊的。我们楼下有一个小花园,那里有一个大平台,每天都有一群老年人,老太太多,老头少,在那里坐着。有的老太太除了中午回去吃个饭,就会在那里一坐坐一天。其实就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她很孤独,很空虚的。现在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年轻人来去都匆匆忙忙的,包括子女能够倾听老人絮絮叨叨的都很少。很多老人也不是没有子女,但是感觉他们已经被世界遗忘了,这个世界离他们越来越远。我是因为写作这些事儿,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所以我希望,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精神上,作为子女,如果能抽出时间的话,听家中老人絮叨一会儿,常回家看看他们。很多老人就是这么等着,等着出太阳了跟大伙坐坐,等着孩子们回来看看他。但实际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就是在等死。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应该让老年人在精神上更丰满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