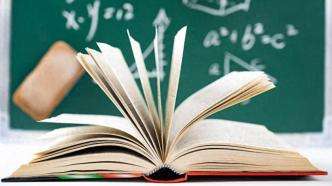千百年来,苏轼的诗文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文化符号。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东坡之眼:苏轼的艺术精神与绘画世界》(以下简称《东坡之眼》)一书中,作者金哲为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切入这位千古文人——以“画”为线索,串联起苏轼的人生轨迹、精神变迁与时代风骨,编织出宋代书画史的脉络。
作者与苏轼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让我们看到,读懂那些藏在画里的“心事”,是读懂苏轼精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经常要“回到”苏轼那里
读书周刊:您曾说:“怀念一个人,那就时不时写写他。”从陆续写了几篇关于苏轼的文章,到完成《东坡之眼》这本书,您的“怀念”是否从一种情感共鸣升华为一种精神对话?
金哲为:苏轼总在不经意间与我产生联结,比如,中秋时节、七月寄望等,有很多让我对苏轼产生联想的时刻。这种联想算不上深刻的精神对话,但用一本书从绘画这个独特的视角来切入他的精神世界,让我能更深入地贴近他。之前写的有关苏轼的文章主题都不同,比较零散,而《东坡之眼》用书的形式来呈现,让我的探索更系统、更深入。
苏轼太过丰富,在很多方面都成就斐然,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也有鲜明的变化,值得后人不断去挖掘。未来,我仍会持续关注与他相关的内容。
读书周刊:“如果一个人确实看到了某些未曾有人涉足的角落,那自然有为拼图全局补上一角的必要”,从苏轼的阅画经历这一角来观察“太过丰富”的苏轼,您如何发现并确信这一角的独特价值?
金哲为:研究中国艺术史就会发现,苏轼是绕不开的。他最早提出了文人画概念。不管是看元代的还是明清的艺术史,会发现后人经常提到他的画论。我之前写沈周时也发现,沈周会经常讲到苏轼,所以经常要“回到”苏轼那里。这让我好奇:苏轼是怎么成为文人画概念的提倡者的?他是如何练就看画的眼睛的?他看过哪些画、有过哪些收藏,又是谁带他走进绘画的世界?这些都是我想要探索的。
从绘画角度切入苏轼,是个很好的选择。看画经历贯穿其一生: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与弟弟苏辙游成都大慈寺看画,题写“精妙冠世”评价唐代的壁画作品,这是现存最早的东坡石刻;他去世前20多天,仍有观赏龙画的记载。相比之下,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诗词创作,时间跨度不及他的观画经历。更重要的是,不同时期他看的画、关于画的文字,都对应着他当时的人生处境和思想状态。尤其是乌台诗案后,他不太敢直言时政了,而艺术则成了安全的表达出口。
读书周刊:在我们熟知的诗文之外,艺术是苏轼情感与思想的另一重镜像。
金哲为:他后期的题画诗与画论看似聚焦艺理,实则暗藏对时政、世风与学风的隐晦评判。这些委婉的表达,有时在他的常规诗文里难觅踪迹,却能在他的艺术论述中得以窥见。
心境变化的鲜活写照
读书周刊:您在整理苏轼散落的画论时,不仅要从题画诗、书信等文字里搜集,还要结合具体语境去理解,这个过程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金哲为:苏轼没有专门写过系统的画论。他关于绘画的观点,散落在题画诗、写给友人的书信或悼念文里。比如,“胸有成竹”这个说法,出自他悼念表兄兼好友文同(字与可)的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强调画家创作前需对竹子有深刻观察和完整构思。他从没有刻意为绘画立说,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的零星论述搜集起来,这是难度很高的工作。接着,对他的很多观点,还需要回归当时的具体语境去理解与转化,其中的难度也不小。
读书周刊: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一些时刻让您感到自己与这位千古文人产生了超越时空的神交?
金哲为:这样的时刻蛮多的。比如,南宋马远的《水图》,明代鉴赏家认为马远继承了苏轼主张的画水应“尽水之变”,描绘的是苏轼所说的“活水”。但细读苏轼《画水记》会发现,他推崇的是“奔流湍急、随山石曲折而变”的水,与马远《水图》里的水有明显差异。马远画水大多没有山石,主要表现水本身的多样变化。
这背后是不同时期画水风格的转变:从北宋中晚期到南宋中期,文人对“水”的理解在改变。苏轼强调水借山石显其变,而南宋时人们更倾向于展现水的“本性之变”,无须依托他物。这里还可引申出更深层的解读:苏轼谈水,从来不只是艺术层面的探讨。他在《东坡易传》等哲学著作中也常以水为喻,而他的一生恰如他推崇的水——屡遭波折、被迫应变,却始终守住本心、奔涌向前,水的形态里藏着他的人生写照与情感倾向。
读书周刊:水已不仅仅是现实世界或艺术范畴的水,还承载着苏轼的人生。
金哲为:比如,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初见时会困惑木头为何画得奇奇怪怪,连他的好友米芾都评价其“无端奇崛”,认为只是苏轼“胸中意气”的随性抒发。其实画中苏轼暗藏着巧思,如他在题跋中的那句“散木支离得自全”。“散木”一词源自《庄子》,苏轼熟读《庄子》,曾说庄子道尽了他未说之言。庄子笔下的“散木”是“不材之木”,因枝干无用而免遭砍伐,得以保全自身。这幅画里的枯木,正是苏轼对庄子思想的艺术化表达。
再比如,苏轼一生大概见过三幅《秋山平远图》,其中两幅有他的题诗。画作题目相同、内容相近,但苏轼在两首题诗里的心境很不一样,反映了他人生不同时期的处境与想法。早年题诗时,他看到的画是非常温馨的田园生活景象,藏着他归隐田园、回归理想居所的向往;当这心愿终成奢望,再看相似的画,他的描述已变成“乱山无境”,是理想落空的怅然。明明是相近的景致,却因人生境遇的变迁而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读,这正是苏轼心境变化的鲜活写照。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
把一片“叶子”描绘清楚
读书周刊:写这本书的时候,您带着一种好奇,想知道苏轼看画的眼睛是怎样练成的。您的好奇,最终找到答案了吗?
金哲为:我觉得是找到了某种心境。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最初动笔写苏轼时,心里满是茫然。他太复杂了,在太多领域有极高成就,留下的东西又浩如烟海,我要怎么去理解他?触及他的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用了张僧繇为宝志禅师画像的典故。张僧繇是大画家,画禅师一面尚且不易,后来听说禅师有十二面,更不知该如何下笔。
我最初也带着这样的困惑:从绘画这个角度切入苏轼,会不会太小?但想写尽苏轼的全貌是不可能的,而我的目标是把关于苏轼的一片“叶子”描绘清楚。而在描绘这片“叶子”的过程中,自然要回溯它生长的土地、当时的空气,以及整个生长环境。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去了解苏轼在其他方面的经历与思想。关键的是,最后得落到“这一叶”上。把其他方面的信息了解和浓缩后,我的书写还是以绘画为起点,但并不仅仅是绘画而已。我希望通过绘画这个切口,看到苏轼不同人生面向里流淌着的同一种精神内核。这其实也暗合了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读书周刊:通过“这一叶”,您看到了什么?
金哲为:能看到很多面向。比如,看他谈“水”,不能只看他的画论,还得结合他对《易经》《尚书》的解读;看他写“马”,也不只是看他如何描述马匹,那些画里的马多是西域贡马,就得结合他当时在朝中的处境来看,甚至要看到他对西夏政策的态度。苏轼文章里常有不少“出位之言”。有些事本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但他觉得非说不可,他对西夏、吐蕃后裔的看法,也常借由这类艺术论述传递出来。所以这本书虽从绘画切入,却能通过这个触底,看到苏轼多面的形象。
读书周刊:有人看了书说:“这角度看苏东坡,完全陌生了啊!”
金哲为:我理解的“陌生感”,就是写书要聚焦大家平时不太能看到的内容。毕竟,现在市面上关于苏东坡的传记特别多。如果找不出新的亮点,单纯复述他的生平故事,根本没必要再写。所以,我就是想挖掘那些不太被触及但又重要的部分来写。而我一直研究中国绘画艺术史,从这个角度切入就很自然。
读书周刊:经由这种陌生,您希望读者最终通往的是熟悉的还是全新的苏轼?
金哲为:苏轼本就没有固定形象,有很多面。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汉学家艾朗诺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这本书199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它的核心就是讲东坡的多面性。就连苏轼自己也说“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昨天的他和今天的他就不同。不同人生阶段的苏轼,所展现出的面目不一样;大家心中的苏轼,自然也各不相同。我不敢说能让读者看到一个“全新的苏轼”,但我希望把我眼中的、从绘画角度解读的这个苏轼呈现给读者。
探寻艺术的时代精神
读书周刊:此书写苏轼与艺术有关的经历,时间是迂回跳跃的,视角是今昔对比的,这种时间线的交织令写作颇具挑战性。
金哲为:确实如此。如果按时间顺序来梳理苏轼的看画、论画、画画,会发现内容多集中在他人生的几个特定阶段,但这不意味着其他时期他就不关注绘画。很多时候,他的文字是回忆式的,比如某天想起从前见过的一幅画,生出新的感慨;翻出家传旧藏,突然想为这幅画写点什么。这些零散的记录,如果按时间线来串联,很容易变成一份枯燥的清单。
所以,我没有选择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而是试图在书中构建“时间感”。比如,“东坡之眼”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苏轼品鉴画作的眼光,二是眼睛是灵性与精气之所聚,眼睛一睁一闭,恰是人的一生。作为大收藏家,苏轼经常将自己的珍藏铺展晾晒,书的尾声,我写了他最后一次铺展书画的场景,紧接着便是他在常州离世,仿佛他闭眼的瞬间,一生的过往都在眼前回放。
全书共九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前四章,主要是厘清苏轼从少年到中年看过什么画。第二部分是第五和第六章,写中年时期的他把从前看过的画、积累的眼界,慢慢沉淀融合。特别提到吴道子、王维、文同这三个人对他艺术观的影响。比如,他评价吴道子时提出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是他自己的艺术追求:既要有传统的根基,又要有豪放的气象,但不能过度突破传统的边界。他的诗词豪放,但细品便知,豪放始终带着克制,一直把握着精妙的尺度。第三部分是最后三章,主要围绕苏轼黄州之后的经历展开,特别是他在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经历了从入朝到被贬广州、海南的仕途起伏,他在这段时间写下的论画文字,恰好藏着他后半生的三对主要矛盾。
读书周刊:书中提炼了贯穿苏轼后半生的三对主要矛盾——江湖与庙堂、进取与退守、想归去与归不去,并分别用中国画中常见的三种意象——贬谪山水、马画、田园山水来对应。
金哲为:将这三种意象对应苏轼晚年的三组人生矛盾,一方面可以呈现那个时代的一些艺术风貌、美学取向,比如,北宋时,士大夫们大都数次身居庙堂,也频频远放江湖。苏轼的朋友如王诜、宋迪都是山水名家,他们将在外所见的风景描绘成图,这些画成为有相似遭遇者共同消解烦忧、寄托幽意的情感媒介,也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山水画传统。同时,将艺术观念与政治、生活、文本互为镜像地联系起来,可以更深入地探寻艺术所根植的时代精神。
他的视角无可替代
读书周刊:书中写到《次韵水官诗并引》中的“丹青偶为戏”可视为苏轼文人画论的开端。从早期认知到成熟理论,其艺术理论的核心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深化?
金哲为:在苏轼之前,中国人评价一幅画好不好,标准往往是“像不像”。那时的画师多以绘画为谋生手段,宫廷画师要按皇帝的命令作画,容不得半点儿戏;民间画师要迎合市场喜好,靠画作换取生计。而苏轼的“丹青偶为戏”,改变了人们对绘画的认知,强调绘画不必以“像”为目标,本质是抒发个人的情感,就像米芾的“胸中盘郁,只是为了抒发”,绘画从此成为文人释放心绪的载体。
这种认知,在苏轼早年刚到京城时就已形成,此后,他对绘画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文同的墨竹给予他很大的触动,他认为人世间的苦难与挫折,就像植物生长中所遇到的环境变化——冷热交替、风雨侵袭,竹子在不同环境里会长出不同的形态。文同所偏爱的那种“逆境之竹”——被砍伐后残留的竹芽,经火烧、被石压,依然顽强生长。哪怕最终只长到一尺高,没能成为参天之竹,却“一尺亦有万尺之意”,这份在困境中坚守的生命力比“长成万尺”更难得。他从竹的坚韧里看到了自己,从水的顺势中照见了心境,这些自然意象都已成为他人生态度的投射。
读书周刊:至今传为苏轼真迹的三件作品都是竹、木、石的组合,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荒寒、简远、具有内在张力的艺术世界。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物象中,正藏着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对生命本真的提炼。
金哲为:苏轼将竹、木、石称作“三友”。他说“竹寒而秀”,天寒时节,多数树木早已凋零,唯有竹子依旧挺立;他说“木瘠而寿”,那些带着病态、枝干瘦弱的树木,虽无人看重、难作材用,却自有一番清瘦的意趣;他说“石丑而文”,长得奇形怪状的丑石,反而比光滑规整的石头更有观赏价值,这份“丑”里藏着天然的纹理与韵味。
它们都带着“不合时宜”的特质,可正是这三个“不合时宜”的物象凑成了苏轼画作的内容。人们常说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而他对竹、木、石的偏爱,正是这种心境的投射。
读书周刊:一幅画的背后,往往是一群人的故事。通过“东坡之眼”,读者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一个怎样精彩的艺术“朋友圈”?
金哲为:大家都知道北宋是中国绘画的高峰,如果选一个人的眼睛带着读者去看这个时代,用谁的眼睛比较好?
开始我考虑过宋徽宗,他是北宋绘画的集大成者,但他处于北宋末期,更多是总结前人成果,和前辈画家并无直接交往,视角偏于整合而非亲历。后又想到郭若虚,他的《图画见闻志》记录了从唐到北宋的绘画传统,可他更像一个纯粹的记录者,缺乏系统的个人评价。还考虑过米芾,他的《画史》就写他在谁家里看到一幅什么样的画,直接给这个画判定真伪。但米芾个性极端,论断往往语出惊人,例如,将一些公认的大师之作贬为只配摆在酒楼,这样的评价主观性太强。
最终选定苏轼,是因为他的视角无可替代。他身处北宋中期,刚好见证了一批重要的画家,如和他差不多同时期入京的郭熙、创作《烟江叠嶂图》的王诜、受他直接影响的李公麟。李公麟有很多作品,都是苏轼出选题,然后他去创作的。苏轼还有一个画家朋友宋迪,宋迪的《潇湘八景图》流传至今,苏轼于元丰元年(1078年)创作的《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诗,是目前可考的最早题咏《潇湘八景图》的作品。苏轼对那个时代的绘画,不只是见证者、欣赏者,也是深度参与者。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许多的诗文与记录,不仅涉及绘画,还是关于同时代人的生平、交往,所以,没有比苏轼再适合的人物了。
我希望通过《东坡之眼》,读者不只是读懂苏轼,更能透过他的视角,看见那个大师辈出的北宋。看到那些传世画作如何在苏轼的见证下完成,也看到画家们各自不同的命运。比如,书中写到的《秋山平远图》,在王安石变法尚未开启时,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为同一幅《秋山平远图》题咏过。这些被忽略的暗线,能让大家看到苏轼同时代的人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与风骨。
读书周刊:《东坡之眼》是你“四年来的第三本书,也是最有底气的一本”。从《画里浮生:中国画的隐秘记忆》《不必向长安:沈周的记忆抽帧术》到此书,沉浸于艺术史研究中,让您的生命获得了怎样与众不同的滋养?
金哲为: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和古人进行一场深度对话。要读懂画里那些婉转的意涵,就得先走进画家的世界,如他一生的经历、他写下的文字,才能在落笔的那一刻,与他达成深度的精神对话。
就像我读沈周,最受触动的是他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沈周的人生没有苏轼那般跌宕丰富,甚至可以说充满重复性。他一生未曾离开苏浙一带,日常无非是侍弄花草、耕种菜畦,与友人游山玩水、提笔绘山水等。生活平淡,但他用幽默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趣味盎然。我从他身上获得的这份感悟,格外治愈。
读苏轼,是跟着他不断经历。我跟着他到黄州、去惠州,想象他在岭南的生活,以及从海南北归时一路的艰辛。与不同人生阶段的苏轼对话,你会明白他为何至今仍被这么多人铭记——人们总能在他的经历里找到某种共鸣。谁的人生不会遇到坎坷?而他教会我们如何自处、如何化解困境、如何与自己和解。
时代在变,古今有巨大不同,但人心中那些本质的情感从未改变。从沈周那里,我获得了治愈;从苏轼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刚直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像水一样柔软而坚韧。
千百年来,苏轼的诗文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文化符号。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东坡之眼:苏轼的艺术精神与绘画世界》(以下简称《东坡之眼》)一书中,作者金哲为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切入这位千古文人——以“画”为线索,串联起苏轼的人生轨迹、精神变迁与时代风骨,编织出宋代书画史的脉络。
作者与苏轼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让我们看到,读懂那些藏在画里的“心事”,是读懂苏轼精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经常要“回到”苏轼那里
读书周刊:您曾说:“怀念一个人,那就时不时写写他。”从陆续写了几篇关于苏轼的文章,到完成《东坡之眼》这本书,您的“怀念”是否从一种情感共鸣升华为一种精神对话?
金哲为:苏轼总在不经意间与我产生联结,比如,中秋时节、七月寄望等,有很多让我对苏轼产生联想的时刻。这种联想算不上深刻的精神对话,但用一本书从绘画这个独特的视角来切入他的精神世界,让我能更深入地贴近他。之前写的有关苏轼的文章主题都不同,比较零散,而《东坡之眼》用书的形式来呈现,让我的探索更系统、更深入。
苏轼太过丰富,在很多方面都成就斐然,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也有鲜明的变化,值得后人不断去挖掘。未来,我仍会持续关注与他相关的内容。
读书周刊:“如果一个人确实看到了某些未曾有人涉足的角落,那自然有为拼图全局补上一角的必要”,从苏轼的阅画经历这一角来观察“太过丰富”的苏轼,您如何发现并确信这一角的独特价值?
金哲为:研究中国艺术史就会发现,苏轼是绕不开的。他最早提出了文人画概念。不管是看元代的还是明清的艺术史,会发现后人经常提到他的画论。我之前写沈周时也发现,沈周会经常讲到苏轼,所以经常要“回到”苏轼那里。这让我好奇:苏轼是怎么成为文人画概念的提倡者的?他是如何练就看画的眼睛的?他看过哪些画、有过哪些收藏,又是谁带他走进绘画的世界?这些都是我想要探索的。
从绘画角度切入苏轼,是个很好的选择。看画经历贯穿其一生: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与弟弟苏辙游成都大慈寺看画,题写“精妙冠世”评价唐代的壁画作品,这是现存最早的东坡石刻;他去世前20多天,仍有观赏龙画的记载。相比之下,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诗词创作,时间跨度不及他的观画经历。更重要的是,不同时期他看的画、关于画的文字,都对应着他当时的人生处境和思想状态。尤其是乌台诗案后,他不太敢直言时政了,而艺术则成了安全的表达出口。
读书周刊:在我们熟知的诗文之外,艺术是苏轼情感与思想的另一重镜像。
金哲为:他后期的题画诗与画论看似聚焦艺理,实则暗藏对时政、世风与学风的隐晦评判。这些委婉的表达,有时在他的常规诗文里难觅踪迹,却能在他的艺术论述中得以窥见。
心境变化的鲜活写照
读书周刊:您在整理苏轼散落的画论时,不仅要从题画诗、书信等文字里搜集,还要结合具体语境去理解,这个过程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金哲为:苏轼没有专门写过系统的画论。他关于绘画的观点,散落在题画诗、写给友人的书信或悼念文里。比如,“胸有成竹”这个说法,出自他悼念表兄兼好友文同(字与可)的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强调画家创作前需对竹子有深刻观察和完整构思。他从没有刻意为绘画立说,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的零星论述搜集起来,这是难度很高的工作。接着,对他的很多观点,还需要回归当时的具体语境去理解与转化,其中的难度也不小。
读书周刊: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一些时刻让您感到自己与这位千古文人产生了超越时空的神交?
金哲为:这样的时刻蛮多的。比如,南宋马远的《水图》,明代鉴赏家认为马远继承了苏轼主张的画水应“尽水之变”,描绘的是苏轼所说的“活水”。但细读苏轼《画水记》会发现,他推崇的是“奔流湍急、随山石曲折而变”的水,与马远《水图》里的水有明显差异。马远画水大多没有山石,主要表现水本身的多样变化。
这背后是不同时期画水风格的转变:从北宋中晚期到南宋中期,文人对“水”的理解在改变。苏轼强调水借山石显其变,而南宋时人们更倾向于展现水的“本性之变”,无须依托他物。这里还可引申出更深层的解读:苏轼谈水,从来不只是艺术层面的探讨。他在《东坡易传》等哲学著作中也常以水为喻,而他的一生恰如他推崇的水——屡遭波折、被迫应变,却始终守住本心、奔涌向前,水的形态里藏着他的人生写照与情感倾向。
读书周刊:水已不仅仅是现实世界或艺术范畴的水,还承载着苏轼的人生。
金哲为:比如,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初见时会困惑木头为何画得奇奇怪怪,连他的好友米芾都评价其“无端奇崛”,认为只是苏轼“胸中意气”的随性抒发。其实画中苏轼暗藏着巧思,如他在题跋中的那句“散木支离得自全”。“散木”一词源自《庄子》,苏轼熟读《庄子》,曾说庄子道尽了他未说之言。庄子笔下的“散木”是“不材之木”,因枝干无用而免遭砍伐,得以保全自身。这幅画里的枯木,正是苏轼对庄子思想的艺术化表达。
再比如,苏轼一生大概见过三幅《秋山平远图》,其中两幅有他的题诗。画作题目相同、内容相近,但苏轼在两首题诗里的心境很不一样,反映了他人生不同时期的处境与想法。早年题诗时,他看到的画是非常温馨的田园生活景象,藏着他归隐田园、回归理想居所的向往;当这心愿终成奢望,再看相似的画,他的描述已变成“乱山无境”,是理想落空的怅然。明明是相近的景致,却因人生境遇的变迁而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读,这正是苏轼心境变化的鲜活写照。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
把一片“叶子”描绘清楚
读书周刊:写这本书的时候,您带着一种好奇,想知道苏轼看画的眼睛是怎样练成的。您的好奇,最终找到答案了吗?
金哲为:我觉得是找到了某种心境。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最初动笔写苏轼时,心里满是茫然。他太复杂了,在太多领域有极高成就,留下的东西又浩如烟海,我要怎么去理解他?触及他的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用了张僧繇为宝志禅师画像的典故。张僧繇是大画家,画禅师一面尚且不易,后来听说禅师有十二面,更不知该如何下笔。
我最初也带着这样的困惑:从绘画这个角度切入苏轼,会不会太小?但想写尽苏轼的全貌是不可能的,而我的目标是把关于苏轼的一片“叶子”描绘清楚。而在描绘这片“叶子”的过程中,自然要回溯它生长的土地、当时的空气,以及整个生长环境。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去了解苏轼在其他方面的经历与思想。关键的是,最后得落到“这一叶”上。把其他方面的信息了解和浓缩后,我的书写还是以绘画为起点,但并不仅仅是绘画而已。我希望通过绘画这个切口,看到苏轼不同人生面向里流淌着的同一种精神内核。这其实也暗合了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读书周刊:通过“这一叶”,您看到了什么?
金哲为:能看到很多面向。比如,看他谈“水”,不能只看他的画论,还得结合他对《易经》《尚书》的解读;看他写“马”,也不只是看他如何描述马匹,那些画里的马多是西域贡马,就得结合他当时在朝中的处境来看,甚至要看到他对西夏政策的态度。苏轼文章里常有不少“出位之言”。有些事本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但他觉得非说不可,他对西夏、吐蕃后裔的看法,也常借由这类艺术论述传递出来。所以这本书虽从绘画切入,却能通过这个触底,看到苏轼多面的形象。
读书周刊:有人看了书说:“这角度看苏东坡,完全陌生了啊!”
金哲为:我理解的“陌生感”,就是写书要聚焦大家平时不太能看到的内容。毕竟,现在市面上关于苏东坡的传记特别多。如果找不出新的亮点,单纯复述他的生平故事,根本没必要再写。所以,我就是想挖掘那些不太被触及但又重要的部分来写。而我一直研究中国绘画艺术史,从这个角度切入就很自然。
读书周刊:经由这种陌生,您希望读者最终通往的是熟悉的还是全新的苏轼?
金哲为:苏轼本就没有固定形象,有很多面。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汉学家艾朗诺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这本书199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它的核心就是讲东坡的多面性。就连苏轼自己也说“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昨天的他和今天的他就不同。不同人生阶段的苏轼,所展现出的面目不一样;大家心中的苏轼,自然也各不相同。我不敢说能让读者看到一个“全新的苏轼”,但我希望把我眼中的、从绘画角度解读的这个苏轼呈现给读者。
探寻艺术的时代精神
读书周刊:此书写苏轼与艺术有关的经历,时间是迂回跳跃的,视角是今昔对比的,这种时间线的交织令写作颇具挑战性。
金哲为:确实如此。如果按时间顺序来梳理苏轼的看画、论画、画画,会发现内容多集中在他人生的几个特定阶段,但这不意味着其他时期他就不关注绘画。很多时候,他的文字是回忆式的,比如某天想起从前见过的一幅画,生出新的感慨;翻出家传旧藏,突然想为这幅画写点什么。这些零散的记录,如果按时间线来串联,很容易变成一份枯燥的清单。
所以,我没有选择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而是试图在书中构建“时间感”。比如,“东坡之眼”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苏轼品鉴画作的眼光,二是眼睛是灵性与精气之所聚,眼睛一睁一闭,恰是人的一生。作为大收藏家,苏轼经常将自己的珍藏铺展晾晒,书的尾声,我写了他最后一次铺展书画的场景,紧接着便是他在常州离世,仿佛他闭眼的瞬间,一生的过往都在眼前回放。
全书共九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前四章,主要是厘清苏轼从少年到中年看过什么画。第二部分是第五和第六章,写中年时期的他把从前看过的画、积累的眼界,慢慢沉淀融合。特别提到吴道子、王维、文同这三个人对他艺术观的影响。比如,他评价吴道子时提出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是他自己的艺术追求:既要有传统的根基,又要有豪放的气象,但不能过度突破传统的边界。他的诗词豪放,但细品便知,豪放始终带着克制,一直把握着精妙的尺度。第三部分是最后三章,主要围绕苏轼黄州之后的经历展开,特别是他在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经历了从入朝到被贬广州、海南的仕途起伏,他在这段时间写下的论画文字,恰好藏着他后半生的三对主要矛盾。
读书周刊:书中提炼了贯穿苏轼后半生的三对主要矛盾——江湖与庙堂、进取与退守、想归去与归不去,并分别用中国画中常见的三种意象——贬谪山水、马画、田园山水来对应。
金哲为:将这三种意象对应苏轼晚年的三组人生矛盾,一方面可以呈现那个时代的一些艺术风貌、美学取向,比如,北宋时,士大夫们大都数次身居庙堂,也频频远放江湖。苏轼的朋友如王诜、宋迪都是山水名家,他们将在外所见的风景描绘成图,这些画成为有相似遭遇者共同消解烦忧、寄托幽意的情感媒介,也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山水画传统。同时,将艺术观念与政治、生活、文本互为镜像地联系起来,可以更深入地探寻艺术所根植的时代精神。
他的视角无可替代
读书周刊:书中写到《次韵水官诗并引》中的“丹青偶为戏”可视为苏轼文人画论的开端。从早期认知到成熟理论,其艺术理论的核心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深化?
金哲为:在苏轼之前,中国人评价一幅画好不好,标准往往是“像不像”。那时的画师多以绘画为谋生手段,宫廷画师要按皇帝的命令作画,容不得半点儿戏;民间画师要迎合市场喜好,靠画作换取生计。而苏轼的“丹青偶为戏”,改变了人们对绘画的认知,强调绘画不必以“像”为目标,本质是抒发个人的情感,就像米芾的“胸中盘郁,只是为了抒发”,绘画从此成为文人释放心绪的载体。
这种认知,在苏轼早年刚到京城时就已形成,此后,他对绘画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文同的墨竹给予他很大的触动,他认为人世间的苦难与挫折,就像植物生长中所遇到的环境变化——冷热交替、风雨侵袭,竹子在不同环境里会长出不同的形态。文同所偏爱的那种“逆境之竹”——被砍伐后残留的竹芽,经火烧、被石压,依然顽强生长。哪怕最终只长到一尺高,没能成为参天之竹,却“一尺亦有万尺之意”,这份在困境中坚守的生命力比“长成万尺”更难得。他从竹的坚韧里看到了自己,从水的顺势中照见了心境,这些自然意象都已成为他人生态度的投射。
读书周刊:至今传为苏轼真迹的三件作品都是竹、木、石的组合,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荒寒、简远、具有内在张力的艺术世界。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物象中,正藏着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对生命本真的提炼。
金哲为:苏轼将竹、木、石称作“三友”。他说“竹寒而秀”,天寒时节,多数树木早已凋零,唯有竹子依旧挺立;他说“木瘠而寿”,那些带着病态、枝干瘦弱的树木,虽无人看重、难作材用,却自有一番清瘦的意趣;他说“石丑而文”,长得奇形怪状的丑石,反而比光滑规整的石头更有观赏价值,这份“丑”里藏着天然的纹理与韵味。
它们都带着“不合时宜”的特质,可正是这三个“不合时宜”的物象凑成了苏轼画作的内容。人们常说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而他对竹、木、石的偏爱,正是这种心境的投射。
读书周刊:一幅画的背后,往往是一群人的故事。通过“东坡之眼”,读者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一个怎样精彩的艺术“朋友圈”?
金哲为:大家都知道北宋是中国绘画的高峰,如果选一个人的眼睛带着读者去看这个时代,用谁的眼睛比较好?
开始我考虑过宋徽宗,他是北宋绘画的集大成者,但他处于北宋末期,更多是总结前人成果,和前辈画家并无直接交往,视角偏于整合而非亲历。后又想到郭若虚,他的《图画见闻志》记录了从唐到北宋的绘画传统,可他更像一个纯粹的记录者,缺乏系统的个人评价。还考虑过米芾,他的《画史》就写他在谁家里看到一幅什么样的画,直接给这个画判定真伪。但米芾个性极端,论断往往语出惊人,例如,将一些公认的大师之作贬为只配摆在酒楼,这样的评价主观性太强。
最终选定苏轼,是因为他的视角无可替代。他身处北宋中期,刚好见证了一批重要的画家,如和他差不多同时期入京的郭熙、创作《烟江叠嶂图》的王诜、受他直接影响的李公麟。李公麟有很多作品,都是苏轼出选题,然后他去创作的。苏轼还有一个画家朋友宋迪,宋迪的《潇湘八景图》流传至今,苏轼于元丰元年(1078年)创作的《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诗,是目前可考的最早题咏《潇湘八景图》的作品。苏轼对那个时代的绘画,不只是见证者、欣赏者,也是深度参与者。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许多的诗文与记录,不仅涉及绘画,还是关于同时代人的生平、交往,所以,没有比苏轼再适合的人物了。
我希望通过《东坡之眼》,读者不只是读懂苏轼,更能透过他的视角,看见那个大师辈出的北宋。看到那些传世画作如何在苏轼的见证下完成,也看到画家们各自不同的命运。比如,书中写到的《秋山平远图》,在王安石变法尚未开启时,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为同一幅《秋山平远图》题咏过。这些被忽略的暗线,能让大家看到苏轼同时代的人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与风骨。
读书周刊:《东坡之眼》是你“四年来的第三本书,也是最有底气的一本”。从《画里浮生:中国画的隐秘记忆》《不必向长安:沈周的记忆抽帧术》到此书,沉浸于艺术史研究中,让您的生命获得了怎样与众不同的滋养?
金哲为: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和古人进行一场深度对话。要读懂画里那些婉转的意涵,就得先走进画家的世界,如他一生的经历、他写下的文字,才能在落笔的那一刻,与他达成深度的精神对话。
就像我读沈周,最受触动的是他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沈周的人生没有苏轼那般跌宕丰富,甚至可以说充满重复性。他一生未曾离开苏浙一带,日常无非是侍弄花草、耕种菜畦,与友人游山玩水、提笔绘山水等。生活平淡,但他用幽默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趣味盎然。我从他身上获得的这份感悟,格外治愈。
读苏轼,是跟着他不断经历。我跟着他到黄州、去惠州,想象他在岭南的生活,以及从海南北归时一路的艰辛。与不同人生阶段的苏轼对话,你会明白他为何至今仍被这么多人铭记——人们总能在他的经历里找到某种共鸣。谁的人生不会遇到坎坷?而他教会我们如何自处、如何化解困境、如何与自己和解。
时代在变,古今有巨大不同,但人心中那些本质的情感从未改变。从沈周那里,我获得了治愈;从苏轼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刚直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像水一样柔软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