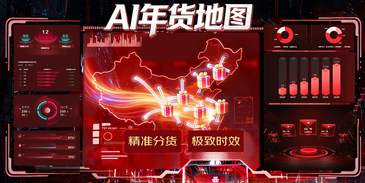展开明代画家仇英的《独乐园图》长卷,那青绿设色的明丽景色,工笔细描的静雅之气,将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从文字化为诗意图景。这幅画不仅是园林影像的再现,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司马光自称“迂叟”,他在《独乐园记》中写道:“各尽其分而安之”,以独乐对抗世俗喧嚣;仇英则以画笔勾勒出独乐园七景,将司马光的隐逸哲思与政治失意的矛盾,凝练于亭台、竹石、流水之间。仇英以苏州园林式的秀美重构洛阳独乐园,虽非历史原貌,却更贴近文人心中“理想国”的样貌——一方园林,既是避世桃源,亦是精神丰碑。画中的草木动物,都在诉说着中国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永恒命题。
名园入画
早在宋代,就有画家画过独乐园图了。“明四家”中,沈周、文征明、仇英都画过有关“独乐”题材的画卷。沈周为祝贺老友徐有贞60寿诞,画了《芳园独乐图》,画的是徐有贞退休之后优游林下的情景。沈周取这个画题,也是拿徐有贞和大宋名臣司马光相比拟,算是一种不着痕迹的恭维。而文征明和仇英的《独乐园图》,则都和宋代那位佚名画家一样,画的是司马光在独乐园中逍遥自得的情景。还有人摹画了明代佚名画家的《司马光归隐图》,题名为《太白独乐图》,署名唐寅,流传到现在,倒也成了古董。这样一来,“明四家”都和“独乐”画沾上了关系。说起独乐,人们除了想到孟子的“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之外,还能想到司马光的独乐园,为什么他这个园子这么深入人心呢?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52岁的司马光踏上了洛阳的土地。彼时,王安石变法正如火如荼,而司马光坚决反对“青苗法”等一系列新政,朝堂上的争执已令他身心俱疲,他于是自请外放,以“西京留守司御史台”闲职退居洛阳。初到洛阳的两年,司马光暂居陋巷,夏日酷暑难耐时,竟效仿寒士掘地为室,被时人戏称“司马入地”。熙宁六年(1073年),他在洛阳尊贤坊北关购得二十亩荒地。这片土地背倚伊水,远眺万安山,虽无王公园林的雕梁画栋,却因主人的匠心独运,化作一方承载士大夫精神的文化净土——独乐园。独乐园中的读书堂内,五千卷藏书堆积如山。在这里,司马光带领范祖禹等助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毅力编纂《资治通鉴》。稍有闲暇,会参加居洛文化名流的“洛阳耆英会”,或者在园中独自徜徉。
仇英的《独乐园图》,需要从右至左,缓缓展开欣赏,一幕幕场景会让人心动神驰。“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七个场景衔接有序,司马光现身于每个场景中,或读书、或闲坐、或远眺。其中乐趣,正如他在《独乐园记》中所说:“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竹与灵芝
李清照的老爸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评价独乐园说:“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但“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仇英把独乐园画得这样精致典雅,也几乎让人忘了这所园子是一个宛似刘禹锡“陋室”的所在。它因陋就简,往好了说是充满天趣,真实一点描绘,就是颇有些寒酸了。
钓鱼庵建在水池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就是种了一圈竹子,把竹子顶端捆扎在一起,形成一个庵房的样子,形状有点像渔民们在水边搭建的简陋房子,司马光就坐在庵中垂钓。司马光在《独乐园七咏》中写道:“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园中出现最多的植物,就是竹子。种竹斋前,司马光还在指挥着童仆,移来竹子,让竹林更加繁盛呢。竹的高洁、坚韧、有节,就是他人格的投射。
采药圃中,又是用竹子扎了一个庵子,通往庵子的道路两侧,也种上翠竹,形成一个绿色走廊。药圃的畦垄像棋盘一样整齐,里面种着各种草药,如人参、灵芝、地黄、石蒜、石竹、三七、肾蕨等,一个畦子里却只有一棵。浇花亭两侧的花栏中,芍药、牡丹、杂花每样也只栽两棵。司马光自己说:“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
灵芝自古被视为仙草,象征长生与祥瑞。仇英在药圃中画上灵芝,是有依据的。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说,僧人参寥子曾到独乐园游赏,看到一处干燥的高坡上,并不依托枯木,而是平地长出二十多棵灵芝。参寥子问园丁,怎样浇灌才让灵芝得以生长繁茂呢?园丁说:“天生灵物,不假人力”。参寥子感慨道:“真不愧是司马温公的仆人!”
灵芝就是“惟吾德馨”的物象实证。上面说的园丁,很可能就是司马家以戆直朴厚闻名的忠仆吕直。一次,司马光让吕直去市上卖掉一匹马,特意叮嘱说:“这匹马今年夏天得过肺病,你一定要告诉买主。”平日里,有人要参观独乐园,常会给守园的吕直一点小费。吕直就攒下来,在园中盖了一个公厕和一座井亭。司马光问他:“你咋不留着自己花呢?”吕直说:“难道只有相公做得了好人,吕直就不能做好人吗?”
仇英笔下的竹庵以天然的竹丛围合而成,也是司马光顺应自然之道的心理投射。他曾说,在独乐园,“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他的施政理念以保守主义为核心,强调遵循祖宗之法与儒家伦理,反对激进变革,主张通过德治和礼制维护社会稳定。他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认为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扰民害国,破坏传统经济秩序,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这也是他远离朝堂,避居洛阳著书“独乐”的原因。他的“穴居”与纯天然竹庵,都在无言诉说着自己的理念。
还是这个吕直,一直称呼主人“君实秀才”。苏东坡听了觉得不妥,就教吕直改口称呼主人为“相公”。司马光听他突然这么叫,觉得很别扭,得知真相后叹道:“好好一个人,被苏子瞻教坏了!”
虎与鹿鹤
仇英给“采药圃”里的司马光身下画了一张虎皮褥子,这是耐人寻味的细节。《易·革卦》中的九五爻辞为“大人虎变”,其辞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在古人心中,“大人”是凤毛麟角的圣贤。大人物像猛虎变换皮毛一般进行变革,威猛迅疾不可测度,不用占卜也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彼时新法推行,司马光退居洛阳,表面“独乐”,实则“四海望陶冶”(苏轼诗)。司马光在《独乐园七咏》中自比严子陵、陶渊明,却在《见山台》诗里泄露心曲:“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司马光坐在虎皮上,既示退隐之志,又含未泯的济世雄心。仇英借此暗示:独乐非消极避世,而是以退为进的姿态。看似超然的归隐,实为“待时而动”的政治蛰伏。
浇花亭和采药圃畔,都有一只白鹤昂首而立,陪伴在司马光身旁,像是他的知音。鹤的孤独姿态,也映射了司马光的政治境遇。古人认为,鹤是仙禽,也象征着君子、贤士。明代周履靖在《相鹤经》中写道:“夫顶丹胫碧,毛羽莹洁,颈纤而修,身耸而正,足臞而节高,颇类不食烟火人,可谓之鹤。”仇英让仙鹤伴立,象征司马光品行高洁。
通往见山台的池水畔,有两只鹿在徜徉饮水。鹿、鹤往往并称,鹿也是仙兽,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中,葛洪就牵着一头鹿。汉扬雄《解嘲》道:“往昔周纲解结,群鹿争逸。”李善注引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鹿”与“禄”谐音,古人又常以“鹿”象征“禄”表示文运与仕途。另一方面,鹿又象征隐逸的生活,它恬淡清幽的生活环境和隐士的理想家园相似。所以唐李颀《行路难》中说:“薄俗嗟嗟难重陈,深山麋鹿可为邻。”苏东坡《赤壁赋》中有句:“侣鱼虾而友麋鹿”。鹿身上的两重寓意,也可以是司马光的身份隐喻。一方面,他在独乐园中“逍遥相羊,惟意所适”。另一方面,他终究是普天下人寄寓厚望的政治领袖,苏轼有诗云:“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他终会从这里走出去,再次担当起家国重任的。
独乐园的“独乐”,终究无法脱离“众乐”的期待。元丰七年(1084年),66岁的司马光在独乐园完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进献给皇帝。次年,神宗驾崩,高太后急召司马光回朝为宰相,独乐园的竹影在车马喧嚣中渐渐模糊。
真正的“独乐”,从不是遗世独立的孤芳自赏,而是以孤往精神守护道统的文明火种。《独乐园图》中的乐,是司马光的“各安其分”,是仇英的“以画传心”。独乐非孤绝,而是于纷扰中筑起一座心灵花园;众乐非喧闹,而是以德性滋养天下。独乐之趣,不在逃离尘世,而在心有所安;众乐之望,不在强求共鸣,而在德馨自远。看着仇英的画卷,仍能感受司马光临流执卷,清风入怀之乐。仇英以笔墨凝固的,不仅是园林胜景,更是一个时代文人对理想生活、志趣追求的优雅想象。
展开明代画家仇英的《独乐园图》长卷,那青绿设色的明丽景色,工笔细描的静雅之气,将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从文字化为诗意图景。这幅画不仅是园林影像的再现,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司马光自称“迂叟”,他在《独乐园记》中写道:“各尽其分而安之”,以独乐对抗世俗喧嚣;仇英则以画笔勾勒出独乐园七景,将司马光的隐逸哲思与政治失意的矛盾,凝练于亭台、竹石、流水之间。仇英以苏州园林式的秀美重构洛阳独乐园,虽非历史原貌,却更贴近文人心中“理想国”的样貌——一方园林,既是避世桃源,亦是精神丰碑。画中的草木动物,都在诉说着中国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永恒命题。
名园入画
早在宋代,就有画家画过独乐园图了。“明四家”中,沈周、文征明、仇英都画过有关“独乐”题材的画卷。沈周为祝贺老友徐有贞60寿诞,画了《芳园独乐图》,画的是徐有贞退休之后优游林下的情景。沈周取这个画题,也是拿徐有贞和大宋名臣司马光相比拟,算是一种不着痕迹的恭维。而文征明和仇英的《独乐园图》,则都和宋代那位佚名画家一样,画的是司马光在独乐园中逍遥自得的情景。还有人摹画了明代佚名画家的《司马光归隐图》,题名为《太白独乐图》,署名唐寅,流传到现在,倒也成了古董。这样一来,“明四家”都和“独乐”画沾上了关系。说起独乐,人们除了想到孟子的“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之外,还能想到司马光的独乐园,为什么他这个园子这么深入人心呢?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52岁的司马光踏上了洛阳的土地。彼时,王安石变法正如火如荼,而司马光坚决反对“青苗法”等一系列新政,朝堂上的争执已令他身心俱疲,他于是自请外放,以“西京留守司御史台”闲职退居洛阳。初到洛阳的两年,司马光暂居陋巷,夏日酷暑难耐时,竟效仿寒士掘地为室,被时人戏称“司马入地”。熙宁六年(1073年),他在洛阳尊贤坊北关购得二十亩荒地。这片土地背倚伊水,远眺万安山,虽无王公园林的雕梁画栋,却因主人的匠心独运,化作一方承载士大夫精神的文化净土——独乐园。独乐园中的读书堂内,五千卷藏书堆积如山。在这里,司马光带领范祖禹等助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毅力编纂《资治通鉴》。稍有闲暇,会参加居洛文化名流的“洛阳耆英会”,或者在园中独自徜徉。
仇英的《独乐园图》,需要从右至左,缓缓展开欣赏,一幕幕场景会让人心动神驰。“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七个场景衔接有序,司马光现身于每个场景中,或读书、或闲坐、或远眺。其中乐趣,正如他在《独乐园记》中所说:“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竹与灵芝
李清照的老爸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评价独乐园说:“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但“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仇英把独乐园画得这样精致典雅,也几乎让人忘了这所园子是一个宛似刘禹锡“陋室”的所在。它因陋就简,往好了说是充满天趣,真实一点描绘,就是颇有些寒酸了。
钓鱼庵建在水池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就是种了一圈竹子,把竹子顶端捆扎在一起,形成一个庵房的样子,形状有点像渔民们在水边搭建的简陋房子,司马光就坐在庵中垂钓。司马光在《独乐园七咏》中写道:“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园中出现最多的植物,就是竹子。种竹斋前,司马光还在指挥着童仆,移来竹子,让竹林更加繁盛呢。竹的高洁、坚韧、有节,就是他人格的投射。
采药圃中,又是用竹子扎了一个庵子,通往庵子的道路两侧,也种上翠竹,形成一个绿色走廊。药圃的畦垄像棋盘一样整齐,里面种着各种草药,如人参、灵芝、地黄、石蒜、石竹、三七、肾蕨等,一个畦子里却只有一棵。浇花亭两侧的花栏中,芍药、牡丹、杂花每样也只栽两棵。司马光自己说:“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
灵芝自古被视为仙草,象征长生与祥瑞。仇英在药圃中画上灵芝,是有依据的。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说,僧人参寥子曾到独乐园游赏,看到一处干燥的高坡上,并不依托枯木,而是平地长出二十多棵灵芝。参寥子问园丁,怎样浇灌才让灵芝得以生长繁茂呢?园丁说:“天生灵物,不假人力”。参寥子感慨道:“真不愧是司马温公的仆人!”
灵芝就是“惟吾德馨”的物象实证。上面说的园丁,很可能就是司马家以戆直朴厚闻名的忠仆吕直。一次,司马光让吕直去市上卖掉一匹马,特意叮嘱说:“这匹马今年夏天得过肺病,你一定要告诉买主。”平日里,有人要参观独乐园,常会给守园的吕直一点小费。吕直就攒下来,在园中盖了一个公厕和一座井亭。司马光问他:“你咋不留着自己花呢?”吕直说:“难道只有相公做得了好人,吕直就不能做好人吗?”
仇英笔下的竹庵以天然的竹丛围合而成,也是司马光顺应自然之道的心理投射。他曾说,在独乐园,“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他的施政理念以保守主义为核心,强调遵循祖宗之法与儒家伦理,反对激进变革,主张通过德治和礼制维护社会稳定。他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认为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扰民害国,破坏传统经济秩序,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这也是他远离朝堂,避居洛阳著书“独乐”的原因。他的“穴居”与纯天然竹庵,都在无言诉说着自己的理念。
还是这个吕直,一直称呼主人“君实秀才”。苏东坡听了觉得不妥,就教吕直改口称呼主人为“相公”。司马光听他突然这么叫,觉得很别扭,得知真相后叹道:“好好一个人,被苏子瞻教坏了!”
虎与鹿鹤
仇英给“采药圃”里的司马光身下画了一张虎皮褥子,这是耐人寻味的细节。《易·革卦》中的九五爻辞为“大人虎变”,其辞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在古人心中,“大人”是凤毛麟角的圣贤。大人物像猛虎变换皮毛一般进行变革,威猛迅疾不可测度,不用占卜也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彼时新法推行,司马光退居洛阳,表面“独乐”,实则“四海望陶冶”(苏轼诗)。司马光在《独乐园七咏》中自比严子陵、陶渊明,却在《见山台》诗里泄露心曲:“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司马光坐在虎皮上,既示退隐之志,又含未泯的济世雄心。仇英借此暗示:独乐非消极避世,而是以退为进的姿态。看似超然的归隐,实为“待时而动”的政治蛰伏。
浇花亭和采药圃畔,都有一只白鹤昂首而立,陪伴在司马光身旁,像是他的知音。鹤的孤独姿态,也映射了司马光的政治境遇。古人认为,鹤是仙禽,也象征着君子、贤士。明代周履靖在《相鹤经》中写道:“夫顶丹胫碧,毛羽莹洁,颈纤而修,身耸而正,足臞而节高,颇类不食烟火人,可谓之鹤。”仇英让仙鹤伴立,象征司马光品行高洁。
通往见山台的池水畔,有两只鹿在徜徉饮水。鹿、鹤往往并称,鹿也是仙兽,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中,葛洪就牵着一头鹿。汉扬雄《解嘲》道:“往昔周纲解结,群鹿争逸。”李善注引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鹿”与“禄”谐音,古人又常以“鹿”象征“禄”表示文运与仕途。另一方面,鹿又象征隐逸的生活,它恬淡清幽的生活环境和隐士的理想家园相似。所以唐李颀《行路难》中说:“薄俗嗟嗟难重陈,深山麋鹿可为邻。”苏东坡《赤壁赋》中有句:“侣鱼虾而友麋鹿”。鹿身上的两重寓意,也可以是司马光的身份隐喻。一方面,他在独乐园中“逍遥相羊,惟意所适”。另一方面,他终究是普天下人寄寓厚望的政治领袖,苏轼有诗云:“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他终会从这里走出去,再次担当起家国重任的。
独乐园的“独乐”,终究无法脱离“众乐”的期待。元丰七年(1084年),66岁的司马光在独乐园完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进献给皇帝。次年,神宗驾崩,高太后急召司马光回朝为宰相,独乐园的竹影在车马喧嚣中渐渐模糊。
真正的“独乐”,从不是遗世独立的孤芳自赏,而是以孤往精神守护道统的文明火种。《独乐园图》中的乐,是司马光的“各安其分”,是仇英的“以画传心”。独乐非孤绝,而是于纷扰中筑起一座心灵花园;众乐非喧闹,而是以德性滋养天下。独乐之趣,不在逃离尘世,而在心有所安;众乐之望,不在强求共鸣,而在德馨自远。看着仇英的画卷,仍能感受司马光临流执卷,清风入怀之乐。仇英以笔墨凝固的,不仅是园林胜景,更是一个时代文人对理想生活、志趣追求的优雅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