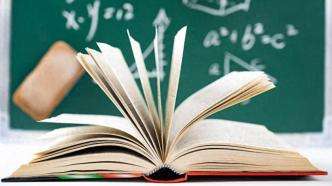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瑞典夏之夜》以《牺牲》的理念为核心
“白夜的季节来临了。”
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剧本的第一句话。这部电影也是瑞典电影的骄傲——它是瑞典电影人邀请塔可夫斯基全程在瑞典拍摄的,主要取景于斯德哥尔摩,以及波罗的海的著名旅游景点哥特兰岛。“白夜”,正是其最迷人的一道“景观”。
最近,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瑞典皇家剧院来到首都剧场,带来了一出《瑞典夏之夜》,讲述了发生在三十多年前拍摄现场的某个“白夜”的、“如梦”般的故事。
在观众还没进场的时候。演员实际上已经在剧场外出现了。和我一起进剧场的是一个典型的光头北欧美男子,他拿着一杯咖啡,缓缓走向观众席,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使馆工作人员吧?
美男子再出现的时候,已经在舞台上——在仿佛“白夜”的光线中(整出戏的布光显然经过了精心安排),观众没有觉察到故事已经开始,就仿佛在瑞典夏夜光线的明暗交替中,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内感受到“白夜”的漫长:漫长,来自猝不及防的观众心理时间,它的故事背景与核心毫无疑问就是塔可夫斯基电影《牺牲》的拍摄和理念,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是非常陌生的。戏剧中使用的几段《牺牲》中的影像,准确地体现了塔可夫斯基的创作指向:片头的达·芬奇名作《博士来拜》(塔可夫斯基在意大利参观乌菲齐美术馆的时候深受感动,当时就决定要把这个主题用于下一部影片),在斯德哥尔摩老城区拍摄的奇妙的核灾难场面(奇妙的是外景地与《博士来拜》的某处细节完全重合),以及片尾海边那棵复活的树,等等。
但是对台上的演员而言,他们只不过在演出一个日常的时刻,好比漫长夏夜的一段小憩,做了一个短暂的梦而已。在梦里,他们和日常一样谈论艺术与人生,由于工作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与导演产生了矛盾,只不过梦醒来后,他们似乎对这个俄罗斯人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这个拍摄过程,随时都能让他们见到真实的“梦境”。
两位影史最伟大导演
相邻却未见面
剧本的编剧厄兰·约瑟夫森是瑞典国宝级演员,也是英格玛·伯格曼的御用演员、《牺牲》的主演。我们知道瑞典皇家剧院与伯格曼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牺牲》主要用了伯格曼的班底,尤其是他的御用摄像师凯文·尼克维斯特。在岛上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就轮流住在尼克维斯特和约瑟夫森家里。伯格曼的亲密战友、御用女主角丽芙·乌曼也参加过这部影片的试镜。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竟然从没见过面。当时伯格曼并没有“忙”,他所居住的法罗岛就紧挨着哥特兰岛;而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们甚至曾经在同一座楼里——就是不见面。但他们无疑是非常认可彼此的,在这里很有必要将伯格曼的那段评价重新翻译一下:
第一次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就给我留下了奇迹般的印象。我意想不到地来到了自己一直想进入,却久久没有找到钥匙的那扇门口,而塔可夫斯基却已经自信、自如地待在里面。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将我一直想表达却无法表达的内容呈现出来的人。这令人激动、鼓舞。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电影大师,他创造了新的、有机的电影语言,像一面镜子、一场梦一般反映了生活。
电影,除去纪录片的话,就是梦和幻想。所以我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对他来说,梦境是显明的,他什么也不解释——但顺便插一句,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可解释的呢?他是一个先知,能够用如此繁复,却同时又如此轻柔的艺术风格将自己的梦境一一呈现出来,我一生都在叩响的那扇大门,他却自然而然就已经在里面了。而我却只有两三次机会进入而已。
伯格曼对塔可夫斯基的评价之于瑞典电影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无须放大《瑞典夏之夜》中的矛盾、隔阂、语言障碍,这是他们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导演经历各种“颠倒梦想”,至于他们是否认同导演,我想几十年后还能排演这出戏就已经是最好的说明。
塔可夫斯基:“最会做梦”的先知
总体来说,塔可夫斯基可能是世界导演中最会做梦的。不仅是说他的影像“如梦幻泡影”,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他的梦也非常多,而且都像电影一般。当然,这些梦大多数是“梦魇”,最离奇的是,他的梦总是会“成真”,不是在电影里就是在生活中。
拍《牺牲》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已经知道自己罹患肺癌,次年就去世了。这一年,他做的梦非常多,《牺牲》中那些莫名的鬼魅气息正是他自己的噩梦。这个故事带有“末世论”色彩,表达的是在一个信仰崩坏的世界,培植信念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信念,道德、价值观的坍塌会导致灾祸的发生,主人公就预感到核灾难的一幕。神奇的是,这部影片刚杀青,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发生了。也是在拍摄《牺牲》的时候,摄制组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勘景,走到一条街道上,塔可夫斯基突然变得非常紧张,对约瑟夫森说这个地方不吉利,很快会有灾祸发生。次年,即《牺牲》上映当年,瑞典首相帕尔梅就恰好在那个地点被刺客枪杀,至今没有找到凶手。
这样说起来似乎有点“怪力乱神”,但恰好印证了伯格曼关于塔可夫斯基“先知先觉”的判断。《瑞典夏之夜》中,演员们抱怨他整夜等他需要的“晨曦微光”的到来。第一天因为他们到达哥特兰岛的时候都已经凌晨六点了,根本拍不到他需要的效果,于是演员们原地等待,又等了一整天到次日凌晨四点,这就是这出戏剧的“故事背景”。实际上他等的不仅是光,他还等风到,等云到。奇妙的是,需要的那些自然现象都被他等到了。在哥特兰岛上的重头戏,亚历山大火烧自己的宅子,他嫌风不够大,烧得不精彩,于是又重新建起房子,这回就像孔明借东风一样,烧了个透,成为电影史上经典的一个长镜头。
剧组(大约五十人)登岛的时候,塔可夫斯基给大家开会。他说:“我们必须秘密地跟大自然签约,得让它帮助我们拍摄。”这听起来非常“万物有灵论”,但他就是这么想的,甚至是这么做的。为了营造孤寂的气氛,他在岛上摧花折柳,将好端端的稠李树都给砍了。影片中演员的表演都带点“鬼”气,那都是他一点点“调教”的结果,因此电影的拍摄进度非常慢。影片中有一幕“公鸡的梦”,就是他在岛上做的梦直接转换为影像。他事先向制片人(在《瑞典夏之夜》中她的“抓狂”是非常真实的,她差点给逼疯了)描述了自己的梦:他梦见自己死了,穿着白衣服躺在沙发上。房间里有很多人跪在那里。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穿着白衣服,如同天使一般。然后他说梦见了几乎就是弗洛伊德式的场景: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赶公鸡。一切都真真儿地清晰,“好像电影里那样”。他还梦见脚下坐着一个女人,好像他的妻子,她转脸,转脸……却并不是。
然后,他在一天之内,动员整个摄制组上阵充当演员,在黄昏与夜晚交替之际,用一个长镜头把这个梦境拍了出来。所有人脸上都是大写的“服”。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将这些偶然与巧合归结为塔可夫斯基作为伟大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正是这种洞察力,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深远的洞见,让瑞典艺术家们至今对他难以忘怀,《瑞典夏之夜》就是如明镜一般的证据。很多杰出的艺术家都有这种“穿透力”,比如他最崇敬的达·芬奇。恰好今年是达·芬奇逝世五百周年,我们可以一起纪念,或许这也是“偶然与巧合”。
《瑞典夏之夜》以《牺牲》的理念为核心
“白夜的季节来临了。”
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剧本的第一句话。这部电影也是瑞典电影的骄傲——它是瑞典电影人邀请塔可夫斯基全程在瑞典拍摄的,主要取景于斯德哥尔摩,以及波罗的海的著名旅游景点哥特兰岛。“白夜”,正是其最迷人的一道“景观”。
最近,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瑞典皇家剧院来到首都剧场,带来了一出《瑞典夏之夜》,讲述了发生在三十多年前拍摄现场的某个“白夜”的、“如梦”般的故事。
在观众还没进场的时候。演员实际上已经在剧场外出现了。和我一起进剧场的是一个典型的光头北欧美男子,他拿着一杯咖啡,缓缓走向观众席,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使馆工作人员吧?
美男子再出现的时候,已经在舞台上——在仿佛“白夜”的光线中(整出戏的布光显然经过了精心安排),观众没有觉察到故事已经开始,就仿佛在瑞典夏夜光线的明暗交替中,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内感受到“白夜”的漫长:漫长,来自猝不及防的观众心理时间,它的故事背景与核心毫无疑问就是塔可夫斯基电影《牺牲》的拍摄和理念,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是非常陌生的。戏剧中使用的几段《牺牲》中的影像,准确地体现了塔可夫斯基的创作指向:片头的达·芬奇名作《博士来拜》(塔可夫斯基在意大利参观乌菲齐美术馆的时候深受感动,当时就决定要把这个主题用于下一部影片),在斯德哥尔摩老城区拍摄的奇妙的核灾难场面(奇妙的是外景地与《博士来拜》的某处细节完全重合),以及片尾海边那棵复活的树,等等。
但是对台上的演员而言,他们只不过在演出一个日常的时刻,好比漫长夏夜的一段小憩,做了一个短暂的梦而已。在梦里,他们和日常一样谈论艺术与人生,由于工作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与导演产生了矛盾,只不过梦醒来后,他们似乎对这个俄罗斯人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这个拍摄过程,随时都能让他们见到真实的“梦境”。
两位影史最伟大导演
相邻却未见面
剧本的编剧厄兰·约瑟夫森是瑞典国宝级演员,也是英格玛·伯格曼的御用演员、《牺牲》的主演。我们知道瑞典皇家剧院与伯格曼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牺牲》主要用了伯格曼的班底,尤其是他的御用摄像师凯文·尼克维斯特。在岛上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就轮流住在尼克维斯特和约瑟夫森家里。伯格曼的亲密战友、御用女主角丽芙·乌曼也参加过这部影片的试镜。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竟然从没见过面。当时伯格曼并没有“忙”,他所居住的法罗岛就紧挨着哥特兰岛;而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们甚至曾经在同一座楼里——就是不见面。但他们无疑是非常认可彼此的,在这里很有必要将伯格曼的那段评价重新翻译一下:
第一次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就给我留下了奇迹般的印象。我意想不到地来到了自己一直想进入,却久久没有找到钥匙的那扇门口,而塔可夫斯基却已经自信、自如地待在里面。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将我一直想表达却无法表达的内容呈现出来的人。这令人激动、鼓舞。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电影大师,他创造了新的、有机的电影语言,像一面镜子、一场梦一般反映了生活。
电影,除去纪录片的话,就是梦和幻想。所以我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对他来说,梦境是显明的,他什么也不解释——但顺便插一句,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可解释的呢?他是一个先知,能够用如此繁复,却同时又如此轻柔的艺术风格将自己的梦境一一呈现出来,我一生都在叩响的那扇大门,他却自然而然就已经在里面了。而我却只有两三次机会进入而已。
伯格曼对塔可夫斯基的评价之于瑞典电影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无须放大《瑞典夏之夜》中的矛盾、隔阂、语言障碍,这是他们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导演经历各种“颠倒梦想”,至于他们是否认同导演,我想几十年后还能排演这出戏就已经是最好的说明。
塔可夫斯基:“最会做梦”的先知
总体来说,塔可夫斯基可能是世界导演中最会做梦的。不仅是说他的影像“如梦幻泡影”,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他的梦也非常多,而且都像电影一般。当然,这些梦大多数是“梦魇”,最离奇的是,他的梦总是会“成真”,不是在电影里就是在生活中。
拍《牺牲》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已经知道自己罹患肺癌,次年就去世了。这一年,他做的梦非常多,《牺牲》中那些莫名的鬼魅气息正是他自己的噩梦。这个故事带有“末世论”色彩,表达的是在一个信仰崩坏的世界,培植信念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信念,道德、价值观的坍塌会导致灾祸的发生,主人公就预感到核灾难的一幕。神奇的是,这部影片刚杀青,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发生了。也是在拍摄《牺牲》的时候,摄制组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勘景,走到一条街道上,塔可夫斯基突然变得非常紧张,对约瑟夫森说这个地方不吉利,很快会有灾祸发生。次年,即《牺牲》上映当年,瑞典首相帕尔梅就恰好在那个地点被刺客枪杀,至今没有找到凶手。
这样说起来似乎有点“怪力乱神”,但恰好印证了伯格曼关于塔可夫斯基“先知先觉”的判断。《瑞典夏之夜》中,演员们抱怨他整夜等他需要的“晨曦微光”的到来。第一天因为他们到达哥特兰岛的时候都已经凌晨六点了,根本拍不到他需要的效果,于是演员们原地等待,又等了一整天到次日凌晨四点,这就是这出戏剧的“故事背景”。实际上他等的不仅是光,他还等风到,等云到。奇妙的是,需要的那些自然现象都被他等到了。在哥特兰岛上的重头戏,亚历山大火烧自己的宅子,他嫌风不够大,烧得不精彩,于是又重新建起房子,这回就像孔明借东风一样,烧了个透,成为电影史上经典的一个长镜头。
剧组(大约五十人)登岛的时候,塔可夫斯基给大家开会。他说:“我们必须秘密地跟大自然签约,得让它帮助我们拍摄。”这听起来非常“万物有灵论”,但他就是这么想的,甚至是这么做的。为了营造孤寂的气氛,他在岛上摧花折柳,将好端端的稠李树都给砍了。影片中演员的表演都带点“鬼”气,那都是他一点点“调教”的结果,因此电影的拍摄进度非常慢。影片中有一幕“公鸡的梦”,就是他在岛上做的梦直接转换为影像。他事先向制片人(在《瑞典夏之夜》中她的“抓狂”是非常真实的,她差点给逼疯了)描述了自己的梦:他梦见自己死了,穿着白衣服躺在沙发上。房间里有很多人跪在那里。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穿着白衣服,如同天使一般。然后他说梦见了几乎就是弗洛伊德式的场景: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赶公鸡。一切都真真儿地清晰,“好像电影里那样”。他还梦见脚下坐着一个女人,好像他的妻子,她转脸,转脸……却并不是。
然后,他在一天之内,动员整个摄制组上阵充当演员,在黄昏与夜晚交替之际,用一个长镜头把这个梦境拍了出来。所有人脸上都是大写的“服”。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将这些偶然与巧合归结为塔可夫斯基作为伟大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正是这种洞察力,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深远的洞见,让瑞典艺术家们至今对他难以忘怀,《瑞典夏之夜》就是如明镜一般的证据。很多杰出的艺术家都有这种“穿透力”,比如他最崇敬的达·芬奇。恰好今年是达·芬奇逝世五百周年,我们可以一起纪念,或许这也是“偶然与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