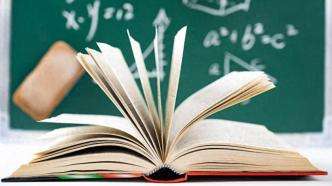嘉宾:许知远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作者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 菁 《三联生活周刊》常务副主编
主题:历史和未来一样崭新
时间:2019年5月22 日19:00—21:30
地点:77剧场·北京东城区美术馆后街 77 号
主办:单向空间、世纪文景、活字文化
规模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东西会变成生命力
李菁:《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你计划中“梁启超传三卷本”的第一卷。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梁启超?你在序里很戏剧化地描述你在跟他的对视中找到了一种感觉,有一种顿悟。你是想写一个长的、宽广的、时代感的东西,正好碰到了梁启超吗?
许知远:我觉得还是跟我从事新闻业有关吧。我2002年毕业之后就做新闻记者,梁启超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等于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开创者。这是一个亲切感。而且当时我就做报社的“主笔”,这个名字在被搁置多年后重新启用。梁启超当年也是做主笔。所以那个时候跟他就有同感。
写三卷本,很大原因是我个人的一个弱点——我对规模的迷恋。我喜欢非常厚的书,我想在杭州开一个很大的书店。在写的过程中,我确实知道了规模的好处,规模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东西。
李菁:那你不觉得到了一定规模,你的混乱和庞杂会成为一个缺点吗?
许知远: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混乱和庞杂会变成生命力。像梁启超的转型,他介入思想生活、学术生活、政治生活所有机构的建立,19世纪末晚清帝国到民国的建立过程中,他涉及了所有的领域,他是一个强烈的自我更新者。
李菁:以我对你的了解,感觉你更应该写一个《光荣与梦想》式的书,那个体量也够大。我还想知道,你在梁启超身上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击中你的点?
许知远:《光荣与梦想》是事件构成的,我还是对人物传记、对人性格的形成更迷恋。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梁启超个体和他周围的朋友,一个“群传”的概念。过分繁琐的事件对我已经构不成强烈的吸引,一个人对外界的变化做出怎样的应对,他内心的困惑和焦灼,对这些我会产生更强的兴趣。
李菁:这种写作的风格也是你第一次涉足,你用大量的注。这实际上跟你相对熟悉的酣畅淋漓的主观表达是有一些冲突的。想知道这是不是你有意识的一个改变?
许知远:原因有三:第一,确实我年纪大了,我没法像20岁年少轻狂了;第二,我确实想让读者包括我自己,进入那个历史情境。如果你把当时的语言、当时的表达方式全都白话化,那实际上会错失去理解当时情境的感觉——他们是这样写作,他们这样讲话,他们绕来绕去——会失去这样一种质感;第三,出于某种意义上自卑嘛,我是学微电子的,我要写一本这样的书,一定要显得像做学术一样,我想证明我是可以写的。
李菁:请问马勇老师,您作为一名近代史学者,到现在为止在学界来说,梁启超是一个显学吗?
马勇:简单地说,近代史研究排100左右的主题,肯定有梁启超;排50的会有;排前10的没有。显学算不上,应该算是近代史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这么讲。现在写梁启超的传记不超过10本,所以可做的空间还有很多。
为什么要写三卷本就想证明我不是一个网红
李菁:作为历史学家来写梁启超和作为一个许知远这样的网红写梁启超,会特别不一样吧?我本来想问一下许知远,你现在身份比较多,你觉得“演员”和“网红”哪一个身份更符合你?
许知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三卷本吗?我就想证明我不是一个网红。
马勇:我本来期望他能够写得很不一样。因为他和梁启超有很强的相似之处,无论经历上还是家国情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梁启超传当中,能够写出完全不一样,就像梁启超写李鸿章的,还没有。梁启超的文字很能够吸引人。
许知远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引文和注释,原来我担心会很影响阅读。但是刚才朗读的那个环节,我在旁边跟他讲,文字能够被诵读的,当代中国已经很少了。写完之后敢让别人读或者自己读起来的文字,真正讲究韵、讲究气的文字,现在真的是很少了。
能写出自己的特色,和纯粹历史专业的人写得不一样,他这个算是一个示范。历史学家肯定不会追求形容词加一个形容词,然后中间顿掉,这种带有感情的文字。我觉得他写梁启超,就应该写出一种感情,写出这种感觉。他现在写出这种特色来了,而且跟历史专业写作,我觉得有差别,但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李菁:那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您以往没太注意到,或者没有发现的一些新的一些史料之类的?
马勇:他这本书的注释选择用尾注而不是脚注,读的时候有些细节我都不知道,我得翻了尾注再往回找。他的观察视角和我们之前有很大的差别。他对一些人际之间,比如家庭、朋友圈的人际关系,做了很多的分析。我觉得在这方面很受启发。这些人物关系写完之后,可能会使近代历史的图景有所改变。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梁启超传记当中,没有这么凸显出来。
李菁:你看马老师讲这意思,其实对你而言,那些脚注或是尾注,这种写作是不必要的。那你写第二卷准备调整吗?
许知远:第二卷里注可能会更多吧。马老师讲的我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我觉得,我比梁启超写文章写得好啊。
李菁:好在哪里?
许知远:梁启超的太飘了。而且他没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叙事感。他只是一个传记的开创者,但并不代表他写得多么好。非常不负责任地说一句,我觉得我将建立起新的传记的传统。阅读的流畅性和史料的解读,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可能还没有做到最好,但基本上也很好了。我的注脚不会减少,而且我很希望它会成为传记写作的一个规范,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典范。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马勇:我不是反对,我不是讲注释多与少,我只是说影响你的那个流畅。等你三本都写完了,可能会一鼓作气再写一个简本出来。我是讲这个意思。
将所有耐心都耗在等待这些材料发生关联
李菁:你写的过程中一定也做了很多的案头准备,像马老师这样近代史学者的书也看了不少。这么多历史学家的著作,有没有给你一些困扰?对自己能完成这个作品有没有怀疑过?
许知远:书刚刚印出来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还真写出来了,真出版了!我很少重新看自己写的东西,翻了一下,那么多注脚,都不知道我怎么抄了这么多东西。
我在写到第三四年的时候,经常陷到那个里面。找不到方向,觉得非常无聊。幸好,平时还有机会(做《十三邀》)见到黑木瞳这些人,可以缓解一下。确实史料给我带来很多的问题,你把它拼不成逻辑,它是几层的困扰。
只有在偶尔的时刻,我感觉到灵光乍现,比如说梁启超逃亡的过程,那是我从晚上十点多写到凌晨四点多写完的,写了六个小时。我感觉我的大脑都在燃烧,整个人烧起来的感觉,就不知道怎么办。
但大部分时候是非常无聊和枯燥的。找了各种关于梁启超的史料就开始抄,觉得哪些东西有用,就开始在电脑上打,从这个抄到那个,从那个抄到这个。抄的过程当中,你对史料就慢慢有感觉。把所有的史料打印出来我随身带着,无聊的时候就看一看。
你不知道那些片段的连接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所以你在等待。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我把所有的耐心都耗在等待这些材料发生关联的过程中。有时候兴冲冲半夜醒了,“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出场”,我经常是半夜想起来就记在本上,“这个开头太牛了,明天早上写”。但是等到早上一看,“这个怎么能作为开头呢?”
李菁:在历史学方面,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写作,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想请教马老师,这一类写作,您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马勇:我个人觉得,近些年非专业的写作,其实对历史学有很大的冲击和贡献。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许知远学的是微电子,更准确说是“跨专业”写历史。在之前这些梁启超传记写作者中,只有许知远和解玺璋老师有媒体从业经历,有这个经历和没有这个的经历,对于理解传记是不同的。不能简单说学历史的就写得一定好,没学历史的就写得一定差。
很想代入戏剧的感觉看到历史充满偶然和可能
李菁:是有一个什么新的史观在带动你写这本书吗?
许知远:首先我很努力地把它还原成人的故事。在我们很多历史写作里,人是消失的,缺少他个人的成长故事。然后我很着力做代际的故事——更早的一代,更晚的一代,经验是很不一样的。代际之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代际是第一卷中非常显著的一个部分。
另外我很想把全球的视角带到这个书里面。第一卷还不明显,到第二卷梁启超流亡到日本的部分之后,就非常明显。我必须要描绘当时明治末年的社会,才能表达出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的那种感受。第二卷和第三卷会非常明显地表达。
还有,我很想把戏剧的感觉代入进来。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能看到历史是充满了偶然和可能,充满了分歧、问题和争论的。我希望它是一个全景式的表达,在北京一个考生去琉璃厂买东西,去哪里吃饭,城市的面貌是怎样的?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在哪里?
这里面还写到谭鑫培,写到很多人。因为他们是同代。本来我想写黄飞鸿,当梁启超他们在公车上书,在看到状况想改变的时候,在台湾刘永福那些人,他们试图顽强抵抗日本人的到来,刘永福手下的一个军官就是黄飞鸿。其实我是想把很多历史的命运重叠放在里面。
翁同龢也是,他曾经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又怎么淡出历史舞台;黄遵宪也很重要,他收到梁启超的信,他在报纸上看到梁启超的一些新闻,他非常感伤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我希望大家能读到很多不同的情绪,它像一个戏剧,像一个舞台,灯光有时照到中央,有的时候也在边缘。有的时候你就出局了,出局之后你可能又重新回来了。
李菁:我知道你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写一个人物,你是想通过这个人物写一个时代,写一个变迁。但我个人有一些小小的疑问,我觉得因为你的野心太大了,你想写的人太多了,舞台也写太大了。有的时候,这个主角模糊了——大段的康有为,或者大段的翁同龢,让我忘记了这是写梁启超的书了。你感受到这种矛盾了吗?是因为资料受限吗?
许知远:在这个历史当中,可以说关于梁启超的记载很少。如果你不勾勒他的语境,不勾勒那个环境,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带动出来的。因为过去没有这些史料,他也不是重要人物,他被遮蔽在康有为的下面了,相关的他的史料的确是很少。
历史学不仅要有材料还要有想象、有感觉
李菁:今天这个发布会现场有方言朗读的环节,还有乐队助兴。
许知远:今天的乐队是我们自己找的,因为我很喜欢花伦乐队,我觉得梁启超也会喜欢电音吧。如果说我写的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话,我确实带有很鲜明的当下的情绪来写历史。你试想,当年梁启超听到“人体解剖”,听到“光学”、“电学”;谭嗣同说,三纲五常太压抑了,世界上有这么多星球,如果每一个人住在一个星球上,就一个人住,我们不就解脱了吗?
他们其实对世界是有莫名其妙的思维方式的,有很超脱的想法,我觉得以前我们是把他们僵化了。今天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他们复活。
就像有个段子说,逃亡前谭嗣同曾经跟梁启超讲过,海外华人都讲广东话,你可以鼓动他们革命;我讲湖南话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得留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不是海外华人——淘金热的那批广东人前往了旧金山、澳大利亚、北美,怎么可能有康有为、孙中山他们的舞台?如果是一群湖南人在海外,那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他们无法交流,他们没有宗族关系。
人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些具体脉络连在一起的。我们以往的历史书会把这些特别细的脉络都扔掉,弄成一种僵化的概念了。而我恰是想表达这些东西。
李菁:纵观梁启超一生的轨迹,他也的确比较多变和善变——一会儿是改良派,然后还保皇过,后来跟孙中山还论战过。这也是对他比较负面一些评价的来源。比较有名的那个约瑟夫·列文森也写过他的一本书,对他有一段比较煽情的感慨——很多年轻人沿着他的路走到了他当年非常努力达到的一个境地,而他又在搞孔子这些东西了。
马老师,许知远在序言里面说梁启超是被世界低估的一个人,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马勇:这个看个人对史料的理解。我是觉得有关梁启超还有很多谜没有解开。在许知远这本第一卷里面也是,比如政变发生的过程中,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传导过去的?按照现在这个脉络,很多问题还是不好解释。历史走过了,可能就永远也解不开。
但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梁启超的思想被低估了。梁启超自认为“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在近代中国转型期间,他是绝对反对突变、反对暴力的变化。他大概很早就认同严复,接纳渐进的改革,主张慢慢地来改变。这里头大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保守主义。梁启超就属于这种保守主义。
最近我也在思考,梁启超的兴趣绝对不在学术,他的兴趣就在政治。他为什么晚年回到学术?这里面有很多的解读空间。另外,对辛亥革命他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个现在也是有很多隐隐约约的争论,大家感觉他好像并不是一个保皇派,并不是清政府的加持者,关键的时候他有作为,但后来他又回避,这都很有意思。
到目前为止的这些谜,都需要梁启超研究的不断推进才能解读。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东西。历史学家,也就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我们才敢说一句:“历史学不仅要有材料,还要有想象,要有感觉。否则就是编大事记了。”
为自己存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添加小小的燃料或水滴
李菁:你这本书的腰封,强调的是“许知远的转型之作”。我想问你,你想往哪儿转?转成什么样子?梁启超晚年进入到学术,你比梁启超启动得还更早一些,现在就要往这个路上走,是吗?
许知远:我是有一个计划的,我有一个后半生的计划。我这么说,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但却是事实发生的。我有一个漫长的计划,希望梁启超三卷只是我九卷本计划的一个开始,一个序言。我想通过几个人物,理解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转变,从嘉庆年间帝国最后的余晖,到鸦片战争、到1901年沉入谷底,然后到寻找中国的革命。我是有这样一个很长的计划。
对我来说,这个计划就像我一个航行的锚一样定在那里。因为我也经常会跟随这个时代飘摇,内心不确定。其实有的时候我能够体会那样一种感觉,在一本书即将快要写到完结部分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陪伴自己二十年的一个老朋友突然就离去了。我喜欢那种画面感。对我来说,可能最后写完那个画面在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我在等待那个时间的到来。
因为我要克服我的厌倦。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厌倦的人,对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必须找不同的事情来抵御我的厌倦。
李菁:那我还是问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你以往的写作风格,包括在《经济观察报》以及写专栏的时候,更多是一种围绕个人观点的表达,都是为文风畅快来服务的。而“梁启超传”这个写作实际上是更回到文本上面,尽量还原梁启超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对你来说,哪一种表达是技术上你觉得更喜欢的?
许知远:尽管我刚才讲话有点故作嚣张,或者自以为是,其实不是的。我是觉得我们存在于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应该能融入其中,我也能为里面添加一块小小的燃料或一个小小的水滴。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共同写一本书。我要加入这所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创造力、你的个人感受都没那么重要,因为你只是大的传统中的一部分。但同时,你的个人创造力又很重要,因为你必须为伟大的传统增加一点点不同的色彩,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对我来说,我确实在写第一卷的时候找到了某种召唤。这个召唤让我安静、镇定。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持续这个召唤。我未来还渴望更多读者,希望很多人通过这个书,或者通过阅读内容能够获得一点点的历史感受。
我们需要建立历史感受。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感受,我们将意识到我们不是那么孤立,我们跟世界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有紧密的连接。这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更充沛的力量。我们也能影响别人,我们不是孤立地生活,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彼此激励,让人感到温暖,又彼此提醒、互相批评的这么一个共同体。所以我的梁启超传,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水滴。
整理/雨驿
嘉宾:许知远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作者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 菁 《三联生活周刊》常务副主编
主题:历史和未来一样崭新
时间:2019年5月22 日19:00—21:30
地点:77剧场·北京东城区美术馆后街 77 号
主办:单向空间、世纪文景、活字文化
规模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东西会变成生命力
李菁:《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你计划中“梁启超传三卷本”的第一卷。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梁启超?你在序里很戏剧化地描述你在跟他的对视中找到了一种感觉,有一种顿悟。你是想写一个长的、宽广的、时代感的东西,正好碰到了梁启超吗?
许知远:我觉得还是跟我从事新闻业有关吧。我2002年毕业之后就做新闻记者,梁启超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等于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开创者。这是一个亲切感。而且当时我就做报社的“主笔”,这个名字在被搁置多年后重新启用。梁启超当年也是做主笔。所以那个时候跟他就有同感。
写三卷本,很大原因是我个人的一个弱点——我对规模的迷恋。我喜欢非常厚的书,我想在杭州开一个很大的书店。在写的过程中,我确实知道了规模的好处,规模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东西。
李菁:那你不觉得到了一定规模,你的混乱和庞杂会成为一个缺点吗?
许知远: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混乱和庞杂会变成生命力。像梁启超的转型,他介入思想生活、学术生活、政治生活所有机构的建立,19世纪末晚清帝国到民国的建立过程中,他涉及了所有的领域,他是一个强烈的自我更新者。
李菁:以我对你的了解,感觉你更应该写一个《光荣与梦想》式的书,那个体量也够大。我还想知道,你在梁启超身上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击中你的点?
许知远:《光荣与梦想》是事件构成的,我还是对人物传记、对人性格的形成更迷恋。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梁启超个体和他周围的朋友,一个“群传”的概念。过分繁琐的事件对我已经构不成强烈的吸引,一个人对外界的变化做出怎样的应对,他内心的困惑和焦灼,对这些我会产生更强的兴趣。
李菁:这种写作的风格也是你第一次涉足,你用大量的注。这实际上跟你相对熟悉的酣畅淋漓的主观表达是有一些冲突的。想知道这是不是你有意识的一个改变?
许知远:原因有三:第一,确实我年纪大了,我没法像20岁年少轻狂了;第二,我确实想让读者包括我自己,进入那个历史情境。如果你把当时的语言、当时的表达方式全都白话化,那实际上会错失去理解当时情境的感觉——他们是这样写作,他们这样讲话,他们绕来绕去——会失去这样一种质感;第三,出于某种意义上自卑嘛,我是学微电子的,我要写一本这样的书,一定要显得像做学术一样,我想证明我是可以写的。
李菁:请问马勇老师,您作为一名近代史学者,到现在为止在学界来说,梁启超是一个显学吗?
马勇:简单地说,近代史研究排100左右的主题,肯定有梁启超;排50的会有;排前10的没有。显学算不上,应该算是近代史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这么讲。现在写梁启超的传记不超过10本,所以可做的空间还有很多。
为什么要写三卷本就想证明我不是一个网红
李菁:作为历史学家来写梁启超和作为一个许知远这样的网红写梁启超,会特别不一样吧?我本来想问一下许知远,你现在身份比较多,你觉得“演员”和“网红”哪一个身份更符合你?
许知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三卷本吗?我就想证明我不是一个网红。
马勇:我本来期望他能够写得很不一样。因为他和梁启超有很强的相似之处,无论经历上还是家国情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梁启超传当中,能够写出完全不一样,就像梁启超写李鸿章的,还没有。梁启超的文字很能够吸引人。
许知远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引文和注释,原来我担心会很影响阅读。但是刚才朗读的那个环节,我在旁边跟他讲,文字能够被诵读的,当代中国已经很少了。写完之后敢让别人读或者自己读起来的文字,真正讲究韵、讲究气的文字,现在真的是很少了。
能写出自己的特色,和纯粹历史专业的人写得不一样,他这个算是一个示范。历史学家肯定不会追求形容词加一个形容词,然后中间顿掉,这种带有感情的文字。我觉得他写梁启超,就应该写出一种感情,写出这种感觉。他现在写出这种特色来了,而且跟历史专业写作,我觉得有差别,但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李菁:那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您以往没太注意到,或者没有发现的一些新的一些史料之类的?
马勇:他这本书的注释选择用尾注而不是脚注,读的时候有些细节我都不知道,我得翻了尾注再往回找。他的观察视角和我们之前有很大的差别。他对一些人际之间,比如家庭、朋友圈的人际关系,做了很多的分析。我觉得在这方面很受启发。这些人物关系写完之后,可能会使近代历史的图景有所改变。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梁启超传记当中,没有这么凸显出来。
李菁:你看马老师讲这意思,其实对你而言,那些脚注或是尾注,这种写作是不必要的。那你写第二卷准备调整吗?
许知远:第二卷里注可能会更多吧。马老师讲的我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我觉得,我比梁启超写文章写得好啊。
李菁:好在哪里?
许知远:梁启超的太飘了。而且他没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叙事感。他只是一个传记的开创者,但并不代表他写得多么好。非常不负责任地说一句,我觉得我将建立起新的传记的传统。阅读的流畅性和史料的解读,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可能还没有做到最好,但基本上也很好了。我的注脚不会减少,而且我很希望它会成为传记写作的一个规范,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典范。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马勇:我不是反对,我不是讲注释多与少,我只是说影响你的那个流畅。等你三本都写完了,可能会一鼓作气再写一个简本出来。我是讲这个意思。
将所有耐心都耗在等待这些材料发生关联
李菁:你写的过程中一定也做了很多的案头准备,像马老师这样近代史学者的书也看了不少。这么多历史学家的著作,有没有给你一些困扰?对自己能完成这个作品有没有怀疑过?
许知远:书刚刚印出来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还真写出来了,真出版了!我很少重新看自己写的东西,翻了一下,那么多注脚,都不知道我怎么抄了这么多东西。
我在写到第三四年的时候,经常陷到那个里面。找不到方向,觉得非常无聊。幸好,平时还有机会(做《十三邀》)见到黑木瞳这些人,可以缓解一下。确实史料给我带来很多的问题,你把它拼不成逻辑,它是几层的困扰。
只有在偶尔的时刻,我感觉到灵光乍现,比如说梁启超逃亡的过程,那是我从晚上十点多写到凌晨四点多写完的,写了六个小时。我感觉我的大脑都在燃烧,整个人烧起来的感觉,就不知道怎么办。
但大部分时候是非常无聊和枯燥的。找了各种关于梁启超的史料就开始抄,觉得哪些东西有用,就开始在电脑上打,从这个抄到那个,从那个抄到这个。抄的过程当中,你对史料就慢慢有感觉。把所有的史料打印出来我随身带着,无聊的时候就看一看。
你不知道那些片段的连接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所以你在等待。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我把所有的耐心都耗在等待这些材料发生关联的过程中。有时候兴冲冲半夜醒了,“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出场”,我经常是半夜想起来就记在本上,“这个开头太牛了,明天早上写”。但是等到早上一看,“这个怎么能作为开头呢?”
李菁:在历史学方面,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写作,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想请教马老师,这一类写作,您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马勇:我个人觉得,近些年非专业的写作,其实对历史学有很大的冲击和贡献。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许知远学的是微电子,更准确说是“跨专业”写历史。在之前这些梁启超传记写作者中,只有许知远和解玺璋老师有媒体从业经历,有这个经历和没有这个的经历,对于理解传记是不同的。不能简单说学历史的就写得一定好,没学历史的就写得一定差。
很想代入戏剧的感觉看到历史充满偶然和可能
李菁:是有一个什么新的史观在带动你写这本书吗?
许知远:首先我很努力地把它还原成人的故事。在我们很多历史写作里,人是消失的,缺少他个人的成长故事。然后我很着力做代际的故事——更早的一代,更晚的一代,经验是很不一样的。代际之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代际是第一卷中非常显著的一个部分。
另外我很想把全球的视角带到这个书里面。第一卷还不明显,到第二卷梁启超流亡到日本的部分之后,就非常明显。我必须要描绘当时明治末年的社会,才能表达出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的那种感受。第二卷和第三卷会非常明显地表达。
还有,我很想把戏剧的感觉代入进来。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能看到历史是充满了偶然和可能,充满了分歧、问题和争论的。我希望它是一个全景式的表达,在北京一个考生去琉璃厂买东西,去哪里吃饭,城市的面貌是怎样的?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在哪里?
这里面还写到谭鑫培,写到很多人。因为他们是同代。本来我想写黄飞鸿,当梁启超他们在公车上书,在看到状况想改变的时候,在台湾刘永福那些人,他们试图顽强抵抗日本人的到来,刘永福手下的一个军官就是黄飞鸿。其实我是想把很多历史的命运重叠放在里面。
翁同龢也是,他曾经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又怎么淡出历史舞台;黄遵宪也很重要,他收到梁启超的信,他在报纸上看到梁启超的一些新闻,他非常感伤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我希望大家能读到很多不同的情绪,它像一个戏剧,像一个舞台,灯光有时照到中央,有的时候也在边缘。有的时候你就出局了,出局之后你可能又重新回来了。
李菁:我知道你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写一个人物,你是想通过这个人物写一个时代,写一个变迁。但我个人有一些小小的疑问,我觉得因为你的野心太大了,你想写的人太多了,舞台也写太大了。有的时候,这个主角模糊了——大段的康有为,或者大段的翁同龢,让我忘记了这是写梁启超的书了。你感受到这种矛盾了吗?是因为资料受限吗?
许知远:在这个历史当中,可以说关于梁启超的记载很少。如果你不勾勒他的语境,不勾勒那个环境,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带动出来的。因为过去没有这些史料,他也不是重要人物,他被遮蔽在康有为的下面了,相关的他的史料的确是很少。
历史学不仅要有材料还要有想象、有感觉
李菁:今天这个发布会现场有方言朗读的环节,还有乐队助兴。
许知远:今天的乐队是我们自己找的,因为我很喜欢花伦乐队,我觉得梁启超也会喜欢电音吧。如果说我写的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话,我确实带有很鲜明的当下的情绪来写历史。你试想,当年梁启超听到“人体解剖”,听到“光学”、“电学”;谭嗣同说,三纲五常太压抑了,世界上有这么多星球,如果每一个人住在一个星球上,就一个人住,我们不就解脱了吗?
他们其实对世界是有莫名其妙的思维方式的,有很超脱的想法,我觉得以前我们是把他们僵化了。今天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他们复活。
就像有个段子说,逃亡前谭嗣同曾经跟梁启超讲过,海外华人都讲广东话,你可以鼓动他们革命;我讲湖南话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得留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不是海外华人——淘金热的那批广东人前往了旧金山、澳大利亚、北美,怎么可能有康有为、孙中山他们的舞台?如果是一群湖南人在海外,那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他们无法交流,他们没有宗族关系。
人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些具体脉络连在一起的。我们以往的历史书会把这些特别细的脉络都扔掉,弄成一种僵化的概念了。而我恰是想表达这些东西。
李菁:纵观梁启超一生的轨迹,他也的确比较多变和善变——一会儿是改良派,然后还保皇过,后来跟孙中山还论战过。这也是对他比较负面一些评价的来源。比较有名的那个约瑟夫·列文森也写过他的一本书,对他有一段比较煽情的感慨——很多年轻人沿着他的路走到了他当年非常努力达到的一个境地,而他又在搞孔子这些东西了。
马老师,许知远在序言里面说梁启超是被世界低估的一个人,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马勇:这个看个人对史料的理解。我是觉得有关梁启超还有很多谜没有解开。在许知远这本第一卷里面也是,比如政变发生的过程中,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传导过去的?按照现在这个脉络,很多问题还是不好解释。历史走过了,可能就永远也解不开。
但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梁启超的思想被低估了。梁启超自认为“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在近代中国转型期间,他是绝对反对突变、反对暴力的变化。他大概很早就认同严复,接纳渐进的改革,主张慢慢地来改变。这里头大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保守主义。梁启超就属于这种保守主义。
最近我也在思考,梁启超的兴趣绝对不在学术,他的兴趣就在政治。他为什么晚年回到学术?这里面有很多的解读空间。另外,对辛亥革命他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个现在也是有很多隐隐约约的争论,大家感觉他好像并不是一个保皇派,并不是清政府的加持者,关键的时候他有作为,但后来他又回避,这都很有意思。
到目前为止的这些谜,都需要梁启超研究的不断推进才能解读。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东西。历史学家,也就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我们才敢说一句:“历史学不仅要有材料,还要有想象,要有感觉。否则就是编大事记了。”
为自己存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添加小小的燃料或水滴
李菁:你这本书的腰封,强调的是“许知远的转型之作”。我想问你,你想往哪儿转?转成什么样子?梁启超晚年进入到学术,你比梁启超启动得还更早一些,现在就要往这个路上走,是吗?
许知远:我是有一个计划的,我有一个后半生的计划。我这么说,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但却是事实发生的。我有一个漫长的计划,希望梁启超三卷只是我九卷本计划的一个开始,一个序言。我想通过几个人物,理解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转变,从嘉庆年间帝国最后的余晖,到鸦片战争、到1901年沉入谷底,然后到寻找中国的革命。我是有这样一个很长的计划。
对我来说,这个计划就像我一个航行的锚一样定在那里。因为我也经常会跟随这个时代飘摇,内心不确定。其实有的时候我能够体会那样一种感觉,在一本书即将快要写到完结部分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陪伴自己二十年的一个老朋友突然就离去了。我喜欢那种画面感。对我来说,可能最后写完那个画面在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我在等待那个时间的到来。
因为我要克服我的厌倦。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厌倦的人,对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必须找不同的事情来抵御我的厌倦。
李菁:那我还是问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你以往的写作风格,包括在《经济观察报》以及写专栏的时候,更多是一种围绕个人观点的表达,都是为文风畅快来服务的。而“梁启超传”这个写作实际上是更回到文本上面,尽量还原梁启超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对你来说,哪一种表达是技术上你觉得更喜欢的?
许知远:尽管我刚才讲话有点故作嚣张,或者自以为是,其实不是的。我是觉得我们存在于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应该能融入其中,我也能为里面添加一块小小的燃料或一个小小的水滴。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共同写一本书。我要加入这所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创造力、你的个人感受都没那么重要,因为你只是大的传统中的一部分。但同时,你的个人创造力又很重要,因为你必须为伟大的传统增加一点点不同的色彩,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对我来说,我确实在写第一卷的时候找到了某种召唤。这个召唤让我安静、镇定。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持续这个召唤。我未来还渴望更多读者,希望很多人通过这个书,或者通过阅读内容能够获得一点点的历史感受。
我们需要建立历史感受。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感受,我们将意识到我们不是那么孤立,我们跟世界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有紧密的连接。这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更充沛的力量。我们也能影响别人,我们不是孤立地生活,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彼此激励,让人感到温暖,又彼此提醒、互相批评的这么一个共同体。所以我的梁启超传,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水滴。
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