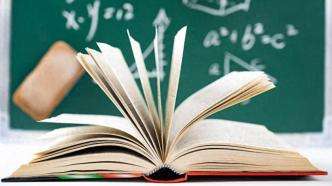日本文艺界对莎士比亚的热爱,或许并不是一个谜。以即将在首都剧场上演的X-LIVE版“蜷川幸雄X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与《裘力斯·凯撒》为例,能看得到日本对西方文明中“理性”的吸收:仿佛一块巨大的海绵,慢慢消化掉有利于自己肌体的养分,并将其变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蜷川幸雄凭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刻诠释,被称为“世界的蜷川”。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大导演黑泽明便被称为“世界电影界的莎士比亚”,这一点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摆渡西东:致敬黑泽明”单元中显示得淋漓尽致。
但黑泽明其实更为复杂,他的身影之后除了莎士比亚,还有另外一个大文豪的存在,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常常在打架。
托尔斯泰为何不喜欢莎士比亚?
列夫·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是出了名的。他写于1903年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是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一个大文豪对一个前辈文豪全盘的否定:“莎士比亚剧作的内容……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蔑视群氓,即劳动阶级,否定任何志在改变现存制度的意图,不仅宗教方面的,也包括人文方面的意图”;“而那些不懂艺术的美学评论家们,在卓有声望的歌德宣扬这种谎言时,就像乌鸦攫食兽尸那样,争相附和,开始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美”……
为什么?
这里面固然有“挑战权威”“较劲”“不服”的意味,但更多与托尔斯泰当时的精神危机有关。他所否定的不仅是莎士比亚,也包括几乎全部自己的作品,除了一本为农民的孩子写的小册子之外。“阿尔扎马斯之夜”之后,托尔斯泰进行了漫长的精神探索。托尔斯泰将信仰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生命”提高到最高地位,并且身体力行;他在充满欲望、奢华的生活中只看到了生命的虚无,而很多所谓经典作家的作品在他看来则充满了谎言、堕落。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满着阴谋、黑暗、恶毒,这样的文艺会把社会带到哪里去呢?
严重的道德焦虑。
然而不幸的是,托尔斯泰的焦虑在20世纪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更糟:两次世界大战及各种局部战争,核武器,信仰的坍塌。并且,连同人道主义一起破产了。
当然,托尔斯泰也难免偏颇,“堕入一边”。20世纪,文学不再居于“中心”,托尔斯泰看到了电影的发明,轻蔑地称之为“呼风唤雨的玩意儿”(德朗科夫1907年拍摄的《托尔斯泰的一天》正是俄国最早的电影之一),但他没能看到电影在20世纪的兴盛。
“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也受益于托翁
黑泽明是20世纪电影的几座高峰之一。有趣的是,他经常被媒体称作“电影界的莎士比亚”。
从很多迹象看来,黑泽明确实与莎士比亚颇有缘分。他改编莎士比亚的电影《蜘蛛巢城》(《麦克白》)、《乱》(《李尔王》)都被认为是优秀的莎剧银幕化杰作。如果考虑到将其日本化的难度,恐怕打分还得再高一些。此外,黑泽明有一些“大片”在格局、主题、人物塑造方面,确实很有些莎士比亚的气魄与气息。例如《七武士》和《影子武士》,艺术风格都非常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其情节的生动、丰富,人物个性和语言的鲜明、朴实,历史生活形象的真实可信,都称得上是莎士比亚在20世纪的回响。
甚至于《七武士》和《影子武士》的主人公,即三船敏郎饰演的菊千代,与仲代达矢饰演的假武田信玄,从语言到形体,都带有莎士比亚人物的“疯癫”特征,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哈姆雷特、福斯塔夫……
但是,黑泽明的艺术造诣,同样也来自托尔斯泰,或许这种影响比莎士比亚给他的更多。和塔尔科夫斯基一样,他将《战争与和平》视为自己的“艺术学院”。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战争与和平》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段,都能作为艺术典范”。托尔斯泰人物心理描写的惊人真实,难道没有对黑泽明产生很大的影响吗?只有对艺术极端缺乏感受力的人才会指责黑泽明人物“性格扁平”。我们还是以《影子武士》为例,开头几分钟,三个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固定机位,却有效传达出极为丰富的信息,三个人的性格、身份、意图都昭然若揭。盗贼在这短短几分钟里,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活动,仅靠微表情、有限的肢体语言,就把他的心理变化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在整部影片中,盗贼是如何一步步认同了主公,并在最后走向了“牺牲”,都有着可信的铺垫。
黑泽明的人道主义“过时”了吗?
如果说,高明的诗学手法有着某些共性,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诗学也有共同点的话,那么在诗学之外,黑泽明的33部影片中,更多却是与莎士比亚的“差异”——世界观的差异。
这种差异,正是在于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的分歧,在于面对“底层”的苦难时产生的那种“羞耻心”。
这种“羞耻心”的根源正是托尔斯泰代表的俄罗斯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但是,黑泽明并非一个单纯的接受者。
黑泽明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有他哥哥的影响。这位哥哥和很多上世纪初的文艺青年一样悲观虚无,将俄国作家、无政府主义者阿尔志跋绥夫(鲁迅翻译过几篇他的小说)奉为偶像,后来自杀。俄罗斯文学中所传达的知识阶层对“底层”的关注,与影响黑泽明青春期的左派思潮不谋而合,此中隐含着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部分人是否有必要在另一部分人的苦难面前有愧疚感,甚至罪感?
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当然可以看出世界观的分野,也涉及到托尔斯泰反复提到的那个问题:“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视野是局限而狭隘的。当然,这种知识分子式的,将泥土与大地“神圣化”,同样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托尔斯泰代表的俄罗斯文化极大拓宽了世界文化的视野,通常“人道主义”与“良知”“道德自我完善”是人们给他贴上的标签。黑泽明的身上也有一些类似的“标签”。当然,黑泽明并不是一个思想家类型的导演,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已经显示出他的力所不能及。
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回答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今天的全人类,那就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卡拉马佐夫已经代表大多数人退还了“上帝的入场券”之后,人道主义(即便是大众理解的那个意思)是否已经过时?
“底层”是黑泽明电影着力描绘的图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远远高于他与莎士比亚重合的部分。他不仅将高尔基的名剧《在底层》搬上银幕,底层更是和他电影中的一个关键词——地狱,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不仅将其中一部影片命名为《天国与地狱》(“地狱”描绘的正是底层图景),更是使用大量的镜头拍摄贫民窟、小酒馆、舞厅、街角等穷人聚居处,其频率之高在同级别导演中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与托尔斯泰有根本性的不同,黑泽明从未将“底层”理想化或美化过,相反,更接近于一种“劣根性批判”。“底层”充满苦难,但自私、愚昧、盲动。《七武士》和《战国英豪》这两部黑泽明最杰出的古装片中,农民阶层都被展现为贪婪、盲目、狭隘、胆小懦弱的人(虽然最后他们的错误都会被宽恕)。他们是很可怜,但是他们更需要被教育和拯救。
那谁来拯救他们呢?就是被他们的苦难唤起“良知”的人群。这个人群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但不限于“知识分子”。他们需要“底层”的救赎,但也“铁肩担道义”。 他们有武士阶层,有警察、公务员,有大学生、教授,也有商人、企业家。除了武士之外,黑泽明的主人公最有意思的职业就是医生:他们救治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理想。《静静的决斗》《泥醉天使》《红胡子》,莫不如此。有时候,这种人道主义看起来是过于理想化的,甚至损害了影片的艺术性。
那么,是大导演自己浑然不觉吗?比如,他看不到强化、煽情的坏处?他难道不知道,只要用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就能轻松将所有的这些愧疚、不安一笔勾销?应该并非如此。他只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而已。
毕竟他是以被自己的丑陋吓出一身油的“蛤蟆”自比的人。这样时时自省的人,又怎会放过自己的“良知”?如果我们今天看《生之欲》依然能为它深深地感动,深感今天如此道德、情感取向的电影是如此稀缺的话,黑泽明又怎会“过时”呢?
日本文艺界对莎士比亚的热爱,或许并不是一个谜。以即将在首都剧场上演的X-LIVE版“蜷川幸雄X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与《裘力斯·凯撒》为例,能看得到日本对西方文明中“理性”的吸收:仿佛一块巨大的海绵,慢慢消化掉有利于自己肌体的养分,并将其变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蜷川幸雄凭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刻诠释,被称为“世界的蜷川”。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大导演黑泽明便被称为“世界电影界的莎士比亚”,这一点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摆渡西东:致敬黑泽明”单元中显示得淋漓尽致。
但黑泽明其实更为复杂,他的身影之后除了莎士比亚,还有另外一个大文豪的存在,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常常在打架。
托尔斯泰为何不喜欢莎士比亚?
列夫·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是出了名的。他写于1903年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是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一个大文豪对一个前辈文豪全盘的否定:“莎士比亚剧作的内容……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蔑视群氓,即劳动阶级,否定任何志在改变现存制度的意图,不仅宗教方面的,也包括人文方面的意图”;“而那些不懂艺术的美学评论家们,在卓有声望的歌德宣扬这种谎言时,就像乌鸦攫食兽尸那样,争相附和,开始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美”……
为什么?
这里面固然有“挑战权威”“较劲”“不服”的意味,但更多与托尔斯泰当时的精神危机有关。他所否定的不仅是莎士比亚,也包括几乎全部自己的作品,除了一本为农民的孩子写的小册子之外。“阿尔扎马斯之夜”之后,托尔斯泰进行了漫长的精神探索。托尔斯泰将信仰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生命”提高到最高地位,并且身体力行;他在充满欲望、奢华的生活中只看到了生命的虚无,而很多所谓经典作家的作品在他看来则充满了谎言、堕落。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满着阴谋、黑暗、恶毒,这样的文艺会把社会带到哪里去呢?
严重的道德焦虑。
然而不幸的是,托尔斯泰的焦虑在20世纪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更糟:两次世界大战及各种局部战争,核武器,信仰的坍塌。并且,连同人道主义一起破产了。
当然,托尔斯泰也难免偏颇,“堕入一边”。20世纪,文学不再居于“中心”,托尔斯泰看到了电影的发明,轻蔑地称之为“呼风唤雨的玩意儿”(德朗科夫1907年拍摄的《托尔斯泰的一天》正是俄国最早的电影之一),但他没能看到电影在20世纪的兴盛。
“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也受益于托翁
黑泽明是20世纪电影的几座高峰之一。有趣的是,他经常被媒体称作“电影界的莎士比亚”。
从很多迹象看来,黑泽明确实与莎士比亚颇有缘分。他改编莎士比亚的电影《蜘蛛巢城》(《麦克白》)、《乱》(《李尔王》)都被认为是优秀的莎剧银幕化杰作。如果考虑到将其日本化的难度,恐怕打分还得再高一些。此外,黑泽明有一些“大片”在格局、主题、人物塑造方面,确实很有些莎士比亚的气魄与气息。例如《七武士》和《影子武士》,艺术风格都非常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其情节的生动、丰富,人物个性和语言的鲜明、朴实,历史生活形象的真实可信,都称得上是莎士比亚在20世纪的回响。
甚至于《七武士》和《影子武士》的主人公,即三船敏郎饰演的菊千代,与仲代达矢饰演的假武田信玄,从语言到形体,都带有莎士比亚人物的“疯癫”特征,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哈姆雷特、福斯塔夫……
但是,黑泽明的艺术造诣,同样也来自托尔斯泰,或许这种影响比莎士比亚给他的更多。和塔尔科夫斯基一样,他将《战争与和平》视为自己的“艺术学院”。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战争与和平》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段,都能作为艺术典范”。托尔斯泰人物心理描写的惊人真实,难道没有对黑泽明产生很大的影响吗?只有对艺术极端缺乏感受力的人才会指责黑泽明人物“性格扁平”。我们还是以《影子武士》为例,开头几分钟,三个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固定机位,却有效传达出极为丰富的信息,三个人的性格、身份、意图都昭然若揭。盗贼在这短短几分钟里,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活动,仅靠微表情、有限的肢体语言,就把他的心理变化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在整部影片中,盗贼是如何一步步认同了主公,并在最后走向了“牺牲”,都有着可信的铺垫。
黑泽明的人道主义“过时”了吗?
如果说,高明的诗学手法有着某些共性,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诗学也有共同点的话,那么在诗学之外,黑泽明的33部影片中,更多却是与莎士比亚的“差异”——世界观的差异。
这种差异,正是在于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的分歧,在于面对“底层”的苦难时产生的那种“羞耻心”。
这种“羞耻心”的根源正是托尔斯泰代表的俄罗斯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但是,黑泽明并非一个单纯的接受者。
黑泽明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有他哥哥的影响。这位哥哥和很多上世纪初的文艺青年一样悲观虚无,将俄国作家、无政府主义者阿尔志跋绥夫(鲁迅翻译过几篇他的小说)奉为偶像,后来自杀。俄罗斯文学中所传达的知识阶层对“底层”的关注,与影响黑泽明青春期的左派思潮不谋而合,此中隐含着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部分人是否有必要在另一部分人的苦难面前有愧疚感,甚至罪感?
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当然可以看出世界观的分野,也涉及到托尔斯泰反复提到的那个问题:“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视野是局限而狭隘的。当然,这种知识分子式的,将泥土与大地“神圣化”,同样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托尔斯泰代表的俄罗斯文化极大拓宽了世界文化的视野,通常“人道主义”与“良知”“道德自我完善”是人们给他贴上的标签。黑泽明的身上也有一些类似的“标签”。当然,黑泽明并不是一个思想家类型的导演,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已经显示出他的力所不能及。
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回答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今天的全人类,那就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卡拉马佐夫已经代表大多数人退还了“上帝的入场券”之后,人道主义(即便是大众理解的那个意思)是否已经过时?
“底层”是黑泽明电影着力描绘的图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远远高于他与莎士比亚重合的部分。他不仅将高尔基的名剧《在底层》搬上银幕,底层更是和他电影中的一个关键词——地狱,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不仅将其中一部影片命名为《天国与地狱》(“地狱”描绘的正是底层图景),更是使用大量的镜头拍摄贫民窟、小酒馆、舞厅、街角等穷人聚居处,其频率之高在同级别导演中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与托尔斯泰有根本性的不同,黑泽明从未将“底层”理想化或美化过,相反,更接近于一种“劣根性批判”。“底层”充满苦难,但自私、愚昧、盲动。《七武士》和《战国英豪》这两部黑泽明最杰出的古装片中,农民阶层都被展现为贪婪、盲目、狭隘、胆小懦弱的人(虽然最后他们的错误都会被宽恕)。他们是很可怜,但是他们更需要被教育和拯救。
那谁来拯救他们呢?就是被他们的苦难唤起“良知”的人群。这个人群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但不限于“知识分子”。他们需要“底层”的救赎,但也“铁肩担道义”。 他们有武士阶层,有警察、公务员,有大学生、教授,也有商人、企业家。除了武士之外,黑泽明的主人公最有意思的职业就是医生:他们救治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理想。《静静的决斗》《泥醉天使》《红胡子》,莫不如此。有时候,这种人道主义看起来是过于理想化的,甚至损害了影片的艺术性。
那么,是大导演自己浑然不觉吗?比如,他看不到强化、煽情的坏处?他难道不知道,只要用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就能轻松将所有的这些愧疚、不安一笔勾销?应该并非如此。他只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而已。
毕竟他是以被自己的丑陋吓出一身油的“蛤蟆”自比的人。这样时时自省的人,又怎会放过自己的“良知”?如果我们今天看《生之欲》依然能为它深深地感动,深感今天如此道德、情感取向的电影是如此稀缺的话,黑泽明又怎会“过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