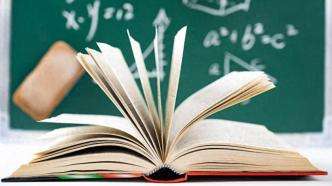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曾子芊
陈黎、张芬龄夫妇均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二人合译作品有《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野兽派太太:达菲诗集》《白石上的黑石:巴列霍诗选》等逾二十种。《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小林一茶俳句300》《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是其在大陆出版的对国外诗人的最新译介。
同时作为译者与诗人,陈黎与妻子张芬龄在台湾成名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拉丁美洲现代诗选》,是宝岛上翻译聂鲁达、巴列霍等拉美诗人的先锋。不过,他们却是在近几年才开启了与大陆出版界的频繁互动,成为了风靡大陆阅读市场的“辛波斯卡译者”和“聂鲁达译者”。对此,陈黎表示,2012年辛波斯卡诗选的出版或许稍稍改变了大陆诗歌出版的情状,不过这与当时新媒体的影响力逐步增大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在有些评论家的眼里,陈黎的首要文化身份还是“诗人”。即使是不经常接触诗歌的读者,或许也会对陈黎的那首全由“兵、乒、乓、丘”四字组成的《战争交响曲》印象深刻。融音乐与绘画入诗,是陈黎的诗艺特色。
自1993年始,陈黎还陆续出版过自己的俳句作品《小宇宙:现代俳句100 首》《小宇宙:现代俳句200首》和简体版的《小宇宙:现代俳句266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中亦可见其对这种以小见大、简洁含蓄诗型的喜爱。他热衷于对古典俳句或其他艺术经典做致敬与变奏。
2018年年初,陈黎开始翻译自己喜爱的俳文名家小林一茶的诗选,前后花费一个半月的时间。之后,他因“忽觉自己对芭蕉几乎一无所知”,遂决定也试做一本《松尾芭蕉俳句300》,花费两个半月的时间。最后,大出他意料之外,自己居然又顺势续做了一本《夕颜:日本短歌400》——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2月20日,花费近三个月的时间,选译了从七世纪《万叶集》天智天皇到二十世纪石川啄木,将近四十位歌人四百多首短歌。
早闻陈黎对待工作高度勤奋,有迅捷地捕捉、挖掘诗歌资源的能力,一直以来,写、译的密度都相当大。与他交谈,也很难不被他身上对生命和艺术的热情所感染,他的天真与活力总让人一时遗忘这位诗人、译者其实已年过花甲。
“我是一个只能‘日理一机’的人。”陈黎说,“我从小性急,反应也许比常人快些,每借渴望和热情为翼,尽量飞快行事”。对于诗的创造和翻译,他表示,自己甘愿“做诗歌的牛马”。
【书乡专访】
书乡: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相比,您好像更喜欢小林一茶?
陈黎:这次着手翻译日本俳句诗人的选集就是缘起自对一茶的喜爱,为什么会特别喜欢一茶的诗?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和“一茶”一样,是以小宇宙窥见大世界。我很少离开台湾花莲,也没有太想离开,就像是“我在我的城复制所有的城,在我的世界城旅行全世界”。只要热情在,那么即使是在太平洋边缘岛屿上的我也可以成为“世界中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好像把宇宙放置在了一碗茶里。所以我说会和一茶投契,而且他写了很多“边缘”的东西,他将神圣的佛教元素与粗鄙的世俗事物并置。他的诗自成一格,不受任何规范束缚,甚至把身体的污垢都写入诗意。一开始,翻译芭蕉的诗则更像是“做作业”和“修学分”。
书乡: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对松尾芭蕉有产生什么新的看法吗?
陈黎:虽然是怀着“做作业”和“修学分”的心理去翻译松尾芭蕉,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却逐渐开始承认,即使我更喜欢小林一茶,松尾芭蕉却是俳句中的“金牌选手”。一提起他,可能大家总会说“俳圣”“禅寂”什么的,这其实只是他的一面。举个例子,芭蕉有一首诗“今宵明月——/只要清澄,/住下就是京城”。芭蕉这首二十三岁之作虽只有短短十七音节,却可充分见其巧妙料理字音、字义之功力。原诗直译大约是“只要清澄/住下就是京城/今日之月”,上五之“清澄”与中七之“住下”日文发音皆为“すめ”(sume),此所谓“挂词”(双关语)。而下五之“今日”,日文发音“きょう”(kyō),与“京(都)”同音。诗中还融入了谚语“住めば都”(住下就是京城;久居则安)。快意地玩这种语言游戏,这是芭蕉一生诗艺最精彩的一部分。歌唱本身和追寻文字的趣味才是所有歌者的第一要义。我在《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这本书里写的导读《八叫芭蕉》的题目也是在向他致敬。此外,芭蕉几度变换了自己的俳风,最终趋向了“轻”的风格,“就像一条浅溪流过沙上”。当苦难那么重的时候,以“轻”去举“重”,人生的况味得以透过艺术去表达。目前,我和张芬龄完成了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的选本翻译,接下来我们还会翻译另一位俳谐名家与谢芜村的作品。
书乡:周作人曾在文章《一茶的诗》里写过,“日本的俳句,原是不可译的诗,一茶的俳句却尤为不可译”。原因是俳句的美在于简洁含蓄,意在言外,翻译容易损毁它的这种特质。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陈黎:弗罗斯特曾有名言说“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诗不可译”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不过,有关俳句,我想把它和我们在日本吃生鱼片的经历联系起来——日本人总是会给你切一片、三片、五片或者七片。俳句也是这样,它是有关奇数、畸零、残缺的美学,与我们有完整 “起承转合”结构的古诗不同,它是悬在空中的“火花”。不过,由于日本与我们同属“汉字文化圈”,一首17音节的俳句或31音节的短歌,“字词”有限,承载不了太多内容,但里头可能包含不少汉字,日本古典俳句、短歌作者同时也受汉诗影响或用中国文学之典。此次进行一茶与芭蕉的中译工作,我和张芬龄都发现,“非汉字文化圈”的译者译日本俳句时,能做到信、达、雅兼顾,再现日文诗原味的机会,还是远不如长期使用汉字的我们。
书乡:虽然周作人说俳句不可译,但他自己也还是忍不住翻译了几首。您觉得自己的翻译和之前的翻译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陈黎: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有关“新旧”的讨论。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时代的语言,或者说时尚的语言,已经与周作人、徐志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了。我其实没有把芭蕉和一茶当成是古人,如果他们生活在当代,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用手机。一茶诗作里那种大胆的风格,也让我深受感染。借用松尾芭蕉说过的“不易”和“流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不易就是“不变”,“流行”则是与时俱进。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可以转换的东西。我认为古往今来的诗人都在进行诗歌的家庭之旅,我只是赓续了这些前辈们的脚步。
书乡:有人曾说您译诗的态度是把作为诗人的身份和特质在翻译里尽可能地隐去了,不强调自己“诗人译诗”的身份,而是尽可能贴合原作本身。
陈黎:我不强调所谓“诗人作为译者”的身份是因为,每个译者——不管是不是“诗人”——在译诗时一定觉得自己在写诗。所以所谓的“创造性的翻译”,或说把译诗当成写诗、当成“再创造”,是极自然之事,无需特别标举。贴合原作本身、符合“信、达、雅”当然是基础。但我在译这些诗时,我也不觉得我笔下出来的中文诗是由芭蕉、一茶所作,我觉得它们像我自己写的中文诗,是自身具足、独一无二的陈黎与张芬龄风格的。
书乡:在这两本俳句的译作里,我们也会读到一些独特的“再创造”。像——“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艸/兵兵兵兵乒乒乓乓丘:梦/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这种比较有个人特色的翻译,会不会担心有读者觉得稍微脱离了原意一些?
陈黎:这首诗的直译约如下——“夏草:/将士们/梦之遗迹……”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大家都知道我传播得最广的一首诗还是《战争交响曲》。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居然看到《战争交响曲》里那些奇“兵”的身影从松尾芭蕉的文本里跳脱出来。我当然也可以选择直译,但我跟很多人差不多,虽不能开风气之先,至少也期盼弄点别人没弄过的东西,希望做出来的东西要有“个性”。但这样翻译的例子还是比较少的,三百首里可能只有三五首,希望能适当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书乡:这次从芭蕉的一千首和一茶的两万首诗里,各选出350首左右的诗来,想知道遴选工作是否有一个标准?
陈黎:一本精选集最优先要纳入的,自然是古往今来大家公认的诗人最高等级的作品,比如说松尾芭蕉的“古池——/青蛙跃入:/水之音”这种名作。这就有赖自己从书上、从网络上,寻看众多关心一茶、芭蕉两位巨匠的日本或世界各地读者、学者喜好,集思广益,形成共识。我过去从英语系读世界文学的经验,我半辈子买的一大堆没看的英文、日文或其他语文的书,也派得上用场,助我、激化我挑选诗作。藏着各种信息、各种可能的网络世界,当然是更重要的新型“武器库”。若非我事先在网络上搜索到一些可充分助我达成任务的日文(或其他语文)相关网页或数据库,我根本不可能投入这工作。再比如说,像小林一茶的“下下又下下,/下又下之下国——/凉快无上啊!”这首俳句,大部分人都不会将它纳入选集中,但在我看来,它是一首奇诗、妙诗,连用了七个“下”字,描写他在偏远信浓国乡下地方,一个人泡汤时的无上凉快。翻译其实是首先一种“目光”,每位译者的“目光”都会不同。希望读者们能用更轻松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差异。
▌曾子芊
陈黎、张芬龄夫妇均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二人合译作品有《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野兽派太太:达菲诗集》《白石上的黑石:巴列霍诗选》等逾二十种。《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小林一茶俳句300》《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是其在大陆出版的对国外诗人的最新译介。
同时作为译者与诗人,陈黎与妻子张芬龄在台湾成名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拉丁美洲现代诗选》,是宝岛上翻译聂鲁达、巴列霍等拉美诗人的先锋。不过,他们却是在近几年才开启了与大陆出版界的频繁互动,成为了风靡大陆阅读市场的“辛波斯卡译者”和“聂鲁达译者”。对此,陈黎表示,2012年辛波斯卡诗选的出版或许稍稍改变了大陆诗歌出版的情状,不过这与当时新媒体的影响力逐步增大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在有些评论家的眼里,陈黎的首要文化身份还是“诗人”。即使是不经常接触诗歌的读者,或许也会对陈黎的那首全由“兵、乒、乓、丘”四字组成的《战争交响曲》印象深刻。融音乐与绘画入诗,是陈黎的诗艺特色。
自1993年始,陈黎还陆续出版过自己的俳句作品《小宇宙:现代俳句100 首》《小宇宙:现代俳句200首》和简体版的《小宇宙:现代俳句266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中亦可见其对这种以小见大、简洁含蓄诗型的喜爱。他热衷于对古典俳句或其他艺术经典做致敬与变奏。
2018年年初,陈黎开始翻译自己喜爱的俳文名家小林一茶的诗选,前后花费一个半月的时间。之后,他因“忽觉自己对芭蕉几乎一无所知”,遂决定也试做一本《松尾芭蕉俳句300》,花费两个半月的时间。最后,大出他意料之外,自己居然又顺势续做了一本《夕颜:日本短歌400》——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2月20日,花费近三个月的时间,选译了从七世纪《万叶集》天智天皇到二十世纪石川啄木,将近四十位歌人四百多首短歌。
早闻陈黎对待工作高度勤奋,有迅捷地捕捉、挖掘诗歌资源的能力,一直以来,写、译的密度都相当大。与他交谈,也很难不被他身上对生命和艺术的热情所感染,他的天真与活力总让人一时遗忘这位诗人、译者其实已年过花甲。
“我是一个只能‘日理一机’的人。”陈黎说,“我从小性急,反应也许比常人快些,每借渴望和热情为翼,尽量飞快行事”。对于诗的创造和翻译,他表示,自己甘愿“做诗歌的牛马”。
【书乡专访】
书乡: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相比,您好像更喜欢小林一茶?
陈黎:这次着手翻译日本俳句诗人的选集就是缘起自对一茶的喜爱,为什么会特别喜欢一茶的诗?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和“一茶”一样,是以小宇宙窥见大世界。我很少离开台湾花莲,也没有太想离开,就像是“我在我的城复制所有的城,在我的世界城旅行全世界”。只要热情在,那么即使是在太平洋边缘岛屿上的我也可以成为“世界中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好像把宇宙放置在了一碗茶里。所以我说会和一茶投契,而且他写了很多“边缘”的东西,他将神圣的佛教元素与粗鄙的世俗事物并置。他的诗自成一格,不受任何规范束缚,甚至把身体的污垢都写入诗意。一开始,翻译芭蕉的诗则更像是“做作业”和“修学分”。
书乡: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对松尾芭蕉有产生什么新的看法吗?
陈黎:虽然是怀着“做作业”和“修学分”的心理去翻译松尾芭蕉,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却逐渐开始承认,即使我更喜欢小林一茶,松尾芭蕉却是俳句中的“金牌选手”。一提起他,可能大家总会说“俳圣”“禅寂”什么的,这其实只是他的一面。举个例子,芭蕉有一首诗“今宵明月——/只要清澄,/住下就是京城”。芭蕉这首二十三岁之作虽只有短短十七音节,却可充分见其巧妙料理字音、字义之功力。原诗直译大约是“只要清澄/住下就是京城/今日之月”,上五之“清澄”与中七之“住下”日文发音皆为“すめ”(sume),此所谓“挂词”(双关语)。而下五之“今日”,日文发音“きょう”(kyō),与“京(都)”同音。诗中还融入了谚语“住めば都”(住下就是京城;久居则安)。快意地玩这种语言游戏,这是芭蕉一生诗艺最精彩的一部分。歌唱本身和追寻文字的趣味才是所有歌者的第一要义。我在《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这本书里写的导读《八叫芭蕉》的题目也是在向他致敬。此外,芭蕉几度变换了自己的俳风,最终趋向了“轻”的风格,“就像一条浅溪流过沙上”。当苦难那么重的时候,以“轻”去举“重”,人生的况味得以透过艺术去表达。目前,我和张芬龄完成了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的选本翻译,接下来我们还会翻译另一位俳谐名家与谢芜村的作品。
书乡:周作人曾在文章《一茶的诗》里写过,“日本的俳句,原是不可译的诗,一茶的俳句却尤为不可译”。原因是俳句的美在于简洁含蓄,意在言外,翻译容易损毁它的这种特质。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陈黎:弗罗斯特曾有名言说“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诗不可译”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不过,有关俳句,我想把它和我们在日本吃生鱼片的经历联系起来——日本人总是会给你切一片、三片、五片或者七片。俳句也是这样,它是有关奇数、畸零、残缺的美学,与我们有完整 “起承转合”结构的古诗不同,它是悬在空中的“火花”。不过,由于日本与我们同属“汉字文化圈”,一首17音节的俳句或31音节的短歌,“字词”有限,承载不了太多内容,但里头可能包含不少汉字,日本古典俳句、短歌作者同时也受汉诗影响或用中国文学之典。此次进行一茶与芭蕉的中译工作,我和张芬龄都发现,“非汉字文化圈”的译者译日本俳句时,能做到信、达、雅兼顾,再现日文诗原味的机会,还是远不如长期使用汉字的我们。
书乡:虽然周作人说俳句不可译,但他自己也还是忍不住翻译了几首。您觉得自己的翻译和之前的翻译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陈黎: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有关“新旧”的讨论。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时代的语言,或者说时尚的语言,已经与周作人、徐志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了。我其实没有把芭蕉和一茶当成是古人,如果他们生活在当代,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用手机。一茶诗作里那种大胆的风格,也让我深受感染。借用松尾芭蕉说过的“不易”和“流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不易就是“不变”,“流行”则是与时俱进。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可以转换的东西。我认为古往今来的诗人都在进行诗歌的家庭之旅,我只是赓续了这些前辈们的脚步。
书乡:有人曾说您译诗的态度是把作为诗人的身份和特质在翻译里尽可能地隐去了,不强调自己“诗人译诗”的身份,而是尽可能贴合原作本身。
陈黎:我不强调所谓“诗人作为译者”的身份是因为,每个译者——不管是不是“诗人”——在译诗时一定觉得自己在写诗。所以所谓的“创造性的翻译”,或说把译诗当成写诗、当成“再创造”,是极自然之事,无需特别标举。贴合原作本身、符合“信、达、雅”当然是基础。但我在译这些诗时,我也不觉得我笔下出来的中文诗是由芭蕉、一茶所作,我觉得它们像我自己写的中文诗,是自身具足、独一无二的陈黎与张芬龄风格的。
书乡:在这两本俳句的译作里,我们也会读到一些独特的“再创造”。像——“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艸/兵兵兵兵乒乒乓乓丘:梦/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这种比较有个人特色的翻译,会不会担心有读者觉得稍微脱离了原意一些?
陈黎:这首诗的直译约如下——“夏草:/将士们/梦之遗迹……”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大家都知道我传播得最广的一首诗还是《战争交响曲》。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居然看到《战争交响曲》里那些奇“兵”的身影从松尾芭蕉的文本里跳脱出来。我当然也可以选择直译,但我跟很多人差不多,虽不能开风气之先,至少也期盼弄点别人没弄过的东西,希望做出来的东西要有“个性”。但这样翻译的例子还是比较少的,三百首里可能只有三五首,希望能适当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书乡:这次从芭蕉的一千首和一茶的两万首诗里,各选出350首左右的诗来,想知道遴选工作是否有一个标准?
陈黎:一本精选集最优先要纳入的,自然是古往今来大家公认的诗人最高等级的作品,比如说松尾芭蕉的“古池——/青蛙跃入:/水之音”这种名作。这就有赖自己从书上、从网络上,寻看众多关心一茶、芭蕉两位巨匠的日本或世界各地读者、学者喜好,集思广益,形成共识。我过去从英语系读世界文学的经验,我半辈子买的一大堆没看的英文、日文或其他语文的书,也派得上用场,助我、激化我挑选诗作。藏着各种信息、各种可能的网络世界,当然是更重要的新型“武器库”。若非我事先在网络上搜索到一些可充分助我达成任务的日文(或其他语文)相关网页或数据库,我根本不可能投入这工作。再比如说,像小林一茶的“下下又下下,/下又下之下国——/凉快无上啊!”这首俳句,大部分人都不会将它纳入选集中,但在我看来,它是一首奇诗、妙诗,连用了七个“下”字,描写他在偏远信浓国乡下地方,一个人泡汤时的无上凉快。翻译其实是首先一种“目光”,每位译者的“目光”都会不同。希望读者们能用更轻松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