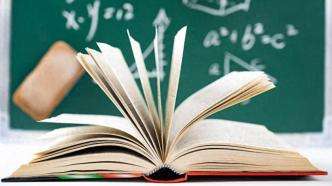答题者:弋舟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8年3月
简历
祖籍江苏无锡,西安生西安长,现居兰州,国内文坛“70后”代表性小说家之一。曾获郁达夫小说奖(第三、四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周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等五部,小说集《刘晓东》《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多部,随笔集《犹在缸中》等两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1/ 你说过“西安,生于斯长于斯”,在你的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安在我心目中是座永远的“大城”。当然,这个“大”里有不少主观的因素,但我想,却也不乏客观的依据。众所周知,它是著名的古都,见证过我们这个文明最为辉煌的时刻。当我离开它,每每忆及,脑子里总是这样一幅想象中的画面——八百里秦川之上,一座大城亘古屹立。在我,这个想象堪称“隐喻”,它在精神源头中,至少给我这样一个自称“没有故乡的人”某种象征性的归属感。童年记忆里最顽固的,当然是这座大城的城墙——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它穿越时空,对应于当代,非常奇妙地约束出一个中国之“城”的形态,在根本上区别于现代城市的概念,但又古今映照,时刻提醒着你基于我们的文明去理解世界,理解生命。其次,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有限的物质匮乏年代,于是你就能理解我童年记忆中关于食物的记忆了,譬如一毛钱一碗的岐山臊子面。由之,城墙和臊子面,构成了我童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记忆。
2/ 从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到近两年凭借《我们的踟蹰》《所有路的尽头》等作品在茅盾文学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及百花文学奖上屡屡获奖,你是怎样走上写小说的文学之路的?
这样的问题我越来越感到难以回答。因为它似乎隐含着一种“规划感”在里面,似乎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是按照一张图纸设计出的结果——你在某一刻迈了右脚,继而走出五十米左转,等了10分钟红灯,然后……好了,最终你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可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感受,我们站在了今天,委实难以细数自己的步履,那个“怎样走上”的问题,在我看来几乎是无可追究的。你能回答自己是怎样走上媒体之路的吗?当然,这其中可能是会有些契机,譬如你学了新闻,譬如恰好在你找工作的时候这家媒体正在招人,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构成本质上的答案。实际上,在我今天的感受中,我们生命之旅那些重要的事实,可能都不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是在“被选择”。那么好了,我是怎样走上写小说的文学之路呢?我只能回答:那是许多非我意志所决定的原因共同作用着的。
3/ 你的故事里有许多社会问题,而且隐含着一种“悲剧性”气质,比方说《如在水底,如在空中》里两个生活中的受挫者,《会游泳的溺水者》里藏于人性暗处的腐败,《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里因为“偷猫”被网络舆情诅咒的无助……你平时很关注社会热点吗,你的创作灵感通常会来源于此吗?
大多数时候鉴于今天资讯的发达,我们其实已经难以“不关注”了,就像出门淋雨,你无法不感知到雨水的存在。对此,我肯定不会“很”关注,我没有这样主观上的故意。这和职业的工作方式有关吧,我的工作并不建立在对于社会热点的必然关注上,灵感有时或者可能来源于此,但远远谈不上“通常”。就我的认识,“通常”那是一个记者的工作方式,但作为一个记者,想必你也未必“很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关注的可能都不是“热点”本身,而是“热点”其后所含纳的人性奥秘,那是更为本质和更为恒久的命题,相较于“热点”的偶然性,我们着力在必然性的探究上。可这种认识如果导致出对于社会性问题的漠视,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小说在我看来,从来就不应该摆脱它的社会属性,所有伟大的灵魂叙事都有其坚固的尘世基础,所谓“从俗世里来,到灵魂里去”。一个事件,当其成为“社会热点”,必然便有了“标本”的价值,身为一个“社会的人”,你理应对其作出自己的观察。至于“悲剧性”,也许是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观察着世界的作家,也许是因为这就是世界的本质,也许,基于一个“悲剧性”的底色,我们才能建立更为可靠的盼望,建立对于人的基本的理解和同情。
4/ 你经常会做怎样的写作计划?
近些年我的写作计划一部分是外力使然,譬如和出版机构达成了某个选题,或者也难免接受一些命题作文。对此以前我可能是比较排斥的,但逐一实践下来,又觉得这种“被动式”的写作也不乏可取之处。它更像是一个“任务”,有约束力,有紧迫感,落实的过程有一种“工作的伦理”。所谓“工作的伦理”,可能就是负责任、兑现专业水准的要求。在这种状况下,我完成了《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这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采访了数十位空巢老人,无论作品面世受到的关注,还是工作过程给予我自身的启迪,都有着出人意料的效果。
再者,另一部分就是自发地计划写作了。2016年,我写出了《丙申故事集》,2017年,我写出了《丁酉故事集》。这两部短篇小说集有着充分的“计划”色彩,我计划着每一年完成一部集子,首先是因为深感当下我们文学出版的混乱——作家们的小说集重复出版,一本和一本之间内容普遍地大量交叉,换一个书名,重新组合一下篇章,于是就又摆在了读者面前。这种现象当然是对读者的不负责。如今严肃文学的读者已然稀缺,基于对生态的维护,我们都得约束自己的轻率。所以我想以这种方式,出版一本就是一本,全部是新作,并且绝不再和其他的作品拼凑集子。有了这样的第一动机,实践过程中许多意识也逐渐显现。譬如,无论“丙申”还是“丁酉”,这种专属中国的纪年方式,都成为富有意味的写作计划,它们折射着我如今的世界观,而“故事集”的命名,又强调着如今我对小说这门艺术的认识,它表达着我的方法论。
5/ 你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遇到瓶颈期如何越过?
写作纯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在我,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是瓶颈,这种状态一直要到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整个过程就是持续地克服,就像连绵不断的障碍横在眼前,你要么匍匐着钻过去,要么纵身跃过去。“过去”的姿态各异,有的很好看,有的就很难看。但好看与否不是关键,“过去”才是关键。于是,在我看来,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权”的过程,在其中体认自己的无能,接受自己的有限,使出浑身解数,连滚带爬地奔赴最后一个句号。
6/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被边缘化(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出现有人会担心文学就要消亡了的论调),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消亡”,有些貌似真的兑现了,有些貌似兑现了的只是“谈论”本身的消亡。而且,现在我认真想一下,似乎自己并未真的见证过什么事物的“消亡”。噢,座机似乎是消亡了,但手机还在,这说明,在本质上,人类沟通的需要并没有消亡;清朝消亡了,但政治还在,人类管理自身的要求须臾不曾递减,消亡了的,仅仅是那些外在的支持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等同于人类的这些本质性需要,与人之属性紧密关联,于是,当我们谈论文学之消亡,只能将人类的消亡作为前提。可它如今的确是“被边缘化”了,但这不重要,此起彼伏,曾经的喇叭裤也被边缘化了,但有一天它可能也还会回来,回不来,也不妨碍依然有人穿得很好看,更不妨碍人类那份持之以恒装扮自己的企图。我们现在不就依然还在谈论着文学吗?
7/ 你看重文学创作之后的商业营销吗?
这同样难以回答。我们看重长寿吗?当然看重,可活成人瑞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只能是一个泡影。文学有其特殊的属性,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它的确是“小众”的乃至是与商业逻辑对立的,但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又是人性的普遍属性。作家也是人,所以他们活在普遍人性与文学特殊性的矛盾中,张口结舌地回答着记者们提出的这些问题。
8/ 从事文学创作对你影响最深的人?
妈妈。她是学中文的,对于文学有着一个知识女性那种过分的信任和依赖。我是她的儿子,当然深受影响。我是在她手提蘸了水的网兜的抽打下开始见识文学的——她让我每天背会一首唐诗。
9/ 前不久,作家红柯突然英年早逝,除了悼念之情,同作为文学陕军的一员,你觉得你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创作野心是什么?
红柯是我熟悉的作家,也有私谊,他的猝然离世,令人震惊悲恸。但我并非“文学陕军”的一员,我生长在西安,唯一能自如说出的方言是西安话,但如今生活在兰州,从形式上,没有人将我认定为“陕军”的一员,并且,内心里我也没有一个置身“某军”的愿望。可是,如果“文学陕军”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性的指涉,而是某种文学精神的昭示,那么,我愿意被囊括在其中。相较于批评家指认的那种“陕军”风格,我的写作与其还是有出入的,但是我想,当我们将“文学”从世相之中单独拎出来后,就不要在“文学”之中又拎出诸多的差异了吧,那样太令人疲惫。我更愿意将“文学”想象成一个恒定而统一的整体,对其,我没有野心,只是越来越深感自己能力的有限。
10/ 写小说带给你最大的收获?
它让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生而为人,我认为这就是自由的重要兑现。
11/ 临近知天命之年,会有哪些感慨,现在是什么状态?
真的是开始羡慕年轻的生命了,甚至羡慕年轻的愚蠢。也真的是懂得了“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依然还会保有愚蠢的盼望——明知道愚蠢,但也愚蠢着不肯放弃,只是开始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愚蠢了,少了一些对峙的紧张,瞧,这个愚蠢的人。“知天命之年”这组词真的太扎眼了,透着股活腻歪了的劲儿。所以“愚蠢”可能就是对于“知天命”的抵抗。
12/ 你对故乡怎么看?
我曾经说过“我没有故乡”。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性的修辞,实际上,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如此。我的父辈从江南来到了西北,而我,从西北到了更西北的地方。故乡于我,没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归属,如果非要给自己一个据点,那么好吧,如同歌里唱到的——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这个“你”,是一切我所忠于的和想要委身的,是一切接纳我并且怜悯我的。
13/ 提起儿子,你正在陪着少年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你对他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还是好歹过了那“桥”吧,即便匍匐跳跃,即便连滚带爬。我们活在秩序里,服从秩序,这没什么可说的。若要过度美化我们个人化的理念或者过度贬斥秩序的非人性,这既不符合我们实际的行为也无异于在尘世获得有限的自由。当然,如果儿子落水,我会在桥下接着他,将他身心无恙地搀扶住,因为我是他爸爸。
14/ 你最欣赏的朋友品质?
朴素诚恳,有正确的三观,当然,要是还有不凡的见地就更好了。
15/ 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尘世安宁。有干净的衣服,有健康的食物,有体力能够适应的劳作,有温柔的陪伴。当然,鲜衣怒马也很好,食不厌精也不错。
16/ 你平时有哪些阅读偏好,对你影响最深的书和作者?
囿于工作性质,我的阅读可能是一种非常“狭窄”的阅读,好比工程师看的是图纸,我看的更多的只能是小说。这种阅读除了专业价值外,我认为作为“阅读”的本意,是不值得肯定的。小说在我看来,是一种阶段性的读物,对其的阅读,一般在三十岁之前完成就可以了,那时候,阅读小说的确有益于人格的养成。但人过三十,虚构性的作品就可以少读乃至不读了。但这并不说明写小说只能在三十岁之前,也许恰恰相反,一个小说家,可能反倒要依靠岁月才能变得更为可靠。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这些小说家理应具备的质地,唯有岁月可以赐予。于是对于我这种特殊的读者,你就可以理解我难以回答某个作家或者某本书对我构成了根本性的影像了,因为那的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就好比我们无法指认是哪一口饭令我们长到了今天。
17/ 日常生活中你是严肃还是会时常开玩笑,你是悲观主义者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开玩笑的吧。许多郑重之情,借由玩笑来表达,是上帝给人的一项宝贵的能力,但显而易见,这里面有轻浮的风险。如果非要做出一个认定,我承认我是倾向于悲观的,但“主义”或许谈不上,至少,我不想将自己的世界观宣称出“主义”那样的强度。那样太容易造成误解。这个世界莫名其妙地会对一个“悲观主义者”报以歧视,但对“乐观主义者”也往往做着不加思考的怀疑,所以类似的提问都如同陷阱。
18/ 新春伊始,未来的两到三年有什么创作规划?
我难以有个长期的规划,哪怕只有两到三年。这个世界如此急促,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而且,我对自己也没有那么笃定的把握。所谓“规划”,往往更像是一个自我祝福,想得都是好事儿,人一想好事儿,往往又多少会有些不切实际。人本质上的盼望其实就那么几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什么的吧,这种基本的盼望,就不是阶段性的“规划”了,它是终其一生的妄念。如果是特指创作的规划,我也只能回答出今年的内容,它们大致是:写一本名叫《戊戌故事集》的小说集,这是对《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的延续,一件事情一旦有了延续性,意义便会自我生长乃至变得重大和繁盛;写一本童书,这是和出版社早有合约的事,必须得完成了,我自己也有通过一本童书的写作来拓宽自己文学想象的愿望;动笔写一部长篇,这也是久拖未果的一个任务;为下一本非虚构的写作做些预热,这本书将关注抑郁症,可以想见,那将是一件浩大的写作考验;参与一些新书的推广活动……天啊,不能再掰着指头数下去了——瞧,这个愚蠢的人。
本版文/木子吉
答题者:弋舟
提问者:木子吉
时间:2018年3月
简历
祖籍江苏无锡,西安生西安长,现居兰州,国内文坛“70后”代表性小说家之一。曾获郁达夫小说奖(第三、四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周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等五部,小说集《刘晓东》《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多部,随笔集《犹在缸中》等两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1/ 你说过“西安,生于斯长于斯”,在你的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安在我心目中是座永远的“大城”。当然,这个“大”里有不少主观的因素,但我想,却也不乏客观的依据。众所周知,它是著名的古都,见证过我们这个文明最为辉煌的时刻。当我离开它,每每忆及,脑子里总是这样一幅想象中的画面——八百里秦川之上,一座大城亘古屹立。在我,这个想象堪称“隐喻”,它在精神源头中,至少给我这样一个自称“没有故乡的人”某种象征性的归属感。童年记忆里最顽固的,当然是这座大城的城墙——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它穿越时空,对应于当代,非常奇妙地约束出一个中国之“城”的形态,在根本上区别于现代城市的概念,但又古今映照,时刻提醒着你基于我们的文明去理解世界,理解生命。其次,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有限的物质匮乏年代,于是你就能理解我童年记忆中关于食物的记忆了,譬如一毛钱一碗的岐山臊子面。由之,城墙和臊子面,构成了我童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记忆。
2/ 从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到近两年凭借《我们的踟蹰》《所有路的尽头》等作品在茅盾文学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及百花文学奖上屡屡获奖,你是怎样走上写小说的文学之路的?
这样的问题我越来越感到难以回答。因为它似乎隐含着一种“规划感”在里面,似乎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是按照一张图纸设计出的结果——你在某一刻迈了右脚,继而走出五十米左转,等了10分钟红灯,然后……好了,最终你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可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感受,我们站在了今天,委实难以细数自己的步履,那个“怎样走上”的问题,在我看来几乎是无可追究的。你能回答自己是怎样走上媒体之路的吗?当然,这其中可能是会有些契机,譬如你学了新闻,譬如恰好在你找工作的时候这家媒体正在招人,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构成本质上的答案。实际上,在我今天的感受中,我们生命之旅那些重要的事实,可能都不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是在“被选择”。那么好了,我是怎样走上写小说的文学之路呢?我只能回答:那是许多非我意志所决定的原因共同作用着的。
3/ 你的故事里有许多社会问题,而且隐含着一种“悲剧性”气质,比方说《如在水底,如在空中》里两个生活中的受挫者,《会游泳的溺水者》里藏于人性暗处的腐败,《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里因为“偷猫”被网络舆情诅咒的无助……你平时很关注社会热点吗,你的创作灵感通常会来源于此吗?
大多数时候鉴于今天资讯的发达,我们其实已经难以“不关注”了,就像出门淋雨,你无法不感知到雨水的存在。对此,我肯定不会“很”关注,我没有这样主观上的故意。这和职业的工作方式有关吧,我的工作并不建立在对于社会热点的必然关注上,灵感有时或者可能来源于此,但远远谈不上“通常”。就我的认识,“通常”那是一个记者的工作方式,但作为一个记者,想必你也未必“很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关注的可能都不是“热点”本身,而是“热点”其后所含纳的人性奥秘,那是更为本质和更为恒久的命题,相较于“热点”的偶然性,我们着力在必然性的探究上。可这种认识如果导致出对于社会性问题的漠视,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小说在我看来,从来就不应该摆脱它的社会属性,所有伟大的灵魂叙事都有其坚固的尘世基础,所谓“从俗世里来,到灵魂里去”。一个事件,当其成为“社会热点”,必然便有了“标本”的价值,身为一个“社会的人”,你理应对其作出自己的观察。至于“悲剧性”,也许是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观察着世界的作家,也许是因为这就是世界的本质,也许,基于一个“悲剧性”的底色,我们才能建立更为可靠的盼望,建立对于人的基本的理解和同情。
4/ 你经常会做怎样的写作计划?
近些年我的写作计划一部分是外力使然,譬如和出版机构达成了某个选题,或者也难免接受一些命题作文。对此以前我可能是比较排斥的,但逐一实践下来,又觉得这种“被动式”的写作也不乏可取之处。它更像是一个“任务”,有约束力,有紧迫感,落实的过程有一种“工作的伦理”。所谓“工作的伦理”,可能就是负责任、兑现专业水准的要求。在这种状况下,我完成了《我在这世上太孤独》这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采访了数十位空巢老人,无论作品面世受到的关注,还是工作过程给予我自身的启迪,都有着出人意料的效果。
再者,另一部分就是自发地计划写作了。2016年,我写出了《丙申故事集》,2017年,我写出了《丁酉故事集》。这两部短篇小说集有着充分的“计划”色彩,我计划着每一年完成一部集子,首先是因为深感当下我们文学出版的混乱——作家们的小说集重复出版,一本和一本之间内容普遍地大量交叉,换一个书名,重新组合一下篇章,于是就又摆在了读者面前。这种现象当然是对读者的不负责。如今严肃文学的读者已然稀缺,基于对生态的维护,我们都得约束自己的轻率。所以我想以这种方式,出版一本就是一本,全部是新作,并且绝不再和其他的作品拼凑集子。有了这样的第一动机,实践过程中许多意识也逐渐显现。譬如,无论“丙申”还是“丁酉”,这种专属中国的纪年方式,都成为富有意味的写作计划,它们折射着我如今的世界观,而“故事集”的命名,又强调着如今我对小说这门艺术的认识,它表达着我的方法论。
5/ 你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遇到瓶颈期如何越过?
写作纯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在我,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是瓶颈,这种状态一直要到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整个过程就是持续地克服,就像连绵不断的障碍横在眼前,你要么匍匐着钻过去,要么纵身跃过去。“过去”的姿态各异,有的很好看,有的就很难看。但好看与否不是关键,“过去”才是关键。于是,在我看来,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权”的过程,在其中体认自己的无能,接受自己的有限,使出浑身解数,连滚带爬地奔赴最后一个句号。
6/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被边缘化(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出现有人会担心文学就要消亡了的论调),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消亡”,有些貌似真的兑现了,有些貌似兑现了的只是“谈论”本身的消亡。而且,现在我认真想一下,似乎自己并未真的见证过什么事物的“消亡”。噢,座机似乎是消亡了,但手机还在,这说明,在本质上,人类沟通的需要并没有消亡;清朝消亡了,但政治还在,人类管理自身的要求须臾不曾递减,消亡了的,仅仅是那些外在的支持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等同于人类的这些本质性需要,与人之属性紧密关联,于是,当我们谈论文学之消亡,只能将人类的消亡作为前提。可它如今的确是“被边缘化”了,但这不重要,此起彼伏,曾经的喇叭裤也被边缘化了,但有一天它可能也还会回来,回不来,也不妨碍依然有人穿得很好看,更不妨碍人类那份持之以恒装扮自己的企图。我们现在不就依然还在谈论着文学吗?
7/ 你看重文学创作之后的商业营销吗?
这同样难以回答。我们看重长寿吗?当然看重,可活成人瑞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只能是一个泡影。文学有其特殊的属性,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它的确是“小众”的乃至是与商业逻辑对立的,但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又是人性的普遍属性。作家也是人,所以他们活在普遍人性与文学特殊性的矛盾中,张口结舌地回答着记者们提出的这些问题。
8/ 从事文学创作对你影响最深的人?
妈妈。她是学中文的,对于文学有着一个知识女性那种过分的信任和依赖。我是她的儿子,当然深受影响。我是在她手提蘸了水的网兜的抽打下开始见识文学的——她让我每天背会一首唐诗。
9/ 前不久,作家红柯突然英年早逝,除了悼念之情,同作为文学陕军的一员,你觉得你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创作野心是什么?
红柯是我熟悉的作家,也有私谊,他的猝然离世,令人震惊悲恸。但我并非“文学陕军”的一员,我生长在西安,唯一能自如说出的方言是西安话,但如今生活在兰州,从形式上,没有人将我认定为“陕军”的一员,并且,内心里我也没有一个置身“某军”的愿望。可是,如果“文学陕军”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性的指涉,而是某种文学精神的昭示,那么,我愿意被囊括在其中。相较于批评家指认的那种“陕军”风格,我的写作与其还是有出入的,但是我想,当我们将“文学”从世相之中单独拎出来后,就不要在“文学”之中又拎出诸多的差异了吧,那样太令人疲惫。我更愿意将“文学”想象成一个恒定而统一的整体,对其,我没有野心,只是越来越深感自己能力的有限。
10/ 写小说带给你最大的收获?
它让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生而为人,我认为这就是自由的重要兑现。
11/ 临近知天命之年,会有哪些感慨,现在是什么状态?
真的是开始羡慕年轻的生命了,甚至羡慕年轻的愚蠢。也真的是懂得了“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依然还会保有愚蠢的盼望——明知道愚蠢,但也愚蠢着不肯放弃,只是开始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愚蠢了,少了一些对峙的紧张,瞧,这个愚蠢的人。“知天命之年”这组词真的太扎眼了,透着股活腻歪了的劲儿。所以“愚蠢”可能就是对于“知天命”的抵抗。
12/ 你对故乡怎么看?
我曾经说过“我没有故乡”。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性的修辞,实际上,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如此。我的父辈从江南来到了西北,而我,从西北到了更西北的地方。故乡于我,没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归属,如果非要给自己一个据点,那么好吧,如同歌里唱到的——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这个“你”,是一切我所忠于的和想要委身的,是一切接纳我并且怜悯我的。
13/ 提起儿子,你正在陪着少年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你对他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还是好歹过了那“桥”吧,即便匍匐跳跃,即便连滚带爬。我们活在秩序里,服从秩序,这没什么可说的。若要过度美化我们个人化的理念或者过度贬斥秩序的非人性,这既不符合我们实际的行为也无异于在尘世获得有限的自由。当然,如果儿子落水,我会在桥下接着他,将他身心无恙地搀扶住,因为我是他爸爸。
14/ 你最欣赏的朋友品质?
朴素诚恳,有正确的三观,当然,要是还有不凡的见地就更好了。
15/ 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尘世安宁。有干净的衣服,有健康的食物,有体力能够适应的劳作,有温柔的陪伴。当然,鲜衣怒马也很好,食不厌精也不错。
16/ 你平时有哪些阅读偏好,对你影响最深的书和作者?
囿于工作性质,我的阅读可能是一种非常“狭窄”的阅读,好比工程师看的是图纸,我看的更多的只能是小说。这种阅读除了专业价值外,我认为作为“阅读”的本意,是不值得肯定的。小说在我看来,是一种阶段性的读物,对其的阅读,一般在三十岁之前完成就可以了,那时候,阅读小说的确有益于人格的养成。但人过三十,虚构性的作品就可以少读乃至不读了。但这并不说明写小说只能在三十岁之前,也许恰恰相反,一个小说家,可能反倒要依靠岁月才能变得更为可靠。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这些小说家理应具备的质地,唯有岁月可以赐予。于是对于我这种特殊的读者,你就可以理解我难以回答某个作家或者某本书对我构成了根本性的影像了,因为那的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就好比我们无法指认是哪一口饭令我们长到了今天。
17/ 日常生活中你是严肃还是会时常开玩笑,你是悲观主义者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开玩笑的吧。许多郑重之情,借由玩笑来表达,是上帝给人的一项宝贵的能力,但显而易见,这里面有轻浮的风险。如果非要做出一个认定,我承认我是倾向于悲观的,但“主义”或许谈不上,至少,我不想将自己的世界观宣称出“主义”那样的强度。那样太容易造成误解。这个世界莫名其妙地会对一个“悲观主义者”报以歧视,但对“乐观主义者”也往往做着不加思考的怀疑,所以类似的提问都如同陷阱。
18/ 新春伊始,未来的两到三年有什么创作规划?
我难以有个长期的规划,哪怕只有两到三年。这个世界如此急促,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而且,我对自己也没有那么笃定的把握。所谓“规划”,往往更像是一个自我祝福,想得都是好事儿,人一想好事儿,往往又多少会有些不切实际。人本质上的盼望其实就那么几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什么的吧,这种基本的盼望,就不是阶段性的“规划”了,它是终其一生的妄念。如果是特指创作的规划,我也只能回答出今年的内容,它们大致是:写一本名叫《戊戌故事集》的小说集,这是对《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的延续,一件事情一旦有了延续性,意义便会自我生长乃至变得重大和繁盛;写一本童书,这是和出版社早有合约的事,必须得完成了,我自己也有通过一本童书的写作来拓宽自己文学想象的愿望;动笔写一部长篇,这也是久拖未果的一个任务;为下一本非虚构的写作做些预热,这本书将关注抑郁症,可以想见,那将是一件浩大的写作考验;参与一些新书的推广活动……天啊,不能再掰着指头数下去了——瞧,这个愚蠢的人。
本版文/木子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