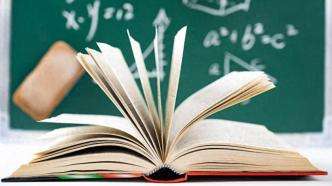不可或缺的细节
《飞行家》这个集子里收有一篇《北方化为乌有》,其题目大抵可以囊括双雪涛迄今的创作范畴。在我们这些同样生于北方、却并非生在更近极北之地的人看来,由一双同辈人的眼睛扫描到的场景,是可以想象的。然而除了想象还是不够的,想象没有温度,这就需要几缕类似汤锅上的热气来复活人间的真实:
在东北的医院,“茶几上摆着几个橘子和一只细口花瓶,花瓶里没有花,暖气太热,一般花都得死,刘一朵买了一盆仙人掌,放在花瓶旁边,像是一个自卑的胖子。”(《跷跷板》)
东北棚户区的夜晚则是这样:“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光明堂》)
这些细节微不足道,可是缺少了它们,就像七味药遗漏了一味,故事便很难站立得住。至少在这部集子里,细节的不可或缺之处在于读者顺利地将压抑和绝望接到手中。大雪落密林,行人踟躇且立,倒闭的工厂像一具风干的巨兽尸身横卧在大地。与俄罗斯文学不同的是,双雪涛很少写到自然风光,但严峻的基调却是一致。因此,作者的每一篇小说都犹如一座冷酷的道德剧场,人们在此戴上面具登台表演以及谢幕。谢幕?——这是最难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早已出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故事并无一个结局。在永恒年岁盘桓头顶的此在,做一个小说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仍然梦想着每一个手势都有其独特的意义,每一抹眼神都有它自足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在时间尽头有一个被他预先讲述的结局在等待着将整个时间序列整合为一个首尾相衔的圆环,而人们居住在这个圆环的中心,被意义和价值的圆满顶礼膜拜。
合乎常理又突破想象
双雪涛是这样的作家吗?我们发现,他偏好志异,但奇闻异事在此不仅仅是寒风雪夜里的佐料。在《跷跷板》中,刘一朵的父亲刘庆革在弥留之际央求主人公“我”,去为他当年杀害、如今托梦于他的工人甘沛元迁坟。“我”在深夜潜入工厂,却发觉门卫正是甘沛元,而“我”依旧在刘庆革指明的位置——跷跷板下——发现了一盘残骸。小说如此结尾:“我盯着骨架看了一会,想了想城市周围的墓地,也许东头的那个棋盘山墓园不错,我给我爷爷扫墓去过,如果能订到南山的位置,居高临下,能够俯瞰半个城。墓碑上该刻什么,一时想不出,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我裹着军大衣蹲在坑边想着,冷风吹动我嘴前的火光,也许我应该去门房的小屋里喝点酒暖暖,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痛快地喝点酒,让筋骨舒缓,然后一切就都清晰起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志异结局。作者无非是让两个“甘沛元”同时在场。设想作者并未写门卫或门卫并不是“甘沛元”,则这篇故事首先就气质而言就寡淡得多了,而意义也并不能充满。一个人深夜去掘墓有什么意思呢?那不过是塞林格的故事。
因此,留给当代作家的悖论便是:一面是日常生活的碎片和无意义,一面是小说谋篇的结构与完满,但后者向生活本身索求它无法给出的意义。着眼于前端,就会像卡佛那样聪明地在一个节点停下,初读者会惊叹,因为他们过于熟悉最高本体尚且在场的世界,而卡佛忠实于生活本身,在后者那里,最高本体早已退出日常生活。如果想要调和生活与文学的冲突,志异是一个出路,但在一些作家那里无疑又显示出背离生活的困境。这一悖论可以综合为一句格言式的命题:如何结构碎片而不丧失碎片的本质?双雪涛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清晰:在《跷跷板》中,是凭借着“我”在坑前沉思的半晌,作者借此溜走。里尔克或许会将这种手段称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第三者的幽灵”,但是我发现,正是有赖于它,小说写作既非浮光掠影的照相,亦非毫无羞耻之心的伪诈。被结构的碎片呈现的是一个无的血盆大口,一个意义的深渊。
诚然,双雪涛写的不止是东北,还有城市(通常是北京)的异乡人,但他们一概背负着位移的深渊。《间距》中的马峰,《北方化为乌有》里的女孩和刘泳,《宽吻》里的离异男子,这些人就像是从密西西比奔赴新英格兰读书的昆丁,仍要接受这样的好奇:“谈谈南方的事吧。那儿是怎么样的。人们在那儿干些什么。他们干吗生活在那儿。他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实情却是,在极北之地,知识分子与作家最早地意识到也最久地忍受着虚无主义。当他们谈论命运,总是令人信服,仿佛他们就是在隐喻那片土地。契诃夫说得很有道理,正因为此,“莫斯科是注定有很多痛苦的一个城市。”因此,如果说大批作家都在挣扎着书写城市的辉煌,那么双雪涛难以被取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无,或者说这个被细节的真实、结构的巧妙所完成的故事,它印证的乃是城市的衰败。这种衰败有时就表现为《白鸟》一篇的谵妄。人物被字母标识(如果不是因为故事,他们甚至不如字母),做着种种既合乎常理又突破想象的事。
写作母题与气质
双雪涛在这部小说集里完整地供出了他的写作母题与气质。故事的结局大多建立在文本层面,但实质上问题没有解决——当然它不是作家的义务。《间距》中“我”和马峰以及另外两位小姑娘齐心协力地撺掇一部剧本,后来因为资金问题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就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小说集最后一篇题为《终点》,不过五百字篇幅,作者似乎在暗示能够拯救“不了了之”的就是终点。但这个终点不再是故事的终点,也不再是意义的终点,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没办法重新开始的终点。
总的来看,无论是寻访记忆中的故乡,还是书写此在的城市,抑或遁入到彻头彻尾的虚构里(《刺杀小说家》),作者都是在描摹一座雾中的城市,其灰蒙而破败,泰半保留着拆迁完毕或亟待拆除的样子。其实小说的功绩也正在于此。当你真正驱车经过书写的对象时,才会发觉它们早已彻底消失,取其代之的是平地而起的几幢新的大厦和CBD。其实何止是城市,在这个世界与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尽其可能地奔逃到几个能量的极点,在那里劳作、休憩、婚配、生育以及终老。如果纵深到这些极点的内部,就会感到禁闭的恐怖,因为布局早已被打破,能量也早已失衡(不过是隐秘地发生着)。如果说在过去人们行走在城市中因为感受到一种平衡祥和的气氛而感到安心并且由此祝福他们心中的现代性,那不过是现代性的起点,如今它滑到这样一个局面,即使在个体的内部,分裂也无所不在,这甚至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因为二者均有赖对方才能互为贬抑地存在)——这种分裂是一方对另一方能量的抽空,是唯一的极点一方能量无限地膨胀到给人们以悲剧的静默感,众多的能量倒空的一方则无限地趋于透明和不存在。最后,这种失衡在个体心中就呈现为失重的感觉:深切的兴废感。悲剧的静默、透明与不存在,以及深切的兴废感,这就是双雪涛在《飞行家》中写到的事情。
不可或缺的细节
《飞行家》这个集子里收有一篇《北方化为乌有》,其题目大抵可以囊括双雪涛迄今的创作范畴。在我们这些同样生于北方、却并非生在更近极北之地的人看来,由一双同辈人的眼睛扫描到的场景,是可以想象的。然而除了想象还是不够的,想象没有温度,这就需要几缕类似汤锅上的热气来复活人间的真实:
在东北的医院,“茶几上摆着几个橘子和一只细口花瓶,花瓶里没有花,暖气太热,一般花都得死,刘一朵买了一盆仙人掌,放在花瓶旁边,像是一个自卑的胖子。”(《跷跷板》)
东北棚户区的夜晚则是这样:“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光明堂》)
这些细节微不足道,可是缺少了它们,就像七味药遗漏了一味,故事便很难站立得住。至少在这部集子里,细节的不可或缺之处在于读者顺利地将压抑和绝望接到手中。大雪落密林,行人踟躇且立,倒闭的工厂像一具风干的巨兽尸身横卧在大地。与俄罗斯文学不同的是,双雪涛很少写到自然风光,但严峻的基调却是一致。因此,作者的每一篇小说都犹如一座冷酷的道德剧场,人们在此戴上面具登台表演以及谢幕。谢幕?——这是最难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早已出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故事并无一个结局。在永恒年岁盘桓头顶的此在,做一个小说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仍然梦想着每一个手势都有其独特的意义,每一抹眼神都有它自足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在时间尽头有一个被他预先讲述的结局在等待着将整个时间序列整合为一个首尾相衔的圆环,而人们居住在这个圆环的中心,被意义和价值的圆满顶礼膜拜。
合乎常理又突破想象
双雪涛是这样的作家吗?我们发现,他偏好志异,但奇闻异事在此不仅仅是寒风雪夜里的佐料。在《跷跷板》中,刘一朵的父亲刘庆革在弥留之际央求主人公“我”,去为他当年杀害、如今托梦于他的工人甘沛元迁坟。“我”在深夜潜入工厂,却发觉门卫正是甘沛元,而“我”依旧在刘庆革指明的位置——跷跷板下——发现了一盘残骸。小说如此结尾:“我盯着骨架看了一会,想了想城市周围的墓地,也许东头的那个棋盘山墓园不错,我给我爷爷扫墓去过,如果能订到南山的位置,居高临下,能够俯瞰半个城。墓碑上该刻什么,一时想不出,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我裹着军大衣蹲在坑边想着,冷风吹动我嘴前的火光,也许我应该去门房的小屋里喝点酒暖暖,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痛快地喝点酒,让筋骨舒缓,然后一切就都清晰起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志异结局。作者无非是让两个“甘沛元”同时在场。设想作者并未写门卫或门卫并不是“甘沛元”,则这篇故事首先就气质而言就寡淡得多了,而意义也并不能充满。一个人深夜去掘墓有什么意思呢?那不过是塞林格的故事。
因此,留给当代作家的悖论便是:一面是日常生活的碎片和无意义,一面是小说谋篇的结构与完满,但后者向生活本身索求它无法给出的意义。着眼于前端,就会像卡佛那样聪明地在一个节点停下,初读者会惊叹,因为他们过于熟悉最高本体尚且在场的世界,而卡佛忠实于生活本身,在后者那里,最高本体早已退出日常生活。如果想要调和生活与文学的冲突,志异是一个出路,但在一些作家那里无疑又显示出背离生活的困境。这一悖论可以综合为一句格言式的命题:如何结构碎片而不丧失碎片的本质?双雪涛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清晰:在《跷跷板》中,是凭借着“我”在坑前沉思的半晌,作者借此溜走。里尔克或许会将这种手段称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第三者的幽灵”,但是我发现,正是有赖于它,小说写作既非浮光掠影的照相,亦非毫无羞耻之心的伪诈。被结构的碎片呈现的是一个无的血盆大口,一个意义的深渊。
诚然,双雪涛写的不止是东北,还有城市(通常是北京)的异乡人,但他们一概背负着位移的深渊。《间距》中的马峰,《北方化为乌有》里的女孩和刘泳,《宽吻》里的离异男子,这些人就像是从密西西比奔赴新英格兰读书的昆丁,仍要接受这样的好奇:“谈谈南方的事吧。那儿是怎么样的。人们在那儿干些什么。他们干吗生活在那儿。他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实情却是,在极北之地,知识分子与作家最早地意识到也最久地忍受着虚无主义。当他们谈论命运,总是令人信服,仿佛他们就是在隐喻那片土地。契诃夫说得很有道理,正因为此,“莫斯科是注定有很多痛苦的一个城市。”因此,如果说大批作家都在挣扎着书写城市的辉煌,那么双雪涛难以被取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无,或者说这个被细节的真实、结构的巧妙所完成的故事,它印证的乃是城市的衰败。这种衰败有时就表现为《白鸟》一篇的谵妄。人物被字母标识(如果不是因为故事,他们甚至不如字母),做着种种既合乎常理又突破想象的事。
写作母题与气质
双雪涛在这部小说集里完整地供出了他的写作母题与气质。故事的结局大多建立在文本层面,但实质上问题没有解决——当然它不是作家的义务。《间距》中“我”和马峰以及另外两位小姑娘齐心协力地撺掇一部剧本,后来因为资金问题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就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小说集最后一篇题为《终点》,不过五百字篇幅,作者似乎在暗示能够拯救“不了了之”的就是终点。但这个终点不再是故事的终点,也不再是意义的终点,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没办法重新开始的终点。
总的来看,无论是寻访记忆中的故乡,还是书写此在的城市,抑或遁入到彻头彻尾的虚构里(《刺杀小说家》),作者都是在描摹一座雾中的城市,其灰蒙而破败,泰半保留着拆迁完毕或亟待拆除的样子。其实小说的功绩也正在于此。当你真正驱车经过书写的对象时,才会发觉它们早已彻底消失,取其代之的是平地而起的几幢新的大厦和CBD。其实何止是城市,在这个世界与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尽其可能地奔逃到几个能量的极点,在那里劳作、休憩、婚配、生育以及终老。如果纵深到这些极点的内部,就会感到禁闭的恐怖,因为布局早已被打破,能量也早已失衡(不过是隐秘地发生着)。如果说在过去人们行走在城市中因为感受到一种平衡祥和的气氛而感到安心并且由此祝福他们心中的现代性,那不过是现代性的起点,如今它滑到这样一个局面,即使在个体的内部,分裂也无所不在,这甚至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因为二者均有赖对方才能互为贬抑地存在)——这种分裂是一方对另一方能量的抽空,是唯一的极点一方能量无限地膨胀到给人们以悲剧的静默感,众多的能量倒空的一方则无限地趋于透明和不存在。最后,这种失衡在个体心中就呈现为失重的感觉:深切的兴废感。悲剧的静默、透明与不存在,以及深切的兴废感,这就是双雪涛在《飞行家》中写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