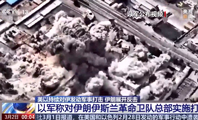“当我们和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注视着我们。你们不是注视着我们。你们注视着我们。你们受到注视。你们暴露在灯光之下。你们不再拥有那些坐在暗处看明处的人的优势。我们不再具有那些站在明处看暗处的人的劣势。”
——彼得·汉德克《骂观众》
那些不再甘于沉默的观众
“观众是戏剧中的必要元素。”如果我们依然承认这个传统观念,并且依然认可“表演者—观众关系”是戏剧活动的核心,那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有一个盲区,长期以来被戏剧评论界普遍忽视,那就是观众席。是的,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台上转移到台下稍微停留片刻,就会看到一个新的潮流正在兴起——
今天的中国观众,或者说中国观众中的一部分先行者,越来越不甘于充当剧场里坐在暗处的沉默群体,他们怀揣着无所畏惧的精神,削尖了脑袋以各种姿势想方设法爬到舞台上,挤进追光下,不管台上演员惊诧的目光,不顾台下众人不满的嘘声,勇敢地参与到表演之中,甚至成为随时可以干扰戏剧活动的生力军。
不久前在京首演的《白兔子,红兔子》,就为这些有觉悟的观众提供了很好的表演空间。这部由伊朗剧作家南星·苏雷曼波尔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互动性的即兴戏剧游戏,观众的参与度必然会影响演出效果。但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中国观众羞于登台,事实上,有些观众甚至还嫌互动不足,主动给自己加戏。
比如有个女观众,多次勇敢地打断演员的表演,发言表态。她先是数次积极申请参与互动,未能得到满足;继而当众向演员提出应改变演出规则,临时增加观众投票的环节;最后干脆直接对演员叫停,现场发表了一大通不知所云的个人意见,当其他观众忍无可忍要求她闭嘴,这位女观众一脸委屈几欲落泪。
同样是在该作品的演出中,为了争抢某一个环节的登台机会,三个观众——两女一男——当众撕扯在了一起。没错,必须用撕扯这个词才能描述战况之惨烈,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其中一名女观众因用力过猛跌坐在表演区里,她显然心有不甘,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竟然当众在地上呆坐半晌。
按照创作者设定的规则,观看过《白兔子,红兔子》的观众终生不得泄露该作品的内容,但本人在此大胆地告诉各位,以上观众的精彩演出很可能已经超出了那位伊朗剧作家的想象之极限,成为中国版演出的独家内容。如果列位看过演出还会惊喜地发现,这些“戏外戏”和该剧主题居然形成了不谋而合的呼应关系。
近年来一些观众自我发挥的即兴戏码,已经成了戏剧爱好者口耳相传的经典段子。比如罗伯特·威尔逊来华演出《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所招致的粗口;或者在浸没式戏剧《不眠之夜》演出现场,有密室逃脱重度玩家从道具柜子里抓了一包中药,试图硬喂给某濒死角色而改写剧情……总之这些观众都活成了“主角”。
这些有着主角梦想的观众,还成功地将他们的表演延伸到了演出之后的演后谈环节。个人认为“演后谈”是一个有些缺陷的叫法,因为它没有约定谁是“谈”的主体,于是几乎每场演后谈都有观众强行争夺话语权,有时不仅是用中文争抢麦克风,每逢遇到外国创作者,总还会有观众冒出来秀一通或蹩脚或不蹩脚的英语。
有一位热衷参与演后谈的女士就曾在京津戏剧圈颇有威望。此人经常在抢得麦克风后,用播音腔当众抒发个人感想,这些感想既空洞又冗长,更无法与他人构成共鸣,听得台上的创作者和台下的其他观众云山雾罩哀鸿遍野。
有时候我们甚至疑心,那些热衷在演后谈上提问的观众是否真的在乎演出本身。比如自杀离世的英国女剧作家萨拉·凯恩的《4.48精神崩溃》不久前在京演出,一位男观众就在演后谈时语气真诚且滔滔不绝地与该剧导演探讨起与本剧并无联系的“安乐死”的话题。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中国当下的戏剧环境,“表演者—观众关系”正在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被改写,旧有的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意识觉醒了的观众前仆后继地将戏剧现场变成释放表达欲望的主场。我们似乎不能仅从文明礼仪和艺术修养的角度来对观众进行简单的批判,因为这已经于事无补了。
谁喂养了瓷器店里的大象
梳理近年来屡屡因观众惹出事端的戏剧演出现场,先锋戏剧演出和小剧场很明显是重灾区。在中国当代戏剧的进程中,先锋戏剧运动和小剧场运动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今天看来颇有些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先锋戏剧运动和小剧场运动的初衷之一,恰恰是希望改写“表演者—观众关系”。
《戏剧在美国的衰落:又如何在法国得以生存》一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便指出,美国先锋戏剧在上世纪70年代从“戏剧”(theater)向“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s)的演进,一方面是在追求对剧场和舞台的解构,另一方面是在追求更大的民主性,并且提出废除等级的文化诉求。
中国的先锋戏剧运动和小剧场运动,同样具有这两方面的追求。比如林兆华的《绝对信号》,率先将戏剧移出了传统的舞台环境;而孟京辉的《等待戈多》,则是“把观众请到舞台上,演员在台下演”。从物理空间的改变,到对既有“表演者—观众关系”的破坏,由此造成的震撼,比戏剧文本的表达来得更为直接。
当戏剧舞台所虚构的艺术的神圣感被消解,观众的心理视角从仰视调整为平视,继而扭转为俯视。在艺术生产的语境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地位差异被抹平乃至颠覆,这也许是先锋戏剧的倡导者们所期待的一种革命结果,但与之相伴相生的副作用则是,艺术家所自拥的文化精英身份必然随之贬值,甚至沦为笑柄。
美国的戏剧先锋始终要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标榜贴近大众,一方面又在警惕大众化,但他们毕竟还有明确的敌人,即趣味平庸的中产阶级文化。但这个基于社会阶级意识所形成的体系划分,在中国找不到相近的对标物,中国的戏剧先锋或文化精英究竟要解放谁及革谁的命,经常成了一团乱麻。
艺术创作领域看似含混的观念,其实是文化思想杂糅的投影。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缺乏必要的历时性序列,而呈现为共时性的独特样貌。上一代艺术家几乎一边拥抱着存在主义,一边咀嚼着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一边排演着荒诞派戏剧,一边任由“读者反应批评”弥散开来。
共时性文化混搭的便利之处,是可以实现艺术的跃进。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的戏剧工作者在保守政治打压之下,先是经历了与大众的报复性割离,以精英主义的高傲抵抗文化当权派,随后才迫于生存压力成为好莱坞等文化帝国的打工者。中国的艺术家则省去了弯路,毫不纠结地便实现了与商业资本的媾和。
中国当代的戏剧工作者对外国戏剧观念的借鉴,从来都是看重形式而轻于思考内涵,他们迫不及待地拷贝外国戏剧的舞美、腔调、形体、游戏性、体验感,却很少想清楚这些舶来品背后的文化指向。而在表达层面上,如果说上一代戏剧工作者曾经懵懂地冒犯过观众,那么如今更多的创作者则是在公然向观众谄媚。
今天中国的戏剧创作环境,似乎难以避开商业运作的逻辑,无论是哪种性质或目的的演出,都可以在市场供需关系中验证合理性。在商业的语境下,消费者(观众)几乎获得了上帝的神权,即使有冒犯“上帝”的企图心,如时下流行的超长演出,或艺术家的特立独行与不逊言辞,最终都被包装成广告营销的slogan。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戏剧创作者变得像百老汇的剧院经理一样在乎观众的好恶,他们会在朋友圈里沾沾自喜地转发评论截屏,会为了媒体差评或豆瓣的吐槽评论而恼羞成怒。当“表演者—观众关系”的一端被加上票房和口碑这两个“硬通货”作砝码之后,谁都明白原本已经失衡的天平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有些尴尬的问题。戏剧创作者一次次抱怨着观众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大象,但他们或许首先应当反思一下,究竟是谁喂养出了这群莽撞的庞然大物。现在,当他们想要将那些爬上舞台的观众驱赶下去的时候,或许也该意识到,他们所要抵抗的并非所谓“乌合之众”,而是塑造了这一群体的机制和环境本身。
必须重塑戏剧艺术的尊严
商业因素(不仅指商业戏剧,也兼指商业化运作的种种手段,及潜在的商业目的)的泛滥,使得戏剧演出的发生现场越来越成为性质暧昧、边界模糊的封闭场域,有时候像圈内人的交际所,专享与自嗨,似社交沙龙,有时候则又像大众娱乐的平行移植版本,共享与群嘲,如联欢晚会,总之与艺术本体没什么关系。
中国当下的娱乐语境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舆论场,在喧哗与躁动背后埋伏着一套严密的循环再生系统。这个场域可以源源不断地持续供应话题,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人们把在其他场域无从释放的表达安全地倾泻于此,又在这里激发新的表达欲望,学习新的话语范式,并尝试借此攻克其他场域的壁垒。
今天,这群训练有素的大众侵入了原本已经泛娱乐化的戏剧场,并且试图将这里改造成他们新的游乐场。想象一下吧:他们对聚光灯的渴望,何尝不是受到电视选秀的启发;他们之间的争抢和互怼,不正如同竞技真人秀的现实翻版;他们在演后谈中滔滔不绝的发言,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肉弹幕”?
更重要的是,戏剧创作者此时所面对的观众,不仅是娱乐时代的消费者,更是所谓的“网生代”群体。网络文化重塑了他们的性格,赋予了他们无视规则、挑衅权威、自我封神的全新人设,同时还赐予了他们操纵话语暴力的技能,消解意义、否定价值、破坏契约、哗众取宠,这是他们手中挥舞的“大杀器”。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群观众在剧场中所制造的种种事端,与其说是有意为之的破坏行为,不如说是久已养成的条件反射。当他们在戏剧演出的现场争先恐后地表演或发言时,这种急于表达的姿态本身,比他们所要试图表达的内容重要得多,更何况这还会为他们赢得安迪·沃霍尔所谓“15分钟明星”的虚幻快感。
我无意将当下的“表演者—观众关系”渲染成剑拔弩张的敌我对立,但艺术家在怀抱着“平权”意识和商业头脑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性,并且这种对抗性贯穿戏剧表演的始终。真正的伟大戏剧作品,从来都是在对抗中完成的,对抗本身正体现了戏剧艺术的尊严。
对艺术尊严的强调,并非是鼓吹以文化精英的立场来藐视大众,不可能附着于附庸风雅与自命不凡的“趣味边缘化”的浮冰之上,而是恰恰应当在创作者自觉的文化意识之中。这样的尊严,理应承载着亚里士多德所教诲的“卡塔西斯”(宣泄、净化、陶冶和升华),这才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健康而积极的互动关系。
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认知:改善“表演者—观众关系”的主动权,从来都掌握在戏剧创作者自己手中,当我们这些戏剧活动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创作者和表演者,也包括评论者和媒体——粗暴地指责观众的时候,或许应当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够真诚地面对观众,甚至我们是否能够真诚地面对戏剧艺术本身。
是时候重新建构这一切了。就像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描述的近二十年来一些美国戏剧工作者所采取的行动那样,我们需要迫切地回归戏剧的本源,向大众敞开胸怀,主动与大众建立平等对话的关系,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捍卫一种面向所有人的具有现代性的戏剧。这毋庸置疑是一种正确的艺术选择。
“你们没有注视。你们注视,并且你们受到注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和你们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在一定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不再称呼你们为‘你们’,而是共同使用另外一个称呼:‘我们’。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团体。”
——彼得·汉德克《骂观众》
“当我们和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注视着我们。你们不是注视着我们。你们注视着我们。你们受到注视。你们暴露在灯光之下。你们不再拥有那些坐在暗处看明处的人的优势。我们不再具有那些站在明处看暗处的人的劣势。”
——彼得·汉德克《骂观众》
那些不再甘于沉默的观众
“观众是戏剧中的必要元素。”如果我们依然承认这个传统观念,并且依然认可“表演者—观众关系”是戏剧活动的核心,那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有一个盲区,长期以来被戏剧评论界普遍忽视,那就是观众席。是的,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台上转移到台下稍微停留片刻,就会看到一个新的潮流正在兴起——
今天的中国观众,或者说中国观众中的一部分先行者,越来越不甘于充当剧场里坐在暗处的沉默群体,他们怀揣着无所畏惧的精神,削尖了脑袋以各种姿势想方设法爬到舞台上,挤进追光下,不管台上演员惊诧的目光,不顾台下众人不满的嘘声,勇敢地参与到表演之中,甚至成为随时可以干扰戏剧活动的生力军。
不久前在京首演的《白兔子,红兔子》,就为这些有觉悟的观众提供了很好的表演空间。这部由伊朗剧作家南星·苏雷曼波尔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互动性的即兴戏剧游戏,观众的参与度必然会影响演出效果。但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中国观众羞于登台,事实上,有些观众甚至还嫌互动不足,主动给自己加戏。
比如有个女观众,多次勇敢地打断演员的表演,发言表态。她先是数次积极申请参与互动,未能得到满足;继而当众向演员提出应改变演出规则,临时增加观众投票的环节;最后干脆直接对演员叫停,现场发表了一大通不知所云的个人意见,当其他观众忍无可忍要求她闭嘴,这位女观众一脸委屈几欲落泪。
同样是在该作品的演出中,为了争抢某一个环节的登台机会,三个观众——两女一男——当众撕扯在了一起。没错,必须用撕扯这个词才能描述战况之惨烈,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其中一名女观众因用力过猛跌坐在表演区里,她显然心有不甘,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竟然当众在地上呆坐半晌。
按照创作者设定的规则,观看过《白兔子,红兔子》的观众终生不得泄露该作品的内容,但本人在此大胆地告诉各位,以上观众的精彩演出很可能已经超出了那位伊朗剧作家的想象之极限,成为中国版演出的独家内容。如果列位看过演出还会惊喜地发现,这些“戏外戏”和该剧主题居然形成了不谋而合的呼应关系。
近年来一些观众自我发挥的即兴戏码,已经成了戏剧爱好者口耳相传的经典段子。比如罗伯特·威尔逊来华演出《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所招致的粗口;或者在浸没式戏剧《不眠之夜》演出现场,有密室逃脱重度玩家从道具柜子里抓了一包中药,试图硬喂给某濒死角色而改写剧情……总之这些观众都活成了“主角”。
这些有着主角梦想的观众,还成功地将他们的表演延伸到了演出之后的演后谈环节。个人认为“演后谈”是一个有些缺陷的叫法,因为它没有约定谁是“谈”的主体,于是几乎每场演后谈都有观众强行争夺话语权,有时不仅是用中文争抢麦克风,每逢遇到外国创作者,总还会有观众冒出来秀一通或蹩脚或不蹩脚的英语。
有一位热衷参与演后谈的女士就曾在京津戏剧圈颇有威望。此人经常在抢得麦克风后,用播音腔当众抒发个人感想,这些感想既空洞又冗长,更无法与他人构成共鸣,听得台上的创作者和台下的其他观众云山雾罩哀鸿遍野。
有时候我们甚至疑心,那些热衷在演后谈上提问的观众是否真的在乎演出本身。比如自杀离世的英国女剧作家萨拉·凯恩的《4.48精神崩溃》不久前在京演出,一位男观众就在演后谈时语气真诚且滔滔不绝地与该剧导演探讨起与本剧并无联系的“安乐死”的话题。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中国当下的戏剧环境,“表演者—观众关系”正在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被改写,旧有的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意识觉醒了的观众前仆后继地将戏剧现场变成释放表达欲望的主场。我们似乎不能仅从文明礼仪和艺术修养的角度来对观众进行简单的批判,因为这已经于事无补了。
谁喂养了瓷器店里的大象
梳理近年来屡屡因观众惹出事端的戏剧演出现场,先锋戏剧演出和小剧场很明显是重灾区。在中国当代戏剧的进程中,先锋戏剧运动和小剧场运动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今天看来颇有些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先锋戏剧运动和小剧场运动的初衷之一,恰恰是希望改写“表演者—观众关系”。
《戏剧在美国的衰落:又如何在法国得以生存》一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便指出,美国先锋戏剧在上世纪70年代从“戏剧”(theater)向“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s)的演进,一方面是在追求对剧场和舞台的解构,另一方面是在追求更大的民主性,并且提出废除等级的文化诉求。
中国的先锋戏剧运动和小剧场运动,同样具有这两方面的追求。比如林兆华的《绝对信号》,率先将戏剧移出了传统的舞台环境;而孟京辉的《等待戈多》,则是“把观众请到舞台上,演员在台下演”。从物理空间的改变,到对既有“表演者—观众关系”的破坏,由此造成的震撼,比戏剧文本的表达来得更为直接。
当戏剧舞台所虚构的艺术的神圣感被消解,观众的心理视角从仰视调整为平视,继而扭转为俯视。在艺术生产的语境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地位差异被抹平乃至颠覆,这也许是先锋戏剧的倡导者们所期待的一种革命结果,但与之相伴相生的副作用则是,艺术家所自拥的文化精英身份必然随之贬值,甚至沦为笑柄。
美国的戏剧先锋始终要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标榜贴近大众,一方面又在警惕大众化,但他们毕竟还有明确的敌人,即趣味平庸的中产阶级文化。但这个基于社会阶级意识所形成的体系划分,在中国找不到相近的对标物,中国的戏剧先锋或文化精英究竟要解放谁及革谁的命,经常成了一团乱麻。
艺术创作领域看似含混的观念,其实是文化思想杂糅的投影。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缺乏必要的历时性序列,而呈现为共时性的独特样貌。上一代艺术家几乎一边拥抱着存在主义,一边咀嚼着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一边排演着荒诞派戏剧,一边任由“读者反应批评”弥散开来。
共时性文化混搭的便利之处,是可以实现艺术的跃进。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的戏剧工作者在保守政治打压之下,先是经历了与大众的报复性割离,以精英主义的高傲抵抗文化当权派,随后才迫于生存压力成为好莱坞等文化帝国的打工者。中国的艺术家则省去了弯路,毫不纠结地便实现了与商业资本的媾和。
中国当代的戏剧工作者对外国戏剧观念的借鉴,从来都是看重形式而轻于思考内涵,他们迫不及待地拷贝外国戏剧的舞美、腔调、形体、游戏性、体验感,却很少想清楚这些舶来品背后的文化指向。而在表达层面上,如果说上一代戏剧工作者曾经懵懂地冒犯过观众,那么如今更多的创作者则是在公然向观众谄媚。
今天中国的戏剧创作环境,似乎难以避开商业运作的逻辑,无论是哪种性质或目的的演出,都可以在市场供需关系中验证合理性。在商业的语境下,消费者(观众)几乎获得了上帝的神权,即使有冒犯“上帝”的企图心,如时下流行的超长演出,或艺术家的特立独行与不逊言辞,最终都被包装成广告营销的slogan。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戏剧创作者变得像百老汇的剧院经理一样在乎观众的好恶,他们会在朋友圈里沾沾自喜地转发评论截屏,会为了媒体差评或豆瓣的吐槽评论而恼羞成怒。当“表演者—观众关系”的一端被加上票房和口碑这两个“硬通货”作砝码之后,谁都明白原本已经失衡的天平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有些尴尬的问题。戏剧创作者一次次抱怨着观众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大象,但他们或许首先应当反思一下,究竟是谁喂养出了这群莽撞的庞然大物。现在,当他们想要将那些爬上舞台的观众驱赶下去的时候,或许也该意识到,他们所要抵抗的并非所谓“乌合之众”,而是塑造了这一群体的机制和环境本身。
必须重塑戏剧艺术的尊严
商业因素(不仅指商业戏剧,也兼指商业化运作的种种手段,及潜在的商业目的)的泛滥,使得戏剧演出的发生现场越来越成为性质暧昧、边界模糊的封闭场域,有时候像圈内人的交际所,专享与自嗨,似社交沙龙,有时候则又像大众娱乐的平行移植版本,共享与群嘲,如联欢晚会,总之与艺术本体没什么关系。
中国当下的娱乐语境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舆论场,在喧哗与躁动背后埋伏着一套严密的循环再生系统。这个场域可以源源不断地持续供应话题,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人们把在其他场域无从释放的表达安全地倾泻于此,又在这里激发新的表达欲望,学习新的话语范式,并尝试借此攻克其他场域的壁垒。
今天,这群训练有素的大众侵入了原本已经泛娱乐化的戏剧场,并且试图将这里改造成他们新的游乐场。想象一下吧:他们对聚光灯的渴望,何尝不是受到电视选秀的启发;他们之间的争抢和互怼,不正如同竞技真人秀的现实翻版;他们在演后谈中滔滔不绝的发言,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肉弹幕”?
更重要的是,戏剧创作者此时所面对的观众,不仅是娱乐时代的消费者,更是所谓的“网生代”群体。网络文化重塑了他们的性格,赋予了他们无视规则、挑衅权威、自我封神的全新人设,同时还赐予了他们操纵话语暴力的技能,消解意义、否定价值、破坏契约、哗众取宠,这是他们手中挥舞的“大杀器”。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群观众在剧场中所制造的种种事端,与其说是有意为之的破坏行为,不如说是久已养成的条件反射。当他们在戏剧演出的现场争先恐后地表演或发言时,这种急于表达的姿态本身,比他们所要试图表达的内容重要得多,更何况这还会为他们赢得安迪·沃霍尔所谓“15分钟明星”的虚幻快感。
我无意将当下的“表演者—观众关系”渲染成剑拔弩张的敌我对立,但艺术家在怀抱着“平权”意识和商业头脑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性,并且这种对抗性贯穿戏剧表演的始终。真正的伟大戏剧作品,从来都是在对抗中完成的,对抗本身正体现了戏剧艺术的尊严。
对艺术尊严的强调,并非是鼓吹以文化精英的立场来藐视大众,不可能附着于附庸风雅与自命不凡的“趣味边缘化”的浮冰之上,而是恰恰应当在创作者自觉的文化意识之中。这样的尊严,理应承载着亚里士多德所教诲的“卡塔西斯”(宣泄、净化、陶冶和升华),这才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健康而积极的互动关系。
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认知:改善“表演者—观众关系”的主动权,从来都掌握在戏剧创作者自己手中,当我们这些戏剧活动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创作者和表演者,也包括评论者和媒体——粗暴地指责观众的时候,或许应当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够真诚地面对观众,甚至我们是否能够真诚地面对戏剧艺术本身。
是时候重新建构这一切了。就像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描述的近二十年来一些美国戏剧工作者所采取的行动那样,我们需要迫切地回归戏剧的本源,向大众敞开胸怀,主动与大众建立平等对话的关系,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捍卫一种面向所有人的具有现代性的戏剧。这毋庸置疑是一种正确的艺术选择。
“你们没有注视。你们注视,并且你们受到注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和你们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在一定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不再称呼你们为‘你们’,而是共同使用另外一个称呼:‘我们’。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团体。”
——彼得·汉德克《骂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