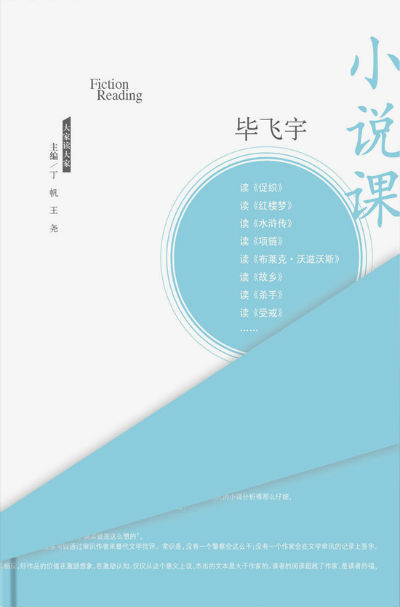2月24日下午,作家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做客东四九条共享际,推出作家新书《小说课》。(千龙网发)
千龙网讯 2月24日下午,作家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做客东四九条共享际,推出作家新书《小说课》,探讨小说与阅读。
《小说课》辑录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讲稿曾发表于《钟山》杂志。
见面会上,毕飞宇说:“我读小说的心态像一个喜欢玩手串的人,把手串拿在手上玩两年、三年是一个道理,所以许许多多我非常喜欢的小说,被我谈了不知道多少遍,所以相对来讲,因为是谈的心、玩的心,就没那么科学、没那么镇定,所以表达出来的时候就轻松一点。”
“(毕飞宇谈小说)每天的讲稿出来之后都产生非常大的反响。很多人就会来找这个讲稿,我们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讲稿结集影响读者,让大家分享毕老师很独特的阅读感受。”《小说课》责任编辑赵萍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说:“毕飞宇的《小说课》为我们深入了解小说提供了很好的一种样本,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品,比如他这本书中谈到的《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或是他所涉猎的外国名家经典,比如说哈代、海鸣威、奈保尔等人的作品。毕飞宇的讲解轻松、谐趣、观点独到,他从自身的作家经验出发,另辟蹊径,让读者见识到小说的曼妙身姿,这就再次回到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初衷,请作家和学者们灵动的叙述他们各自阅读文本时的感受,让阅读不再枯燥,让阅读充满逸趣。”
现场Q&A
提问:您觉得您的阅读对小说的创作上有帮助吗?
毕飞宇:理论上不太可能,因为写作不是盲目的,一定有指向,无非两个方面,理性诉求和美学标准。所谓写作,不就是向自己心中的那个美学标准靠近的一个过程吗?美学标准是什么?必须是这个人他自己去建立。写是建立不了的,只能是通过读,慢慢在你的心目当中建立起一个好小说的标准。如果一个读者脑子里面有一百部功夫小说的体量,他建立起来的肯定是功夫小说的标准。他如果脑子里面是一大堆的琼瑶,他最后也会成为第二个琼瑶。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之后,获益的一定不是文字上的,而是整个人。为什么古代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因为他通过读书,通过读诗,他建立起来一美学标准,用这个标准去写信、去写诗,去和人相处,去做人,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提问:您对于小说的核心,也就是故事,包括故事的规划、创建、设置等等这些方面怎么看?
毕飞宇:说起故事,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写小说有没有故事大纲,尤其是长篇,有没有故事脉络?我没有。跟50后之前的作家比较起来的话,60后的作家带有去故事化的倾向,导致60后作家的共同特征就是故事不那么好看,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缺陷,我们不是以故事见长的作家。有一个大纲,按步就班完成计划,我会非常辛苦,没有快感,所以我愿意永远没有大纲。我每天把电脑打开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一遍,然后今天我往哪走,临时做决定,当然这个决定有可能走差了,走差以后没问题,我写了一个星期写差了,我把这个星期写的东西全删了重新写,当我发现找对的时候,我的内心会充满喜悦的,那种喜悦比吃饭、比在足球场上打进一个球强烈得多。我希望每天都能有所发现,这样我会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每天都能从写作里面得到乐趣,我把这个乐趣看作对我自己的一个奖赏。
提问:您怎么评价娄烨电影版的《推拿》。
毕飞宇:特别好。在我看来,娄烨拍《推拿》是他的一个巅峰状态。我特别喜欢他在拍《推拿》的时候找到的一个调子,这个调子从头到尾都贯穿始终,一个只有在生命力非常强大的情况底下,一个艺术家才会有如此举重若轻的掌控能力。我记得我对娄烨说过一句话,这个电影没有一个地方跟我的小说是像的,可是你看完电影以后却发现,小说里面的东西都在里头。尤其是处理人物关系,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导演在处理众多人物关系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我举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通常一个长篇都得有主人公,可是《推拿》这个作品跟其他任何作品都不一样,它是一群太弱势、太弱势的一个群体,我坚决不愿意让这个作品当中出现有所谓的主人公,然后其他人成为这个人的一个配角,这是人道主义的技术化。娄烨说老毕你知道吗,所有人都以为黄轩的戏是最多的,以为黄轩是男一号,我告诉你老毕,我在剪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专门算着剪的,每个人的时间几乎一样。我特别高兴,虽然不算一个大事情,是很小的事情,但对于我们这些艺术家来讲,对于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来讲,它是重要的,至少我们体现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人真的是平等的。
提问: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会不会出版以后回头再看,或者您自己的这种反思,在作品发表以后,再以什么样具体操作的形式去实现?
毕飞宇:一般来讲,作品寄出去之后我不看,因为我在作品写好之后要放很长时间才会把它发表出去,我在修改小说的过程当中,虽然我没有调查过,也没有打听过,我认为在中国作家里面,作品写完之后修改再冷却,在这个供需方面,我可能是中国作家里面最舍得耗时间的一个人。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导致到最后我看这个小说会看到恶心,等我真的横下一条心,把这个小说打给赵萍吧,打出去之后我一个字都不会再看,我一门心思再看别的作品,放下就彻底放下,通常我不看自己的作品,也很少去反思上一个作品的得失,因为过去的东西你一定得让它过去。已经发表的,已经面向社会的作品,无论我后面有什么异议,我永远不会动它,我永远让它保持我那个水准时候的原貌,这是我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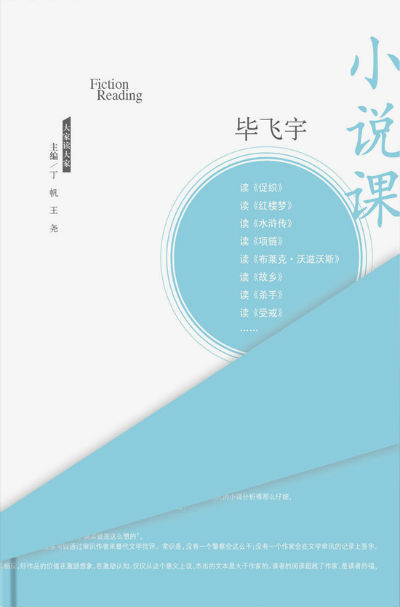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毕飞宇,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现为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玉米》,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英文版)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精彩书摘
施耐庵的小说很实,他依仗的是逻辑。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小说比逻辑要广阔得多,小说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的,甚至于,可以是反逻辑的。曹雪芹就是这样,在许多地方,《红楼梦》就非常反逻辑。因为反逻辑,曹雪芹的描写往往很虚。有时候,你从具体的描写对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达的真实内容,你要从“飞白”——也就是没有写到的地方去看。所谓“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还是来谈“走”路,看看曹雪芹老先生在描写“走”的时候是如何反逻辑的。
——《“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我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就在前几天,一位朋友看了我在《钟山》上的专栏,特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
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补充说,——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所以,关于《项链》,我依然有话要说。我所说的这些莫泊桑也许想过,也许从来就没有想过。
——《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

2月24日下午,作家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做客东四九条共享际,推出作家新书《小说课》。(千龙网发)
千龙网讯 2月24日下午,作家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做客东四九条共享际,推出作家新书《小说课》,探讨小说与阅读。
《小说课》辑录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讲稿曾发表于《钟山》杂志。
见面会上,毕飞宇说:“我读小说的心态像一个喜欢玩手串的人,把手串拿在手上玩两年、三年是一个道理,所以许许多多我非常喜欢的小说,被我谈了不知道多少遍,所以相对来讲,因为是谈的心、玩的心,就没那么科学、没那么镇定,所以表达出来的时候就轻松一点。”
“(毕飞宇谈小说)每天的讲稿出来之后都产生非常大的反响。很多人就会来找这个讲稿,我们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讲稿结集影响读者,让大家分享毕老师很独特的阅读感受。”《小说课》责任编辑赵萍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说:“毕飞宇的《小说课》为我们深入了解小说提供了很好的一种样本,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品,比如他这本书中谈到的《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或是他所涉猎的外国名家经典,比如说哈代、海鸣威、奈保尔等人的作品。毕飞宇的讲解轻松、谐趣、观点独到,他从自身的作家经验出发,另辟蹊径,让读者见识到小说的曼妙身姿,这就再次回到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初衷,请作家和学者们灵动的叙述他们各自阅读文本时的感受,让阅读不再枯燥,让阅读充满逸趣。”
现场Q&A
提问:您觉得您的阅读对小说的创作上有帮助吗?
毕飞宇:理论上不太可能,因为写作不是盲目的,一定有指向,无非两个方面,理性诉求和美学标准。所谓写作,不就是向自己心中的那个美学标准靠近的一个过程吗?美学标准是什么?必须是这个人他自己去建立。写是建立不了的,只能是通过读,慢慢在你的心目当中建立起一个好小说的标准。如果一个读者脑子里面有一百部功夫小说的体量,他建立起来的肯定是功夫小说的标准。他如果脑子里面是一大堆的琼瑶,他最后也会成为第二个琼瑶。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之后,获益的一定不是文字上的,而是整个人。为什么古代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因为他通过读书,通过读诗,他建立起来一美学标准,用这个标准去写信、去写诗,去和人相处,去做人,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提问:您对于小说的核心,也就是故事,包括故事的规划、创建、设置等等这些方面怎么看?
毕飞宇:说起故事,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写小说有没有故事大纲,尤其是长篇,有没有故事脉络?我没有。跟50后之前的作家比较起来的话,60后的作家带有去故事化的倾向,导致60后作家的共同特征就是故事不那么好看,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缺陷,我们不是以故事见长的作家。有一个大纲,按步就班完成计划,我会非常辛苦,没有快感,所以我愿意永远没有大纲。我每天把电脑打开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一遍,然后今天我往哪走,临时做决定,当然这个决定有可能走差了,走差以后没问题,我写了一个星期写差了,我把这个星期写的东西全删了重新写,当我发现找对的时候,我的内心会充满喜悦的,那种喜悦比吃饭、比在足球场上打进一个球强烈得多。我希望每天都能有所发现,这样我会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每天都能从写作里面得到乐趣,我把这个乐趣看作对我自己的一个奖赏。
提问:您怎么评价娄烨电影版的《推拿》。
毕飞宇:特别好。在我看来,娄烨拍《推拿》是他的一个巅峰状态。我特别喜欢他在拍《推拿》的时候找到的一个调子,这个调子从头到尾都贯穿始终,一个只有在生命力非常强大的情况底下,一个艺术家才会有如此举重若轻的掌控能力。我记得我对娄烨说过一句话,这个电影没有一个地方跟我的小说是像的,可是你看完电影以后却发现,小说里面的东西都在里头。尤其是处理人物关系,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导演在处理众多人物关系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我举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通常一个长篇都得有主人公,可是《推拿》这个作品跟其他任何作品都不一样,它是一群太弱势、太弱势的一个群体,我坚决不愿意让这个作品当中出现有所谓的主人公,然后其他人成为这个人的一个配角,这是人道主义的技术化。娄烨说老毕你知道吗,所有人都以为黄轩的戏是最多的,以为黄轩是男一号,我告诉你老毕,我在剪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专门算着剪的,每个人的时间几乎一样。我特别高兴,虽然不算一个大事情,是很小的事情,但对于我们这些艺术家来讲,对于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来讲,它是重要的,至少我们体现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人真的是平等的。
提问: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会不会出版以后回头再看,或者您自己的这种反思,在作品发表以后,再以什么样具体操作的形式去实现?
毕飞宇:一般来讲,作品寄出去之后我不看,因为我在作品写好之后要放很长时间才会把它发表出去,我在修改小说的过程当中,虽然我没有调查过,也没有打听过,我认为在中国作家里面,作品写完之后修改再冷却,在这个供需方面,我可能是中国作家里面最舍得耗时间的一个人。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导致到最后我看这个小说会看到恶心,等我真的横下一条心,把这个小说打给赵萍吧,打出去之后我一个字都不会再看,我一门心思再看别的作品,放下就彻底放下,通常我不看自己的作品,也很少去反思上一个作品的得失,因为过去的东西你一定得让它过去。已经发表的,已经面向社会的作品,无论我后面有什么异议,我永远不会动它,我永远让它保持我那个水准时候的原貌,这是我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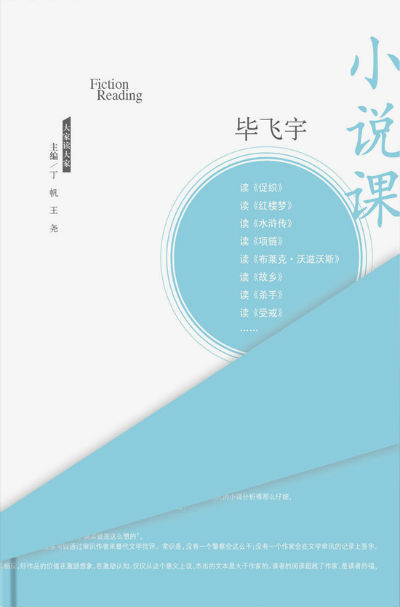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毕飞宇,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现为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玉米》,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英文版)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精彩书摘
施耐庵的小说很实,他依仗的是逻辑。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小说比逻辑要广阔得多,小说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的,甚至于,可以是反逻辑的。曹雪芹就是这样,在许多地方,《红楼梦》就非常反逻辑。因为反逻辑,曹雪芹的描写往往很虚。有时候,你从具体的描写对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达的真实内容,你要从“飞白”——也就是没有写到的地方去看。所谓“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还是来谈“走”路,看看曹雪芹老先生在描写“走”的时候是如何反逻辑的。
——《“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我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就在前几天,一位朋友看了我在《钟山》上的专栏,特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
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补充说,——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所以,关于《项链》,我依然有话要说。我所说的这些莫泊桑也许想过,也许从来就没有想过。
——《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