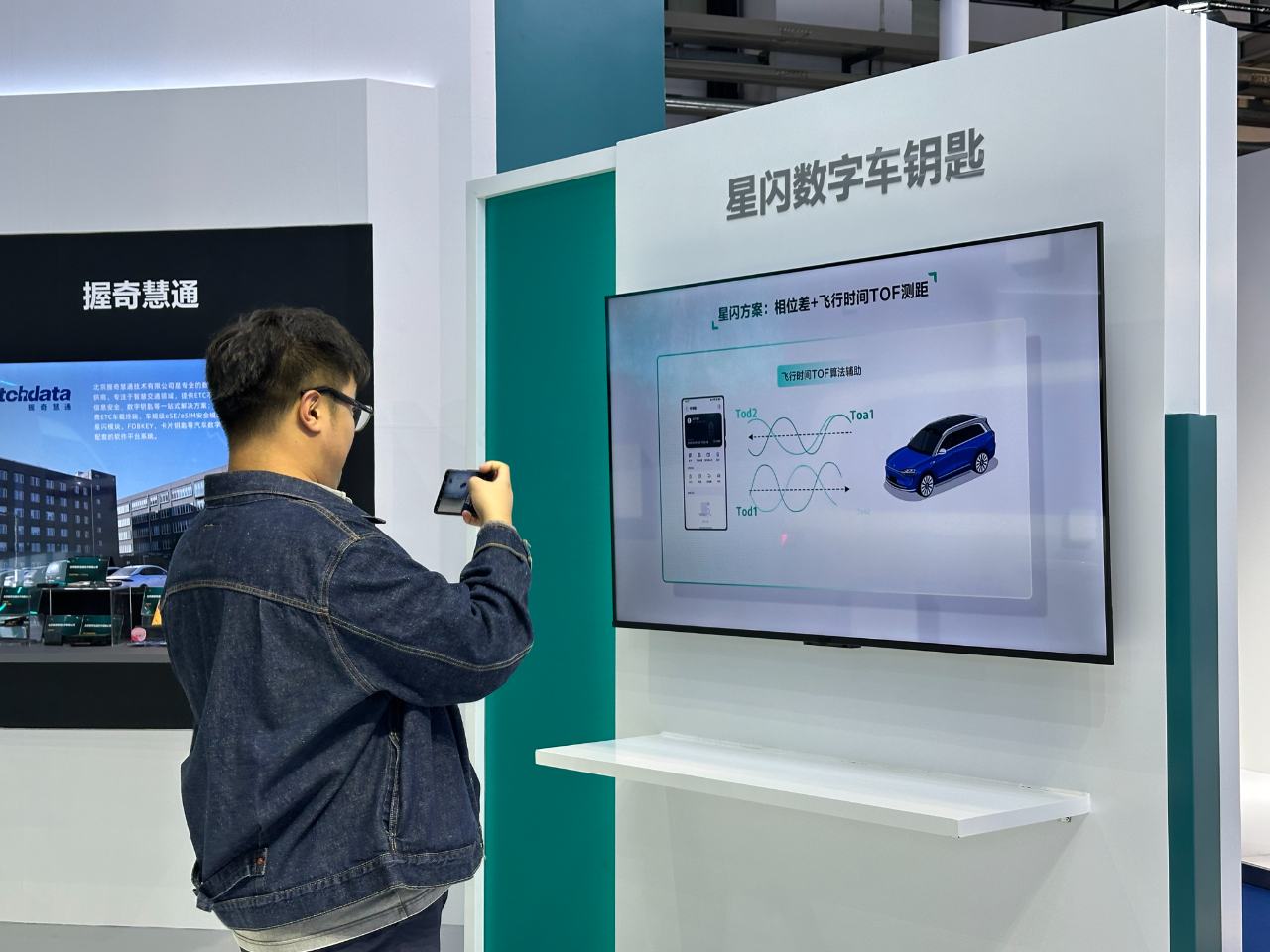冰心写北京的春天时,情绪则要激动得多。如《一日的春光》:“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吞咽”一词流露出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对北国之春的珍惜、兴奋之情。《一日的春光》中的笔调是活泼泼的、扑棱棱的:“今年北平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阴,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的远引了。”
北京的春天是短的,然而作家们凭借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依然可以轻易捕捉对“北平之春”的“存在感”。
周作人写道:“北平到底还是有他的春天,不过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叫人有时来不及尝他的味儿,有时尝了觉得稍枯燥了,虽然名字还叫作春天,但是实在就把他当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头。”北京的春不仅短,而且还时时受到“冬”的干扰:“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

冰心写北京的春天时,情绪则要激动得多。如《一日的春光》:“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吞咽”一词流露出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对北国之春的珍惜、兴奋之情。《一日的春光》中的笔调是活泼泼的、扑棱棱的:“今年北平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阴,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的远引了。”
北京的春天是短的,然而作家们凭借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依然可以轻易捕捉对“北平之春”的“存在感”。
周作人写道:“北平到底还是有他的春天,不过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叫人有时来不及尝他的味儿,有时尝了觉得稍枯燥了,虽然名字还叫作春天,但是实在就把他当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头。”北京的春不仅短,而且还时时受到“冬”的干扰:“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