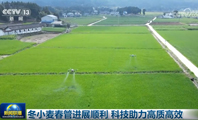我爸一到腊月脚下,就会变得格外吃香。村人们看见他,都一副巴结的模样。有烟的,忙着掏烟,没烟的,则一脸堆笑地拉他到屋里喝口浓茶。
我爸很受用。他一直是个好面子的人,受人尊重,那是无上荣光的事。他不客气地,这家的烟也抽了,那家的茶也喝了,然后,背着双手,轻声哼着《拔根芦柴花》的小调,踱着方步回家来。我们就知道,该忙乎开了。
忙什么呢?忙着收拾他的作场啊。堂屋里杂七杂八的东西,统统被我们塞到别处去了。地清扫干净了,一粒多余的尘也没有。桌子抹干净了,在堂屋中央摆开来。剪刀、小刀备齐。一年里也用不了几次的毛笔,被请了出来,清水泡着。搁在柜脚底下的墨汁瓶,被小心翼翼捧出来,上面落满蜘蛛灰。我们用抹布擦拭干净,拿瓶盖子或是破碗,倒了墨汁出来。
一切准备就绪。我爸方满意地走过来,在桌边站定,他深吸一口气,运笔在手,拿废弃的牛皮纸,先试着写几个字。写完,他对着那几个字,左端详,右端详,微笑。我们在一边看着,觉得我爸很了不得,能文能写。现在想着,有些失笑,我爸也仅仅读了个初中,他也未曾练过书法,写的字也谈不上什么笔锋。可是,在当时不识字或识不了几个字的村人们眼里,那是秀才。
村人们络绎不绝上门来,腋下都夹着一张红纸。他们或站着,或蹲着,说着些家长里短,把我家的小屋挤得满满当当热气腾腾。我们兄妹几个,按我爸的吩咐,伏在地上帮着裁纸。大门上的,二门上的,房门上的,院门上的,厨房门上的,粮囤子上的。余下的边角料儿,也不废掉,我爸会大笔一挥,在上面写个“六畜兴旺”,给贴到羊圈猪圈鸡窝上去。
那时不甚明了,怎么是六畜呢?村子里日常所见的,明明只有鸡鸭猪羊,有牛的人家也甚少,这加起来也才五畜。也是到后来,我念书了,懂得查阅资料了,方才把心中的疑团给解了。六畜,原是指马、牛、羊、鸡、狗、猪。它们是被我们远古祖先最先驯化的牲畜,渐渐演变成了家畜。《三字经·训诂》中,对“六畜”有着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宾客。
我的村人们当然不懂这个。他们也不管这个,只道那是牲畜兴旺,吉利吉祥。他们拿着那张“六畜兴旺”,高兴得不得了,眼睛眯着,笑嘻嘻地盯着看,似乎上面正跑着大肥猪和大肥羊。
一个村子的对联,很让我爸费脑子,他不想太重复,每家每户写的都不一样。他有时会停下手中笔,若有所思地问蹲着的一个人,你家大门上你想写什么呢?那人嘿嘿笑两声,回他,我哪晓得写什么啊,你写什么都好。我爸就写,金鸡报晓,红梅报春。又或是,春满人间福满园之类的。
有一年,我爸给我家大门上写的是“吃大肥肉,穿花洋布”。直白明了,清爽好记。村人们看到,都说这个好,都要求写这个。结果,那一年,全村人家,几乎家家门上都贴着这副对联。正月里在村子里走着,一个村子除了喜气洋洋外,又另添着一份跃动,满满的幸福的气流,在四处蹿着,似乎人人都穿上了新衣裳,人人都有大肥肉吃。真富裕!
我爸一到腊月脚下,就会变得格外吃香。村人们看见他,都一副巴结的模样。有烟的,忙着掏烟,没烟的,则一脸堆笑地拉他到屋里喝口浓茶。
我爸很受用。他一直是个好面子的人,受人尊重,那是无上荣光的事。他不客气地,这家的烟也抽了,那家的茶也喝了,然后,背着双手,轻声哼着《拔根芦柴花》的小调,踱着方步回家来。我们就知道,该忙乎开了。
忙什么呢?忙着收拾他的作场啊。堂屋里杂七杂八的东西,统统被我们塞到别处去了。地清扫干净了,一粒多余的尘也没有。桌子抹干净了,在堂屋中央摆开来。剪刀、小刀备齐。一年里也用不了几次的毛笔,被请了出来,清水泡着。搁在柜脚底下的墨汁瓶,被小心翼翼捧出来,上面落满蜘蛛灰。我们用抹布擦拭干净,拿瓶盖子或是破碗,倒了墨汁出来。
一切准备就绪。我爸方满意地走过来,在桌边站定,他深吸一口气,运笔在手,拿废弃的牛皮纸,先试着写几个字。写完,他对着那几个字,左端详,右端详,微笑。我们在一边看着,觉得我爸很了不得,能文能写。现在想着,有些失笑,我爸也仅仅读了个初中,他也未曾练过书法,写的字也谈不上什么笔锋。可是,在当时不识字或识不了几个字的村人们眼里,那是秀才。
村人们络绎不绝上门来,腋下都夹着一张红纸。他们或站着,或蹲着,说着些家长里短,把我家的小屋挤得满满当当热气腾腾。我们兄妹几个,按我爸的吩咐,伏在地上帮着裁纸。大门上的,二门上的,房门上的,院门上的,厨房门上的,粮囤子上的。余下的边角料儿,也不废掉,我爸会大笔一挥,在上面写个“六畜兴旺”,给贴到羊圈猪圈鸡窝上去。
那时不甚明了,怎么是六畜呢?村子里日常所见的,明明只有鸡鸭猪羊,有牛的人家也甚少,这加起来也才五畜。也是到后来,我念书了,懂得查阅资料了,方才把心中的疑团给解了。六畜,原是指马、牛、羊、鸡、狗、猪。它们是被我们远古祖先最先驯化的牲畜,渐渐演变成了家畜。《三字经·训诂》中,对“六畜”有着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宾客。
我的村人们当然不懂这个。他们也不管这个,只道那是牲畜兴旺,吉利吉祥。他们拿着那张“六畜兴旺”,高兴得不得了,眼睛眯着,笑嘻嘻地盯着看,似乎上面正跑着大肥猪和大肥羊。
一个村子的对联,很让我爸费脑子,他不想太重复,每家每户写的都不一样。他有时会停下手中笔,若有所思地问蹲着的一个人,你家大门上你想写什么呢?那人嘿嘿笑两声,回他,我哪晓得写什么啊,你写什么都好。我爸就写,金鸡报晓,红梅报春。又或是,春满人间福满园之类的。
有一年,我爸给我家大门上写的是“吃大肥肉,穿花洋布”。直白明了,清爽好记。村人们看到,都说这个好,都要求写这个。结果,那一年,全村人家,几乎家家门上都贴着这副对联。正月里在村子里走着,一个村子除了喜气洋洋外,又另添着一份跃动,满满的幸福的气流,在四处蹿着,似乎人人都穿上了新衣裳,人人都有大肥肉吃。真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