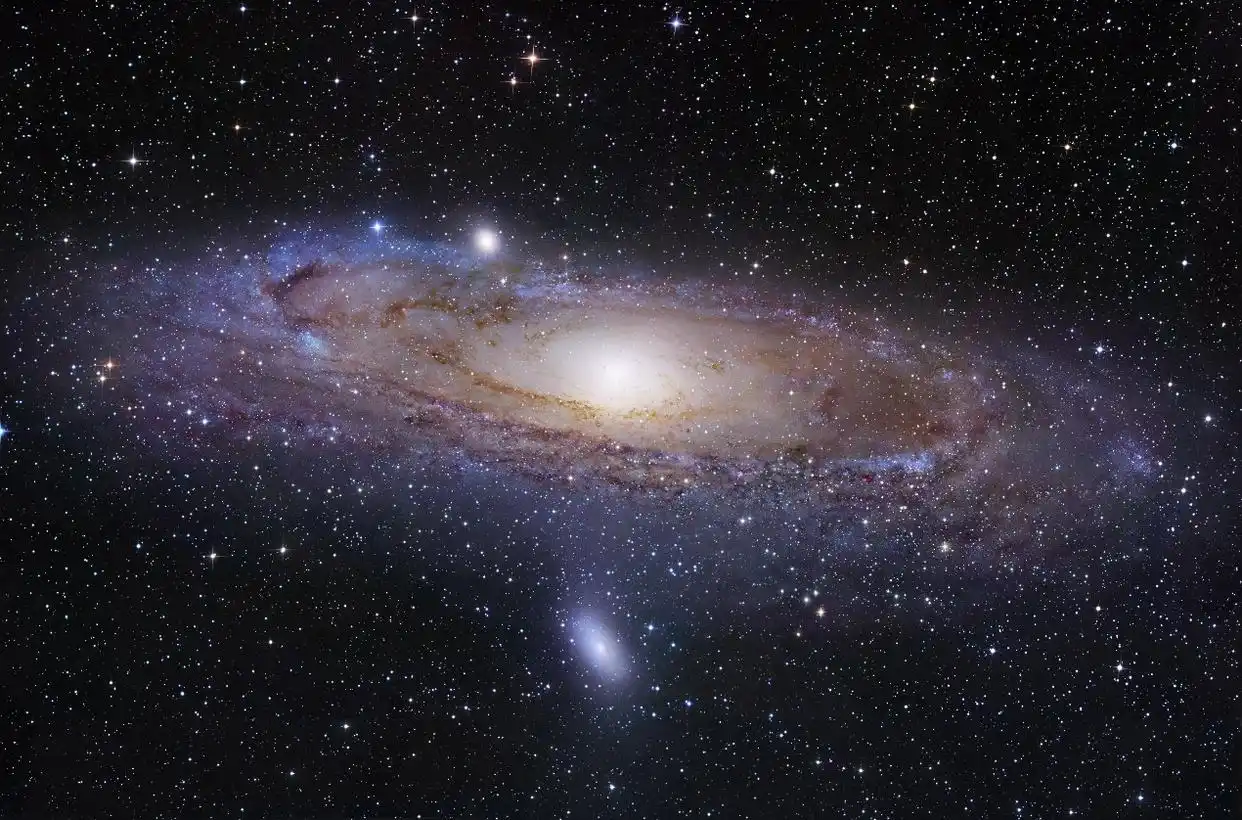1月11日下午,由浙江出版社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在北京皇家饭店举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了独家授权的“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被莫言认可为“定稿版”。“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的十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五种)亦将推出。
当天,莫言身着灰色中式棉布对襟衫,谈笑自如,言语风趣。莫言称,据家谱记载,祖上曾经在浙江龙泉生活过很长的日子,是当地有名的诗人,还有祖上曾经在浙江当过高官,至今仍有管姓族人在龙泉生活,自己也曾经在前几年去龙泉一个大山沟寻根访古,见过长辈。小时候的莫言常常看鲁迅作品,鲁迅是浙江人,后来莫言又有短篇曾入围过鲁迅文学奖,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茅盾是浙江人,莫言说自己是读着茅盾、鲁迅的作品走上的文学道路;从他们的文学里汲取了很多力量,发现了很多主题。“我们在他们的启示下,文学思想引导下,写出了新作,很多作品是他们的延续。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研究浙江的作家也就无所研究了。”
处女作稿费72元
1981年10月,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文学刊物《莲池》双月刊上以头条形式发表。他收到了72块钱的稿费,对于一个月只有15块钱工资的战士来说,不啻于一笔巨款。他请每个战士吃了最好的鸡,抽了当地最贵的烟喝了最贵的酒。在此鼓励下,他继续投稿,《莲池》一连刊发了他5篇小说。
在军艺大胆创新
让莫言发生重大创作变化的地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把全国各地著名的作家、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以讲座的形式请到学校,使学生们短时间之内接触了文学和文学的大量信息,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学的过去以及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注意到的部分,由此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提高了创作的立足点。“刺激了我们大胆求新创作。写出来哪怕不能发表也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在军艺莫言写了近80万字的作品,包括《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在内,学生们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创作有了很大提高。
梦想就是动力
莫言把精力基本放在长篇写作上,他在长篇的结构上下过很大功夫。早期写作写童年、童年记忆,写故乡的风土人情,民间口头文学,长篇小说依然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但是此时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扩展成为文学的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他把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各种事情都纳入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范畴内,“刚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写熟人亲人,继续写作就把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经历,当作自己的故事来写。”
从1981年到现在,莫言写了30多年,年过60的他依然有梦,在梦里,他被自己写的经典句子惊醒,醒来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我每次写作的时候都铆足了劲儿想写一篇世界文学经典,但往往写着写着就觉得像爬一座高山般,爬不到顶。”但梦想就是动力。
今年写不出新作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然过去5年,他的新作今年还是千呼万唤始不出来,他坦陈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很努力”。
莫言对文学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对写经典文学的准备也没有停止。“我一直悄悄地去要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所在地去做采访。”写作是延续性的行为,莫言的新作不可能切断与前面作品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都有内在的、永远不会变的关系,然而,变化一定会有,那便是时代滚滚前行所带来的。(新民晚报记者 徐佳和)
“莫言有言”答新民晚报记者问
问:您觉得您之后,还有哪位中国作家有希望获得诺奖?您是否有看好的作家?
答: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期盼第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热点和焦点都集中在他/她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作为诺奖获得者,我有向瑞典方面推荐作家的权利,我会好好地行使这个权利。我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五十年。
问:您说过您和贾平凹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出身相似,您如何评价他?
答: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从新疆回来到西安,素昧平生,我拍了个电报给贾平凹,让他来火车站接我的往事。那时候火车晚点了8个小时,他举着块写着“莫言”二字的牌子在站台上来回走,没人理他。深更半夜,西安火车站一出站,我充满希望四处张望寻找着贾平凹的身影,我的同学们都说,贾平凹那么大的名气,又和你素不相识,怎么可能来接你。多年之后,我在日本看到了他根据这件事写的散文,才知道真相,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人。
问:您以前说过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把自己当“罪人”写,是不是自我剖析的意思?
答:文学史上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好人坏人非常明确,文学描写也是用词分明,事实上不是如此,生活当中各种人都有,我们不能沿袭过去的写法。好人坏人都要当人来写,好人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要写出好人作为人的一面自私怯懦,坏人也有好的一面,也可能动恻隐之心。每个人心中总是有一个朦胧地带,在人和兽之间的朦胧地带。把自己当罪人写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一个作家深刻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宽谅他,才能被别人宽谅。把人当人写,不要受时代的政治的流行的观点影响,无论什么年代的写作都是把“人”当作首要对象。
问:现在的网络文学铺天盖地,改变了阅读方式,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很早就表态“热烈拥护”。网络文学是文学的重要补充部分,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遵循的最根本的还是关于文学的定律。发展、写作、阅读方式的不同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学的标准。由于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文学内容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是靠锤炼语言吃饭的,一切都是依靠语言本身的魅力,这是对所有写手共同的要求。
问:您的作品乡土性十分强,在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会不会有被误读的可能?
答:误读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中国,我的小说也可能被误读。文学可以有很多种阐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解释,像《怀抱鲜花的女人》等等,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人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如何。国外翻译家在语言翻译过程中挺艰难的,我的描写有很多描写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大量时代创造出的词语,对80年代生人解释起来都比较困难了。这样的过程中,误读是难免的。
1月11日下午,由浙江出版社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在北京皇家饭店举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了独家授权的“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被莫言认可为“定稿版”。“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的十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五种)亦将推出。
当天,莫言身着灰色中式棉布对襟衫,谈笑自如,言语风趣。莫言称,据家谱记载,祖上曾经在浙江龙泉生活过很长的日子,是当地有名的诗人,还有祖上曾经在浙江当过高官,至今仍有管姓族人在龙泉生活,自己也曾经在前几年去龙泉一个大山沟寻根访古,见过长辈。小时候的莫言常常看鲁迅作品,鲁迅是浙江人,后来莫言又有短篇曾入围过鲁迅文学奖,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茅盾是浙江人,莫言说自己是读着茅盾、鲁迅的作品走上的文学道路;从他们的文学里汲取了很多力量,发现了很多主题。“我们在他们的启示下,文学思想引导下,写出了新作,很多作品是他们的延续。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研究浙江的作家也就无所研究了。”
处女作稿费72元
1981年10月,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文学刊物《莲池》双月刊上以头条形式发表。他收到了72块钱的稿费,对于一个月只有15块钱工资的战士来说,不啻于一笔巨款。他请每个战士吃了最好的鸡,抽了当地最贵的烟喝了最贵的酒。在此鼓励下,他继续投稿,《莲池》一连刊发了他5篇小说。
在军艺大胆创新
让莫言发生重大创作变化的地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把全国各地著名的作家、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以讲座的形式请到学校,使学生们短时间之内接触了文学和文学的大量信息,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学的过去以及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注意到的部分,由此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提高了创作的立足点。“刺激了我们大胆求新创作。写出来哪怕不能发表也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在军艺莫言写了近80万字的作品,包括《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在内,学生们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创作有了很大提高。
梦想就是动力
莫言把精力基本放在长篇写作上,他在长篇的结构上下过很大功夫。早期写作写童年、童年记忆,写故乡的风土人情,民间口头文学,长篇小说依然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但是此时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扩展成为文学的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他把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各种事情都纳入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范畴内,“刚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写熟人亲人,继续写作就把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经历,当作自己的故事来写。”
从1981年到现在,莫言写了30多年,年过60的他依然有梦,在梦里,他被自己写的经典句子惊醒,醒来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我每次写作的时候都铆足了劲儿想写一篇世界文学经典,但往往写着写着就觉得像爬一座高山般,爬不到顶。”但梦想就是动力。
今年写不出新作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然过去5年,他的新作今年还是千呼万唤始不出来,他坦陈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很努力”。
莫言对文学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对写经典文学的准备也没有停止。“我一直悄悄地去要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所在地去做采访。”写作是延续性的行为,莫言的新作不可能切断与前面作品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都有内在的、永远不会变的关系,然而,变化一定会有,那便是时代滚滚前行所带来的。(新民晚报记者 徐佳和)
“莫言有言”答新民晚报记者问
问:您觉得您之后,还有哪位中国作家有希望获得诺奖?您是否有看好的作家?
答: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期盼第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热点和焦点都集中在他/她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作为诺奖获得者,我有向瑞典方面推荐作家的权利,我会好好地行使这个权利。我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五十年。
问:您说过您和贾平凹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出身相似,您如何评价他?
答: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从新疆回来到西安,素昧平生,我拍了个电报给贾平凹,让他来火车站接我的往事。那时候火车晚点了8个小时,他举着块写着“莫言”二字的牌子在站台上来回走,没人理他。深更半夜,西安火车站一出站,我充满希望四处张望寻找着贾平凹的身影,我的同学们都说,贾平凹那么大的名气,又和你素不相识,怎么可能来接你。多年之后,我在日本看到了他根据这件事写的散文,才知道真相,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人。
问:您以前说过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把自己当“罪人”写,是不是自我剖析的意思?
答:文学史上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好人坏人非常明确,文学描写也是用词分明,事实上不是如此,生活当中各种人都有,我们不能沿袭过去的写法。好人坏人都要当人来写,好人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要写出好人作为人的一面自私怯懦,坏人也有好的一面,也可能动恻隐之心。每个人心中总是有一个朦胧地带,在人和兽之间的朦胧地带。把自己当罪人写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一个作家深刻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宽谅他,才能被别人宽谅。把人当人写,不要受时代的政治的流行的观点影响,无论什么年代的写作都是把“人”当作首要对象。
问:现在的网络文学铺天盖地,改变了阅读方式,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很早就表态“热烈拥护”。网络文学是文学的重要补充部分,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遵循的最根本的还是关于文学的定律。发展、写作、阅读方式的不同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学的标准。由于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文学内容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是靠锤炼语言吃饭的,一切都是依靠语言本身的魅力,这是对所有写手共同的要求。
问:您的作品乡土性十分强,在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会不会有被误读的可能?
答:误读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中国,我的小说也可能被误读。文学可以有很多种阐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解释,像《怀抱鲜花的女人》等等,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人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如何。国外翻译家在语言翻译过程中挺艰难的,我的描写有很多描写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大量时代创造出的词语,对80年代生人解释起来都比较困难了。这样的过程中,误读是难免的。